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2期
ID: 420875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2期
ID: 420875
唐代宫怨诗情感维度的三重境界
◇ 吴雪伶
摘要:本文拟从唐代宫怨诗情感表达的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拓宽和挖掘,揭示后宫女性的真实生活,阐发宫廷女性的情感世界,表达后宫女性的失意苦闷、愁情怨情的心灵境地,以期真正展示宫怨诗深广的情感价值取向。
关键词:唐代 宫怨诗 情感维度 三重境界
引言
唐代宫怨诗是反映唐代皇帝后宫内苑众多嫔妃宫女愁苦哀怨、失意惆怅的诗歌作品,诗中女主人公大多有真诚的自我独白或委婉含蓄的情感抒发,也有关照熟知并同情后宫女性生活生存状态的男性诗人的代言拟写之作。唐代宫怨诗的情感抒发来自于后宫女性心灵的最深处,情感哀怨凄美,毫无修饰雕琢之嫌,是后宫女性灵魂深处的极度哀吟,是唐代女性自我情感价值的人生悲歌,具有跨时代的共鸣感和穿越时空的震撼力。
一、寂寥悲悯的苦吟之情
唐代后宫女性卑微的社会地位、低贱的特殊身份和独特的情感境遇造就了唐代后宫复杂多变的生活世界,展示了宫女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心理的各种情结,她们的内心世界变得极度的敏感和细腻,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极其委婉和含蓄。唐朝历代统治者常常把后宫作为自己权利专制的主要发泄平台或自己私人奢华生活的重要场所,后宫所有女性都是男权统治下的私人财产和娱乐工具,有个别极具才华或形象极佳的女性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宠幸,有机会常常侍奉在皇帝身边,她们大多也是皇帝喜欢的御用文人,这些上层的女性也极其附庸风雅,其宫怨诗主题大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内容上也倾向于抒写宫中豪华奢侈的宫廷场景及奢靡的宫廷生活,诸如初唐时期的一些后宫嫔妃及皇室公主、后裔等女性。但大多宫女均来自于社会的底层,是一些民间的良家女子,她们绝大多数被迫来到宫中,主要是一些中层或下层的官员主动进献给皇帝,以满足皇帝的淫乐生活;还有,每年也有皇帝亲自选妃的时节,这是唐代宫廷骄奢淫逸生活的真实反映。由此,宫中女性悲惨的命运及无聊苦难的生活自然展开,折射出唐朝历代宫女的心灵苦难历程,其内心的悲吟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
唐代后宫制度严密,等级森严,纪律严酷,白天黑夜都有太监或侍卫把守,没有君王的手谕或直接命令,一切大臣或闲杂人员绝对不能随意出入宫闱禁地。尤其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入宫宫女,一旦进入这个牢笼式的人间地狱,永生将隔绝于人寰,“宫门一入无由出,唯有宫莺得见人”(顾况《宫词》)。若有违反宫规戒律的宫女,将受到残酷的刑罚和折磨,由此,这些宫女将失去完全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受尽无端的凌辱和残酷的压榨。她们的吃穿住行用皆都受制于严厉的制度管理,不论白天黑夜,打扫庭院,洗衣叠被,或浓妆淡抹,弹奏歌舞,不知疲倦,侍奉在皇帝身边,时时刻刻接受君王的召唤或役使,“春天睡起晓妆成,随侍君王触处行”(花蕊夫人《宫词》)。“传声总是君王唤,红烛台前著舞衣”(王涯《宫词》)。这些可怜的宫中女子,大部分原是农家良女,一部分是贵族千金或名门闺秀,但到了宫闱禁地,她们都有同样的生活境地及人生下场。她们烂漫的青春、自由的幸福、理想的爱情瞬间化作泡影,多少个美好的人间岁月,都在这无聊寂寞的后宫生活中消失殆尽,看不到明媚的阳光,呼吸不到新鲜自由的空气,不管多少个不眠之夜,寂寥悲悯的苦吟之情完全充斥于她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哀鸣愁恨的幽怨之情
唐代宫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后宫女子的感情世界是由外到内、由弱到强的,这缘于她们生活在宫中的最底层,比起那些后妃、女官,她们从入宫红颜到老死宫中都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君王,更难以得到宠幸,除非有偶然因素得到君恩而青云直上,这样的几率微乎其微。由此,这些宫女所背负的压力和承受的痛苦是多方面的,是无法释怀的,留给她们的只有流不尽的眼泪,“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张祜《宫词》)。还有,张祜的《孟才人叹》:“偶因清唱奏歌频,选入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何满子》,下泉须吊孟才人。”后宫像这样一生都在“卧看牵牛织女星”的宫女们比比皆是。风华正茂的青春激昂早已被深宫大院的糜烂奢华所扼杀,她们多少次在月明凄冷的深夜独自徘徊,独自倾听清冷的雨声;面对皓月当空,她们又是多少次披衣起床,细数“更漏”,心中的幽怨之情更是油然而生,李白的《玉阶怨》写道:“玉阶生白露,夜久浸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这个近乎失眠而麻木的宫女,没有高呼什么自由、爱情、幸福,只有“却下水晶帘”的细微刻画,满脸怅惘愁苦的哀情让我们感受到她无言的凄楚,引发了我们浮想联翩的惆怅思绪和无限遐想。
白居易的《上阳人》把宫女的这种哀鸣愁恨的幽怨之情抒写得极其真切和凄美动人,宫中“入时十六今六十”的“红颜白发”刻画得细致入微,体现了众多后宫女子的共性悲歌,她们带着青春年华的憧憬和希望进入到宫中,她们又背负着一生的痛苦和悲哀而老无所依,面对这些让常人无法承受的苦痛和折磨,她们依然毫无怨言,没有明显的反抗和斗争,只有在自我欺骗的内心世界里无奈地挣扎,她们内在郁结的哀鸣愁恨蕴涵了多少辛酸和泪水,也折射出整个唐代帝国广阔的女性生活画面。从唐玄宗末到唐宪宗初的五个朝代里,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女子被无情残杀,展示出众多宫女在唐代宫殡制度下是如何惨遭不幸的,真实地批判了封建制度对古代女性残害的罪恶,由此,一些具有道德良心和社会责任意识的政治文人开始关注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通过诗歌的艺术手法和抒情技巧展现得淋淋尽致,进一步促发了唐代宫怨诗的大量涌现,有不少诗人怀着一颗极具敏感性和同情性的心理去真实再现后宫女子严酷的生活处境和复杂的情感世界,开始真正关注和把握这些宫女深层的心理世界,如元稹的《上阳白发人》、王建的《宫词》、李商隐的《宫辞》等诗作。尤其是白居易的《后宫词》:“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这里描写“君恩无常”残酷的社会现实,是造成宫女悲怨之情的真正缘由,宫女内心复杂微妙的心理世界是难以琢磨的,也是无法直接渲染和客观体现的,只有通过特殊的意象和真实的意境来侧面暗示和间接烘托,这样一来,唐代后宫女子痛苦生活的悲惨境地和哀鸣愁恨的幽怨情感就能得到真实的抒写和体现。
三、失意惆怅的绝望之情
古代女性情感压抑引发情感表达的委婉迂折,是唐代宫怨诗文学艺术表现的共性特征,这些宫女深受传统妇道规范的约束,长期地幽闭深宫,情感细腻,感觉敏锐,蕴藉委婉的情感表达与借物寄托的情感抒写成为了她们思想哀鸣的主要传输方式,她们渴望自由的爱情,向往真正的幸福,她们手持团扇,时而仰望明月,时而戏耍流萤;她们对镜自赏,时而细数更漏,时而转寄红叶,她们细致深婉,一唱三叹,倾诉着自己的失意惆怅,表达着自己的绝望无奈,这些宫女情感生活特有的阴暗色调,正源自她们内心难以言说的自我压抑感。她们面对残酷的现实生活和命运遭际,无法也无力改变自己的客观现状及周围环境,她们既不能超脱自我,又不能超然物外,她们只有逆来顺受,安于现状,无奈忍受着怨恨情愁的隐痛。宫女一生基本上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被迫奉献给了这个与世隔绝的人间地狱,她们失意惆怅之情达到了无以言表的绝望之境地,她们给世人只留下了一个被压榨得像干尸一样的躯壳,她们默默地来,又悄无声息地死去,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任何礼葬,更没有什么墓碑,留给世人的仅有一片荒凉的凄惨景象和一段凄迷的情感故事,“秋草宫人斜里墓,宫人谁送葬来时”(张籍《宿山祠》)。“云惨烟愁苑路斜,路傍丘冢尽宫娃。茂陵不是同归处,空寄香魂著野花”(孟迟《宫人斜》)。这些宫女的香消玉殒,无端死去,并没有给统治者奢华糜烂的宫廷生活带来丝毫的影响,新宫女又源源不断地输入进来以供君王们尽情享用,“未央墙西青草路,宫人斜里红妆墓。一边载出一边来,更衣不减寻常数”(王建《宫人斜》)。无论当时有多少御用文人怎样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都无法掩盖帝王后宫穷奢极欲的黑暗生活。
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是作者自身情感的真实折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情动于中而感于外”“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份特有的情感沉淀着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复杂的生活遭际。唐代宫怨诗有着深厚的情感内涵,内蕴着唐代后宫女性忧愁怨恨、失意绝望的心灵隐痛,身上背负着女性特有的安顺与容忍,如此众多的宫女长期地幽闭深宫,在人身及人性方面遭受到严酷的压制和禁锢,这样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有八百多首,宫女所遭遇的情愁绝望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空前绝后的。由此可见,唐代后宫女性这一弱势群体在当时应该是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诚然,这种突出的社会现象会引起唐代诗人们的热切关注,再加上这些士人们特有的生活仕途遭际,怀才不遇的特定心理与失宠宫人的绝望情感二者不谋而合,使宫怨诗的创造主体具有鲜明的双重身份,既代言关注唐代后宫女性的悲惨遭际,又借此婉转表达他们自身的失意和无奈,这也促成了唐代宫怨诗的完全勃兴。这种以情愁怨恨为内核的悲感情怀,建构了唐代宫怨诗主要的情感流向,这种灰暗的情感基调夹杂着男性代言诗人自己独特的身世飘零之感和仕途失意之叹,诸如李白的《怨歌行》、李商隐的《深宫》、刘禹锡的《秋扇词》等,他们运用特定的意象来寄托自身复杂的人生阅历和艰难的仕途生活,并善于营造合适的意境来深层地理性思考他们自身的生活情感和人生哲理,其背后蕴藏着唐代历史上重大的社会变革和险恶的政治斗争,这与唐代后宫女性特有的情感心理有着深层的契合,二者呈现出内外双重维度的情感交叉与共鸣,这种特有的“心理同构”共同推进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可以看出,唐代后宫女性自身特具的生理及心理特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及演变过程中熔铸了唐代特有的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共同建构和培育了唐代女性文学的情感系统,这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结语
只从内容上来看,唐代宫怨诗题材过于单一,缺乏缜密的逻辑构思和深邃的人生哲理,这主要缘于后宫女性的特殊地位、身份以及单调枯燥的宫廷生活,但她们所表达的感情的确蕴含真实的情感体验和灵动的情感抒发,朴实而纯正,是任何文人都无法矫情造作的。这种特殊的情感价值趋向以悲为美的审美艺术风格,也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唐代宫怨诗的极度繁荣和昌盛,唐代宫怨诗作为古代悲美文学的重要一环,既反映了盛唐气象中奢华的宫廷物质生活,也折射出唐代下层女性渴望真情、呼吁自由的强烈愿望,以及在封建宗法制度及“非人性”礼教压制下被极度摧残扭曲的人性价值,同时,也萌发了唐代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语
参考文献
[1]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俞世芬.唐诗与女性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苏者聪.论唐代宫女诗及宫女命运[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5).
[4]韩理洲.简说唐代的宫怨诗[J].人文杂志,1985(6).
【基金项目:2015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文化视阈下的唐诗女性意识研究》(编号:2015-ZD-036);2012年洛阳师范学院省级培育基金资助项目《唐代宫怨诗中的女性意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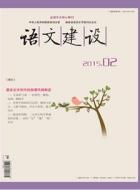
- 莫言文学创作的叙事风格解读 / 周婧
- 浅析狄兰·托马斯诗歌语义的双重性 / 严丽?周灿美
- 高校儿童文学课程体验式教学刍议 / 何敏怡
- 高校写作课教学改革策略 / 高惠宁
- 建构主义关照下的语文阅读教学 / 王昭君
- 文本阐释与文学教学 / 白红兵
- 高校语文教学下“对话式教学”所蕴含的生命意义 / 任春茂
- 高职汉语言文学选修课建设探索 / 郑小娜
- 高校语文教学中的文学诗词鉴赏 / 贺东辉
- 《的职场启示》信息化教学设计 / 胡芳
- 现代诗歌教学中的情景假设 / 李东平
- 高职语文教学中的文学赏析探索 / 褚智慧
- 论高校语文阅读功能与教学的思考 / 肖颖
- 高职语文教学改革与策略研究 / 严绍国
- 高校语文教学问题与建议探索 / 张建军
- 关于胡适文言文教学方法中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探索 / 李宏卓
- 在生本理念下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 杜雅娟
- 女性主义视角下《飘》中斯佳丽的人物形象 / 焦悦梅
- 英美文学中哥特式艺术手法渗透论略 / 李红琴
- 《巴黎圣母院》的文学语言分析 / 张琴
- 论《老人与海》中象征手法的运用 / 谭祎哲
- 从《聊斋》中探究中国文学中的诗化美学 / 莫宇芬
- 薇拉·凯瑟小说《啊,拓荒者!》中的神话原型分析 / 张佳卉
- 论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叙事解读 / 赵前明
- 川端康成《雪国》中人物与创作风格研究 / 樊云
- 浅析《喧哗与骚动》中人物的内心塑造 / 全斌
- 孔子《论语》中名句注解与语言阐释 / 任梦池
- 跨文化视角下对《女勇士》中文化冲突的解读 / 王雪玲
- 象征主义视角下对《阿拉比》的解读 / 张蔚
- 《乡愁》中永恒母爱主题的解读 / 徐保国
- 语言合作原则下对小说《傲慢与偏见》中对话的解读 / 蔡景界
- 外国文学中“重复”结构的叙事分析 / 刘海瑛
- 《白象似的群山》的认知解读 / 李慧
- 生态视角下对《乌托邦》的解读 / 许芳芳
- 对《麦琪的礼物》文学语言艺术的赏析 / 王海蓉
- 从《史记》谈司马迁的史学贡献 / 杨玉萍
- 唐代宫怨诗情感维度的三重境界 / 吴雪伶
- 隐喻视角下的波德莱尔诗词语言 / 刘汝举
- 老舍《四世同堂》文学修辞语言赏析 / 李莉勤
- 文学审美视域下的导游辞写作研究 / 张宁??张乐
- 庞德《华夏集》中李白诗词翻译研究 / 张珏
- 柳州话的动相补语“过” / 易丹
- 多语接触下的百色右江区粤语变异研究 / 严春艳
- 目的论下《爱丽斯漫游仙境》思想与艺术研究 / 莫小芳
- 高校体育专业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路径 / 戴绍斌
- 汉语教学对高校英语教学创新的启示 / 郝建君
- 人文关照下大学思政教育的融入策略探微 / 胡沁熙?曹雯
- 维吾尔族大学生维汉语码转换探析 / 卡米力江·阿不都克力木
- 人文理念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 / 薛潇
- 英语教学中汉语教学迁移机制探微 / 赖妍莉?谢敏
- 大学语文教学对高校体育专业学生人文精神的提高功能 / 赵云书
- 法制史教学中古代文学作品运用的路径略谈 / 李容琴
- 高校体育教学中人文素养的培育思考 / 王民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