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08年第6期
ID: 376418
语文教学之友 2008年第6期
ID: 376418
对标点符号用法中三个疑点的探析
◇ 周保华
目前,中学的标点符号教学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不敢讲、怕讲,有时还不得不讲。例如2004年全国四卷第五题A项:
我们凤凰电视台不存在“阴盛阳衰”的现象。“凤凰”这个词本来就是阴阳结合的:“凤”是雄鸟,“凰”是雌鸟;凤凰台台标也由两只鸟组成:一只公的,一只母的。
此句是正确答案,即“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句”。然而句中“雌鸟”后面已用分号的地方该不该用句号?
又如:我在我的《略论语言形式美》里,指出语言形式美有三种:第一是整齐的美;第二是抑扬的美;第三是回环的美。(王力《语言与文学》,人教2002年版第六册第31页)
此句中的两个分号用得对不对?
这两例都是关于分号的用法。从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以下简称“国标”,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5年12月13日发布,并于1996年6月1日施行)来看,这里的两种情形都未被规范,后例也不属于分行列举。按照目前教学中通行的做法,前者应改为句号,后者的两个分号都应改为逗号。
面对如此困境,我们无论是搞理论研究的还是从事教学实践的,都应积极探索,要在讨论、总结的基础上加以规范,因为在现代汉语表达中标点符号的作用太重要了。笔者虽学识浅陋,难以对众多疑难一一作考察、梳理,但愿意将自己碰到的几个问题罗列在这里,与方家进行交流。
问题一:非完整引用中,引文末尾的问号是否保留?
先看一个例子:
【例1】在语法方面,古今也有不少差别。例如“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就是古代特有的句法,底下“吾与徐公孰美?”才跟现在句法相同。(吕叔湘《语言的演变》,人教2002年版第六册第38页)
例中引文末尾的问号就保留着。这或许是吕叔湘先生的做法,至少代表了教材的观点。再如:
【例2】人的一生中有很多时候都少不了需要通过书面向别人介绍:“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或“我有一个怎样的方案?”这样的问题,因此现代人有更多的理由需要学好作文。(2004年全国四卷第五题B项)
这是一个干扰项,大多数参考分析都认为仅是冒号用错了,不觉得这里的问号用法有问题。当年的出卷专家是否也这样认为,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这两例有这样的特点:句中引文只是作为一个短语充当分句的一个成分,已失去作为问句的独立性。
但问题是,不少书籍或高三复习资料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如:
【例3】“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会问‘月亮为什么会跟我走’‘天有多高’‘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坏人’这些问题。”(《高中总复习优化设计·语文》西苑出版社,2004年第四版第147页)
该书就认为语句中标点符号的用法是合理的,引文末尾并未保留问号。再如2004年全国卷三的第五题C项:
【例4】19岁的女大学生在《幸运52》节目中连续七次夺魁引起了媒体的好奇。有的请她讲:“如何多才多艺”;有的追问她:“怎样身兼数职”;还有的让她讲什么都行……
此项为干扰项,几乎所有的参考分析都只认为句中的书名号应改为引号,且两个冒号应删除,并没有人认为该句的两处引文中该保留句尾的问号。
笔者认为,省去引文中的问号并不会影响语句的表达效果,因为引号内一般都有“怎样”“如何”“为什么”等疑问词提示其语气,引号外一般还有“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等词或短语予以概括。例1中的问号省掉也是可行的,文言本身就无标点。至于此处保留问号的做法大可值得怀疑,标点符号的用法至今都还未成熟,何况吕先生那个时代呢?再说,教材也常出错,即如《语言的演变》中就有这样明显不合常规的例子:
【例5】《世说新语》:“俄而谢玄淮上信至,(谢安)看书竟,默默无言”,“信”和“书”的分别是很清楚的。(人教2002年版第六册第41页)
此句的冒号显然不能管到句末。
再考察目前实际教学中通行的做法,几乎所有资料都一致认为此种情形下末尾的句号或其他句内点号都不应保留。所以,为简明和统一,笔者建议不如将这种情形下的问号也省去。
由此推理,此种情形下的叹号也可省去,这样规则就更统一了。教材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例6】……“他干什么都很出色,真行”,这句话不像上一句四个字四个字的,不整齐,但是也可以,也不错。(张志公《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人教2002年版第六册第44页)
引文中“真行”的后面未保留感叹号。可见,省掉并不会影响作者的表达。
问题二:分号能否表示几个带有冒号语句之间的并列?
例如开篇所引2004年全国四卷第五题A项。再如:
【例1】人言可畏么?答:可畏,又不可畏。可畏者,舆论能形成压力;不可畏者,人们常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高中总复习优化设计·语文》西苑出版社,2004年第四版第147页)
此句标点符号的使用被认为是正确的。这两个例子都认同分号能表示几个带有冒号的语句之间的并列。但平时的阅读和写作告诉我们,这样的使用是欠合理的。尽管冒号和分号都属于句内点号,但一般而言,冒号表示更大的语气停顿,或用在提示语后面,或用在总说性词语后面,或用于总括性词语的前面。例如:
【例2】经验告诉我们:天空的薄云,往往是天气晴朗的;那些低而厚密的云层,常常是阴雨风雪的预兆。
【例3】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在化学系学习;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读机械制造专业;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如果忽视冒号与分号这种在表示句内语气停顿上的差别,势必导致语意表达欠合理,语气欠流畅,而且还会导致通常用法的混乱。所以笔者认为,应尊重这种差别,舍弃用分号来表示几个带有冒号语句之间并列的做法。
同时应明确,若没有使用逗号,则不能用分号来表示并列,如本文开头王力先生《语言与文学》中的那个句子。
问题三:在表示并列的书名号或引文之间可否使用顿号?
在平时的阅读或练习中,经常会碰到类似下列顿号用法的句子:
【例1】参加国庆献礼的优秀影片:《风暴》、《青春之歌》、《林则徐》等,也将在各大城市放映。(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高教出版社,1997年第2版)
【例2】高中语文课程继续坚持《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提出的基本理念,根据新时期高中语文教育的任务和学生的需求,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方面出发设计课程目标,努力改革课程的内容、结构和实施机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第1页)
例1中几个表并列的书名号之间使用了顿号,例2中三个并列的引文短语之间使用了顿号。像这种情形,不用顿号的也有很多。如:
【例3】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大都是文人采用民间创作而进行的再创作。(吴组缃《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人教2005年版高语第五册第25页)
【例4】用什么词儿呢?用“灵”“机灵”“伶俐”“很鬼”“很有心眼儿”?(张志公《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人教2002年版高语第六册第44页)
这种做法会给读者产生混乱的印象,让人无所适从了。笔者认为,在并列的书名号之间可以不采用顿号,因为阅读过程中书名号本身能让读者产生停顿的感觉,而且省去之后又丝毫不影响语意表达,反而显得更简洁。否则,就有为标点而标点之嫌了。但在连续的几个引文之间,若相互为并列关系,还是使用顿号更妥当、更明确些,因为连续的几个引文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多种情况,是否使用顿号含有一定的表达意义。如:
【例5】此“心”“常一”,是不随动静、昼夜、生死而变化的永恒之“心”。(刘晓梅《杨简实心思想探微》,《兰州学刊》2006年第5期第21页)
【例6】“通为一体”只是说明了“心”与“天地万物”一体无碍的状态,但“天地万物”以何种方式达到与“心”“通为一体”的状态?(王心竹《浅析杨简“心本论”思想》,《湖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四期第40页)
例5第一分句中两处连续的引文之间为主谓关系。例6中“与”后面的两处引文之间并非并列关系,“与”跟“心”构成介宾短语,这个介宾短语又与“通为一体”构成偏正关系,共同作为“状态”的定语。
因此,在几个引文之间使用顿号就有了明确表达并列关系的作用,区别于其他逻辑关系。比较规范的司法文件也常有这样的用法,如:
【例7】“×××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辩称”、“自诉人×××诉称”、“经审理查明”、“经复核查明”、“本院认为”等词语后面,凡所提示的下文只有一层意思的用逗号,有数层意思的用冒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制作刑事裁判文书技术规范要求的意见》)
有争议的用法还有很多,“国标”只对各种常用标点符号的基本用法作了规定,还无法规范实际运用中的诸多情形。但像下面三例中个别标点的使用则有随心所欲之嫌了:
【例1】现在创作上有一种长的趋向:短篇向中篇靠拢,中篇向长篇靠拢,长篇呢?一部,两部,三部……。当然,也有长而优、非长不可的,但大多数是不必那么长,确有“水分”可挤的。(《语文建设》1991年第7期第32页)
此句中省略号后再加句号,显得多余。
【例2】唐先生教宋词,基本上不讲,打起无锡腔调。把词“吟”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过了。(2006年高考湖北卷第5题的B项)
此句被认为是标点符号使用合乎规范的。然而句中“无锡腔调”后的句号,就让人颇费思量,与下句语意似有不通。
【例3】(那些人)描写极光时往往显得语竭词穷,只好说“无法以言语形容”,“再也找不出合适的词句加以描绘”之类的话作为遁辞。(曹冲《神奇的极光》,人教2002年版初语第二册第17页)
此句两处引文之间为并列关系却使用了逗号,可能意在强调,但实无必要,应改用顿号为妥。
笔者认为,我们应对实践运用中一些通常的重要的用法积极地进行梳理,并加以规范。这不仅是中学语文教学指导所必需的,更是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需要。规范的首要原则应是保证语意表达的准确、清晰、简洁、流畅。对那些可用也可不用的,我们就一律不用,尽可能减少随心所欲的现象。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些语文老师能走出标点符号教学的尴尬境地。
(作者单位:宁波市慈湖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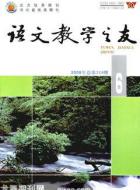
- 语文课改,想说爱你不容易 / 聂翰贤
- 新时期“说课”的误区及其对策探究 / 魏仁勇
- 课堂有效教学的实践与反思 / 姚正祥
- 把好语文教学文本解读的“位” / 蔡俊
- 品好课的滋味 / 刘朋 刘现学
- 课堂上究竟谁该配合谁 / 吕锡锋
- 浅谈语文教学中问题意识的培养 / 姚建芳
- 将课堂讨论引向深入的几种方法 / 徐颖瑛
- 教学中如何培养学困生的自读意识 / 祁文霞
- 语文审美教学策略探微 / 周平
- 怎一个“不会读”了得 / 钱雨辰
- “每日一诗”激活课外阅读 / 傅玉玲
- 略谈词牌名的文化内涵 / 王继红
- 是什么挤占了学生诵读文言文的时间 / 谢国泉
- “阿长”和“长妈妈”哪个更好 / 牛玉峰
- 真假结合 虚实相生 / 苏叶和
- 感悟《斑羚飞渡》 / 赵雅静
- 漫谈佩刀 / 高永正
- “落英”何解 / 徐文健
- “十九个钱”里的深意 / 胡敏
- 到底谁是害死祥林嫂的真正凶手 / 赵爱兵
- 凄苦的命运 不屈的抗争 / 李虎润
- 析“伯庸” / 曾从祥陶淑芬
- “表达方式”应包括“描写” / 郑学武
- 优化作文模式 强化主体意识 / 李仲楷
- 巧拟“题记”先声夺人 / 王峰
- 议论文“三步开头法” / 谷孝平
- “语文试卷讲评”八面观 / 邵明瑞
- 模拟考试之后,教师还有哪些事可做 / 沈国全
- 从《七步诗》看考场作文技巧 / 崔秀燕
- 如何巧妙提取关键词 / 师修武
- 漫画类题型解答技巧 / 凡建锋
- 中考作文应让真情飞扬 / 孟庆巧
- 对标点符号用法中三个疑点的探析 / 周保华
- 古诗文喻词辩正例析 / 于彦春
- ABB式的形容词应该怎样读 / 路书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