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08年第10期
ID: 80977
语文建设 2008年第10期
ID: 80977
也谈“文言文教学:行于‘文’‘言’之中”
◇ 周保华
读罢程永超老师的《文言文教学:行于“文”“言”之中》及其《(兰亭集序)教学设计》(《语文建设》2008年第3期),感触良多。我赞成程老师关于文言文教学的基本看法,也就是“文”和“言”要结合起来,反对将二者割裂。时至今日,我们对文言文教学陷入迷途虽有警醒,但一线教学仍远未得到应有的纠正。更有实效的研讨可能是多提供一些从“言”到“文”的思路。让一线老师有更多的教学选择和教学启发。有些遗憾的是,程老师对此还是惜墨如金。让人意犹未尽。笔者不才,斗胆想作一申述,希望有更多的行家来关注此事。以下笔者结合新近教过的《季氏将伐颛臾》(以下称《季》文)来谈,请行家批评。
一、因言释文
这是文言文教学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一直以来大家所倡导的。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这个方法常被扭曲:或成为“言教”,滑向应试教育的泥坑,或成为“文教”,蜕变为“人文大旗”上的一种点缀。在新课程背景下,笔者认为,坚持因言释文就应该做到扣“言”要严、释“文”要精。
不扣住“言”,释“文”就失去了基础,架空式分析就不可避免,也肯定经不起考试的检验。不少表演性的教学就是如此。扣“言”,一方面要扣住重点词句。详加落实。比如《季》文第一节“无乃尔是过与?”就要让学生明确其句法。此句中“无乃……与?”是一个表示推测语气的疑问句,“尔是过”为宾语前置句,“是”起提宾作用。其次要明确“尔”“过”的词义,对于培养高一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这样的词句具有基础性作用,要敢于不避“将文言文肢解成语言碎片”的嫌疑。另一方面,要扣住有“文”可释的词句。笔者以为,这里的“文”应指“文章”“人文”“文化”。在让学生找出或明确相关语句的基础上,教者可择要发挥,适可而止,即所谓的“精”。比如《季》文第一节中,孔子一口气提出了季氏不该伐颛臾的三点理由:“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这里就已初步显示出孔子思想的两个基本点:礼和仁。教者在此可以先点一下,为下面进一步理解孔子的德政思想作铺垫。
笔者以为,一些重要的“微言”也值得关注。中国古文的遣词用句很多都秉承了《春秋》以来“一字寓褒贬”的文化传统,即所谓的“春秋笔法”。笔者虽反对穷一切“微言”之大义,但对一些与表现文章主旨密切相关的“微言”,认为还是有关注的必要。这也是因言释文。如《季》文开篇便是一句“季氏将伐颛臾”,第一节也以孔子一句反问“何以伐为?”作结。这两个“伐”字不就表现了孔子对即将发生的这场战争的态度吗?我们知道,古人可以用很多暗含不同态度的字眼来叙述战争,如“征、伐、侵、袭”等。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第十六》)季氏作为鲁国的臣子更无资格征伐作为鲁国“公臣”的颛臾,“季氏将伐颛臾”就是无道。本身就是非正义的,“何以伐为”?《左传·庄公二十九年》载“凡师有钟鼓曰伐”,北宋欧阳修也曾解释说“以大加小曰伐”。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季氏打算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去征伐邦域之中毫无抵抗之力且无罪的颛臾的情景。孔子用一“伐”字不正表现了他对季氏卑劣行径的愤慨吗?不正暗示了季氏在大张旗鼓背后所暗藏的祸心吗?这正与文末“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的精辟论断相呼应。教学中。若仅简单地以译文“攻打”来一笔带过。笔者觉得很可惜。
二、因气悟文
中国古代很多大家作文、读文都非常强调“文气”。如唐代韩愈认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清代姚鼐在其《惜抱轩尺牍·与陈处士》中说:“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疾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味”。更早的曹丕和刘勰分别在自己的专著《典论·论文》和《文心雕龙》中都多次以“气”论文。这对我们今天理解古文应有启发。
文气是什么?笔者以为,文气就是流淌于字里行间的作者情韵。弥漫在词句虚实中的某种情绪。优秀的作品。文气总是协调统一、贯穿全文始终的。我和我的同事们尝试从感性体验和理性领悟两个方面来体会文气,从而“悟文”——体会文本蕴涵的作者思想和精神。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感性体验,重在朗读。朗读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读准字音、熟悉文句,更在于通过体会音韵的高低、语势的变化节奏、虚词表现的语气等来体会文气,“求其体势”与“求其神味”并重,从而深入理解文句。如《季》文第一节孔子之言的语气就富有变化:“求!无乃尔是过与?”尽管语含责备,但语气仍很委婉。接着,孔子一连列举出三大理由,充分证明季氏伐颛臾的无理,也表现出对季氏的愤怒。最后“何以伐为?”一句。显得理直气壮。反诘有力。如果说在第一节孔子对自己的弟子还存有宽容的话,那么第二节已不留情面,“不能者止”“且尔言过矣”,就是直陈其错误了。这里,孔子用了两组反问。前一组先用两个短句陈述,语气急促。再用一个长句来反问,抒发内心的激愤;后一组,“且尔言过矣”,在责备中有长叹,接着仍用两个整句来陈述,再用一个短句来反问。进一步表现出对弟子不肯认错、推卸责任的气愤。在这些语气的变化中。孔子“当仁不让”的精神已初步展现出来。第三节,孔子对弟子口是心非、助纣为虐的言行更加气愤。罕见地用“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这样的长句来严厉驳斥,然后慷慨激昂地阐述了自己的德政思想,批评冉有和季路的不作为。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坚持追寻政治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已充分展现出来,对话中展现出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以朗读为抓手。带动对关键词句的理解,再落实到对文气的体会。这样的文言课堂不是更有生气吗?这样。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不就可以抛弃机械、死板的语言材料而面对一个个鲜活的古代生命吗?汲取古人鲜活的情感、精神和智慧不正是新课标指示的学习古代优秀作品的最大价值吗?
理性领悟,重在体会文章的逻辑力量。理性分析是解读文本的常用方法,但仅满足于一般性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特别重视文本内在的逻辑力量以及由此展现出的“正气”“浩气”,这样学生对文本会有更加切实和深刻的理解。诸子散文中很多文章都有很强的逻辑力量,孟子的散文尤其如此。《季》文的内在力量也非同寻常。全文三段其实是三组驳论性对话。呈现先破后立、破中有立的驳论文特点。第一节孔子是针对季氏征伐颛臾的错误而言,第二节孔子是为驳斥冉有、季路推卸责任的言辞,第三节孔子是为批驳冉有、季路错误的治国之道。从整体来看,孔子的态度渐趋严厉。话语也渐趋增多,情绪变得更加激昂,内涵逐层丰富和深刻。展现出一个有浩然正气的孔子,一个为实现自己“礼”“仁” [##] 思想而奋力鼓吹的孔子。
从具体的段落来看。孔子的阐述思维严密,义正词严。力量强大。在第二节。孔子连续运用了引用、类比和比喻等论证手法,将冉有、季路作为季氏家臣所应负的责任阐述得具体而清晰,将他们的托词彻底击穿。第三节,在直接掀开冉有、季路狡辩的面纱后,孔子先正面阐述自己仁德的治国之道,再与冉有、季路错误的行为作对比,使弟子们的严重错误无处遁形,最后再精辟地、极有预见性地指出季氏的险恶用心,以告诫和警醒弟子。至此,弟子们还不惭愧万分、幡然醒悟?朱熹《四书集注》在《论语》这章后引洪氏注曰:“二子仕于季氏,凡季氏所欲为,必以告于夫子。则‘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颛臾之事,不见于经传,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与?”洪氏此注为朱子所重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因疑探文
孔子“均”“和”“安”及“修文德”的理想政治影响华夏几千年,直至今日,我们阅读《季》文仍常常为之感动。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别的收获吗?孙绍振教授说:“分析的对象是文本的矛盾,而许多无效分析,恰恰停留在文本和外部对象的统一性上。”(《语文建设》2008年第3期)满足于“文本与外部对象的统一性”分析虽未必完全无效。但至少是收获单一。扣住“文本的矛盾”来分析文本确实是精辟的见解,当为我们这些一线语文老师所铭记。《季》文三组驳论性对话显示的就是孔子与其学生冉有、季路在对待“季氏将伐颛臾”这件事情上的矛盾,扣住这组矛盾的发生和发展就扣住了本文学习的核心。但是,还有一些矛盾也是值得探究的,这将丰富和加深我们的理解。
比如,《季》文所呈现的孔子对待学生的态度就有让人疑惑之处。我们平时所知的孔子是位温文尔雅、循循善诱的长者,如《论语》开篇《学而》所表现出的长者风范、君子风范。但是他在这里对待两位学生怎么有些声色俱厉呢?
学生会有此一疑,教者不妨引导学生抓住文本进一步思考:孔子对待学生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通过探究,学生会发现,开始时,孔子的责备还是委婉的。如“无乃尔过是与”,因为本段重在批评季氏。但冉有、季路“夫子欲之”的辩解使孔子不满,批评也变得严肃而直接了。等到冉有说“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就看清了他们支持季氏的真实意图,而且发现他们前后言辞矛盾、心口不一,于是变得非常愤怒。这种愤怒,我们可以从孔子对冉有一再直呼其名,以及“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这样的句子里强烈地感受到,更可以从后文关于治国方略的强烈对比中感受到。孔子是为弟子们口是心非、巧言强辩的伪君子行径而愤怒,是,为弟子违背他的谆谆教诲、背叛他的德政思想而愤怒。更是为自己的思想为世人所弃,甚至也为自己的弟子所弃而痛心。
类似的情景,《论语》中还有不少。比如《子路篇》,孔子认为治国必先正名。子路却批评老师说:“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就责他“野哉,由也!”然后详细阐述自己必先正名的思想。孔子的愤怒不仅仅是因子路的无礼,更是因为子路对自己思想的背弃。
在这里,我们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孔子的严师形象,更有当仁不让、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
这样的疑惑,文中还有不少。要是教者能抓住矛盾,因势利导,让学生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那么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不是更加丰富和深刻吗?抓住矛盾,因疑探文,是非常有教学魅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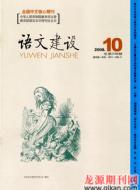
- 高考作文命题:在“变”与“不变”中寻求对策 / 高素英
- 2008年中考名言名句考查排行榜 / 熊雪佳
- 2008年中考作文:视野·困惑·出路 / 史绍典
- 平花·刷街·刷子 / 颜 萌 徐步军
- “裸”族新词:“裸退” / 邵长超
- 释“山寨” / 梁吉平 陈 丽
- “成心”与“存心” / 李小军 金木根
- “等”“等等”前标点的使用 / 隆 林
- “约会”使用情况调查 / 赵晓驰
- 对杜牧《江南春》被误读的再思考 / 孙桂平
- “汉末建安中”与《孔雀东南飞》 / 张庆民
- 非常状态下的写作 / 钱理群
- 美国麻省语文课程标准中的媒介标准分析与启示 / 张同杰
- 语文教学中的禁果效应 / 张 政
- 爱上诗 / 王洪旗
- 把感悟诗歌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 林喜杰
- 用什么指导课堂教学 / 黄国才
- 略读课文教学四问 / 施茂枝
- 倾听生命的呐喊 / 胡志金
- 正确认识鲁迅作品的语文教育价值 / 王栋生
- 平实地导向“元读” / 陈日亮
- 《再别康桥》教学实录 / 孟全波
- 《鸿门宴》教学设计 / 张 琳
- 《三峡》教学设计 / 林福才 陈海亮
- 也谈“文言文教学:行于‘文’‘言’之中” / 周保华
- 从助读系统和练习系统看教材编写的特点 / 张聪慧
- 论点摘编 / 佚名
- 教材文本资源与教学内容的确定 / 曹明海 赵宏亮
- 温故知新 / 饶杰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