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7期
ID: 356206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7期
ID: 356206
《归去来兮辞》二题
◇ 杨盛峰
《归去来兮辞》是隐逸诗人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前人推崇备至。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曰:“两晋无文章,幸独有《归去来辞》一篇耳。”现行人教版高二册语文选入此文,下面讨论一下有关的两个问题。
一、《归去来兮辞》的内容为已然还是设想?
粗略读过此文的读者大概会觉得这是一篇写实的文章。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在该篇的题解中写道:“本篇是作者辞去彭泽令后初到家时所作,写归家时的愉快心情和隐居的乐趣。”这个题解也让人觉得《归去来兮辞》是写实的。但从文章的写作时间来看,就会发现情况也许并不是这样。这篇辞的前边本有一段序(课本未选),序的结尾注明写作时间为“乙巳岁十一月”,也就是冬季辞官时;而辞中的一些内容却是写春天的:“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这说明写作时间在前,正文中的内容在后;换句话说,正文中的内容并不是写作时已然发生的事,而是作者想象中的情形。
其实,不仅春天里西畴的农事、丘壑的游历是想象中的事,就是初抵家时的愉悦也是想象中之事。序文中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怎么突然回去就会“有酒盈樽”了呢?这不过是作者想象中的家居生活罢了。
《宋书·陶潜传》对作者去职为文的情况说得很明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显然,《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之时的心志表白,小序记“不可谏”之“已往”,辞章赋“犹可追”之“来者”,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谓之为“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作者设想归程、设想抵家、设想涉园、设想耕田、设想丘壑游历、设想舒啸赋诗,把未来的事情写得历历在目,仿佛他已一一经历过,而让读者也误以为他在写实。
二、陶渊明设想中的田园生活是愉快而有乐趣的吗?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在《归去来兮辞》的题解中将其内容概括为“归家时的愉快心情和隐居的乐趣”,教参也将课文2、3两段内容概括为“写作者回到田园后的愉快生活”。但是,当我们反复品味这篇文章后,就会咀嚼出深深的苦涩与无奈。
1.生计问题
序中陈述:“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在举家生计艰难之中,陶渊明被迫为官,还希望“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但因不愿“折腰向乡里小人”而弃五斗米之俸,不久即辞官归去。当他再次回到“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的家中,他该怎样面对嗷嗷待哺的妻儿?生计问题始终是他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便在他高歌“归去来”时也决不会忘记这一点:“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他在“折腰”与辞官之间的选择并不轻松。
2.孤独
归去之后的陶渊明虽然有“童仆欢迎,稚子候门”的家庭之欢,有与亲戚情话、与农人往来的人情之乐,但他毕竟不完全属于那个环境,或者说他的精神、思想不可能一直沉浸在亲戚、农人的圈子里。“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二),他心中的理想是常人难以理解的;“抚孤松而盘桓”,“怀良辰以孤往”,“登东皋以舒啸”,他胸中的忧愁又能对谁诉说?
3.归隐之情与济世之志的矛盾
序言中既说“眷然有归欤之情”,又感慨“深愧平生之志”。陶渊明的“平生之志”是什么呢?“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读史述·屈贾》)他希望自己能做稷契一类人物,以济天下苍生。但是官场的黑暗腐朽让他无法忍受,深感“违己交病”,终于决定“归园田居”,过隐士生活。也就是说,隐并不是他的夙愿,而只是在对现实政治绝望之后的一种逃避,一种“独善其身”之道。这样,隐就与志发生了矛盾:“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
4.不知所归之惑
篇名曰“归去来兮”,其实作者最终还是感到不知所归。归园、归田、归林泉之后,生命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行到水穷处,“赋诗”“舒啸”之后又到哪里去?“感吾生之行休”,“聊乘化以归尽”,只有死路一条——这难道是他归去的最终结果吗?“乐夫天命复奚疑?”这分明充满了悲痛、充满了怀疑的结句,留下的是一个巨大的人生难题!
陶渊明无可奈何地归隐,虽然合乎他“性本爱丘山”的质性,但从物质的匮乏到精神的困惑带给他的是“终晓不能静”的悲戚,田园山水的愉悦恐怕是有限的。
[作者通联:陕西镇巴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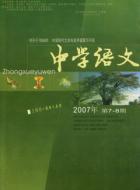
- 论语文教材编制的现代化 / 温立三
- 现代化视阈中口语交际教学的理论依托 / 李子华
-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渗透口语交际训练的研究 / 刘锦慧
- 梁启超语文审美教育思想浅析 / 程春梅
- 语文课程改革的现状与前瞻 / 胡根林
- 语文学习的阅读品质刍议 / 童县城
- 语文阅读技能评价的原则和方法 / 蔡正栋
- 自读课教学的四点思考 / 刘 祥
- 从阅读鉴赏到鉴赏表达 / 张希辉
- 语文书,学生记住了什么? / 余养健
- 个性化阅读的底线 / 吕茂峰 郑丽丽
- 关于“多元解读”的解读 / 曹胜娟
- 走出“前理解”的尴 / 曾令团
- 作文教学应贴近生活 / 李本华
- 怎样分析和感悟材料 / 魏永雅
- 让学生尽情“倾吐”的教学艺术 / 杨永钢
- 仿写与扩写在作文教学中的运用 / 鄢淑云
- 从矛盾的角度浅析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 陈文平
- 新课标下作文评价的发展性策略 / 王福生
- 新课改背景下高中作文评价构想及实践 / 张永飞
- 立足课 / 许晓红
- 枯寂与闲适:三重视界下的情感传达 / 王树文
- 胡屠户在塑造范进形象中的作用 / 张晓勇
- 文言文教学宜删繁就简 / 左培棣
- “剑”是怎么“铸”成的? / 王明建
- 《归去来兮辞》二题 / 杨盛峰
- 文学作品的错位解读 / 崔国明
- 赋情为 / 张静美
-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课堂实录与评点 / 余映潮 钟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