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7期
ID: 356191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7期
ID: 356191
个性化阅读的底线
◇ 吕茂峰 郑丽丽
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作为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之一,上述论断已经成为当下个性化阅读理论依据。充斥于各语文教学刊物的所谓个性化阅读的课例,却昭示出语文教师对这一论断缺乏理性评判。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当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与学生的独特体验产生冲突的时候,教师依仗着“反应多元”作后盾,置“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于不顾,使教学滑向了对学生所谓独特体验的无限尊重,甚至使教学滑向了严重脱离文本的胡编乱造。
请看一则教学案例①。
师:还有吗?小兄弟对这一往事是何态度呢?
生:他根本没忘当年往事。第9段这样说是为了不给我悔过的机会,不肯原谅我。做风筝这件事对于小兄弟来说是一辈子难以忘怀的。因为这风筝是他在小屋里偷偷做成的,却被我毁坏了,一定会深深印在心里。
师:(默许。)
生:我补充王欣的说法,当前社会上也有这样的人,明明深记着这件事,当别人来请罪时,故意说,有过这样的事吗?不记得了,其实他是从心底里不肯原谅对方。
师:(结合生活经验去分析人物形象,怎能否定这种看法?)
生:忘了,书中明确写着小兄弟忘了这件事,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师:(悦耳的童音在此回荡,以书为依据,可取。)
生:没忘,小兄弟不想原谅他,他的做法实在太粗暴了,他是在借爱弟弟之名,干虐杀之事。
师:(抓住兄长的行为作为论据。)
生:忘了,小兄弟非常天真,纯洁,不计较哥哥对自己的粗暴行为。
师:奥,锁住其本性。
生:没忘,小兄弟是非常善解人意,怕我的心里不好受,故意这样说。
师:原来是以真善美为契机。
生:忘了,小兄弟是很宽宏大量的,他‘大人不计小人过’。”
师:联接小兄弟的心灵美。
该课例的作者在课例的结尾有这样的感慨:他们的回答虽然与教师预设的答案——小兄弟是一个天真、可爱、聪明、健忘的受害者,也是一个精神麻木者——已越来越远;我的教学计划已无法顺利完成,但我仍然窃喜,因为已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小兄弟有了独特的见解,有了创造性的认识。
我们不否认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确实有很多时候是多元的。但这些多元的反应有的是率性而为的信口开河,有的是自主自觉地根据文本的综合框架而作的意义取舍,也有的是根据自身经验的即兴发挥,这样的多元反应我们都要统统予以尊重吗?上述课例中,学生对小兄弟到底有没有忘记精神被虐杀的往事这一问题所呈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两种答案,教师的任务是区分作者的所指和材料的能指,引导学生抓住文章的关键点,看谁的答案才是符合作者本义的。这样才能把学生的研读引向深入。如果以书为据肯定小兄弟已经忘记了往事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书中还有一句“无怨的恕,说谎罢了”又该如何理解呢?如果以兄长的行为太粗暴为由说小兄弟不会忘记往事值得肯定,那么不该忘记的事情却偏会忘记不正说明封建社会观念的群体落后和小兄弟的精神麻木吗?如果以生活经验为由肯定小兄弟不会忘记往事,那么个人都以自己生活经验取代作品的价值意义自说自话,创造固然是有了,但是,这还叫做阅读吗?
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而针对中小学生的课堂阅读“应该是学生吸纳词语、语料,积累言语范式,形成良好语感从而提高理解和运用民族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②。这决定了中小学生的课堂阅读基本上属于学习性阅读和接受性阅读,也同时决定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要受制于文本的既定框架,要受制于作者通过调控语言从材料本身生发的相对稳定的意义。如果超越了这条底线,任凭“多元个性”无边蔓延,就会导致语文课的变味和异化,就会造成新的混乱。
鼓励个性化阅读,应该严格区分作文教学和阅读教学对于语文材料的不同阅读要求。有则寓言说,一只猴子摘桃子,往前走,看见地里有西瓜,于是丢掉桃子抱西瓜;再往前走,看见一只兔子,于是又丢掉西瓜去追兔子,最后兔子也没有追到,猴子一无所获。对这则材料,从作文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批评猴子见异思迁以至劳而无功,也可以赞扬猴子永不满足、虽受挫而精神可嘉。如果作者通过对上下文语境控制,表达的是后者,而学生却置作者的语境控制于不顾,偏要根据自己经验认为作者表达的是前者,这是个性化地运用材料,跟我们所倡导的个性化阅读不可同日而语。
个性化阅读,主要是就文学作品而言的。而文学作品的意义绝大多数都是确定的,先在的。某些阐释语文课程标准的文章说“文本的意义不是先在的,确立的,而是在阅读过程中生成的”,其实这类文学作品是极少数的。这种阐释作为一种形象的说法,强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主观能动作用未尝不可,如果将它作为理论来指导我们的阅读教学就过头了。其实,即使是一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圆形”作品其意义也是相对确定的。像有着多元意义的散文《风筝》,有鲁迅的兄弟之情,有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有鲁迅的自省精神,有鲁迅对小兄弟深受“虐杀”却无缘恨得深沉感慨。专家的这些解读虽各个不同,各有侧重,但却绝不会彼此发生冲突。因为这些解读都是依据文本的。如果学生根据生活经验认为小兄弟说忘记的往事是为了不给哥哥悔过的机会,因而作品也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就缺乏文本的依据。
尊重学生独特体验,不是廉价的认同和赞赏,而是要重视,要严肃对待,要以学生的独特体验作为条件和起点,借助文本,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发挥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深广的影响作用。所以当学生的独特体验与作者的生活体验发生冲突的时候,教师有责任引导学生深研文本,循路识真,使学生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又扩展其间接的生活经验,而不是一味地让学生的独特体验“篡位”,凌驾于作者和作品的意义架构之上。
就中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而言,个性化阅读的意义主要在于借助上下文互相注释、互相说明的语言环境,借助经验和想象,添补作品的空白点,。如林海音《爸爸的花儿落了》,作者开头讲,爸爸病倒了,后文没有直接交待爸爸的病情,这对读者来说,就是空白点,这一空白点,读者就可以凭着老高说了半截的话、爸爸护理花的情节以及文章结尾“爸爸的花儿落了”的委婉语等,判定爸爸去世了。这里的判定,也有生活经验的介入,只有这种与作品相容的生活经验对解读文章才是有效的。爸爸去世,“我”的心情怎样?作品也没有明示,这同样是空白点。有的学生能根据作者特别点出告诉“我”消息的老高是“缺了一根手指头”的厨子老高,想象失父之痛如同人失去手指一样难受填补这一空白。而有的学生却根据这一信息想象老高一定是因为非常着急才把应该掩饰起来的断指露了出来。这匪夷所思的想象尽管比前者要曲折的多,但却背离了上下文语境对意义的控制。续写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很多学生想象皇帝会严惩两名骗子,虽愿望良好,却没有抓住作者所揭露的生活本质。有人把这种脱离文本的“创造”称作是“无中生有式创造性阅读”,而把依据文本的想象创造称作“有上生新式创造性阅读”③。我们认为,语文教学的个性化阅读,应该是“有上生新式创造性阅读”,而“无中生有式创造性阅读”则与文学作品的个性化阅读关系不大。
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作为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之一,上述论断已经成为当下个性化阅读理论依据。充斥于各语文教学刊物的所谓个性化阅读的课例,却昭示出语文教师对这一论断缺乏理性评判。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当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与学生的独特体验产生冲突的时候,教师依仗着“反应多元”作后盾,置“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于不顾,使教学滑向了对学生所谓独特体验的无限尊重,甚至使教学滑向了严重脱离文本的胡编乱造。
请看一则教学案例①。
师:还有吗?小兄弟对这一往事是何态度呢?
生:他根本没忘当年往事。第9段这样说是为了不给我悔过的机会,不肯原谅我。做风筝这件事对于小兄弟来说是一辈子难以忘怀的。因为这风筝是他在小屋里偷偷做成的,却被我毁坏了,一定会深深印在心里。
师:(默许。)
生:我补充王欣的说法,当前社会上也有这样的人,明明深记着这件事,当别人来请罪时,故意说,有过这样的事吗?不记得了,其实他是从心底里不肯原谅对方。
师:(结合生活经验去分析人物形象,怎能否定这种看法?)
生:忘了,书中明确写着小兄弟忘了这件事,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师:(悦耳的童音在此回荡,以书为依据,可取。)
生:没忘,小兄弟不想原谅他,他的做法实在太粗暴了,他是在借爱弟弟之名,干虐杀之事。
师:(抓住兄长的行为作为论据。)
生:忘了,小兄弟非常天真,纯洁,不计较哥哥对自己的粗暴行为。
师:奥,锁住其本性。
生:没忘,小兄弟是非常善解人意,怕我的心里不好受,故意这样说。
师:原来是以真善美为契机。
生:忘了,小兄弟是很宽宏大量的,他‘大人不计小人过’。”
师:联接小兄弟的心灵美。
该课例的作者在课例的结尾有这样的感慨:他们的回答虽然与教师预设的答案——小兄弟是一个天真、可爱、聪明、健忘的受害者,也是一个精神麻木者——已越来越远;我的教学计划已无法顺利完成,但我仍然窃喜,因为已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小兄弟有了独特的见解,有了创造性的认识。
我们不否认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确实有很多时候是多元的。但这些多元的反应有的是率性而为的信口开河,有的是自主自觉地根据文本的综合框架而作的意义取舍,也有的是根据自身经验的即兴发挥,这样的多元反应我们都要统统予以尊重吗?上述课例中,学生对小兄弟到底有没有忘记精神被虐杀的往事这一问题所呈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两种答案,教师的任务是区分作者的所指和材料的能指,引导学生抓住文章的关键点,看谁的答案才是符合作者本义的。这样才能把学生的研读引向深入。如果以书为据肯定小兄弟已经忘记了往事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书中还有一句“无怨的恕,说谎罢了”又该如何理解呢?如果以兄长的行为太粗暴为由说小兄弟不会忘记往事值得肯定,那么不该忘记的事情却偏会忘记不正说明封建社会观念的群体落后和小兄弟的精神麻木吗?如果以生活经验为由肯定小兄弟不会忘记往事,那么个人都以自己生活经验取代作品的价值意义自说自话,创造固然是有了,但是,这还叫做阅读吗?
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而针对中小学生的课堂阅读“应该是学生吸纳词语、语料,积累言语范式,形成良好语感从而提高理解和运用民族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②。这决定了中小学生的课堂阅读基本上属于学习性阅读和接受性阅读,也同时决定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要受制于文本的既定框架,要受制于作者通过调控语言从材料本身生发的相对稳定的意义。如果超越了这条底线,任凭“多元个性”无边蔓延,就会导致语文课的变味和异化,就会造成新的混乱。
鼓励个性化阅读,应该严格区分作文教学和阅读教学对于语文材料的不同阅读要求。有则寓言说,一只猴子摘桃子,往前走,看见地里有西瓜,于是丢掉桃子抱西瓜;再往前走,看见一只兔子,于是又丢掉西瓜去追兔子,最后兔子也没有追到,猴子一无所获。对这则材料,从作文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批评猴子见异思迁以至劳而无功,也可以赞扬猴子永不满足、虽受挫而精神可嘉。如果作者通过对上下文语境控制,表达的是后者,而学生却置作者的语境控制于不顾,偏要根据自己经验认为作者表达的是前者,这是个性化地运用材料,跟我们所倡导的个性化阅读不可同日而语。
个性化阅读,主要是就文学作品而言的。而文学作品的意义绝大多数都是确定的,先在的。某些阐释语文课程标准的文章说“文本的意义不是先在的,确立的,而是在阅读过程中生成的”,其实这类文学作品是极少数的。这种阐释作为一种形象的说法,强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主观能动作用未尝不可,如果将它作为理论来指导我们的阅读教学就过头了。其实,即使是一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圆形”作品其意义也是相对确定的。像有着多元意义的散文《风筝》,有鲁迅的兄弟之情,有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有鲁迅的自省精神,有鲁迅对小兄弟深受“虐杀”却无缘恨得深沉感慨。专家的这些解读虽各个不同,各有侧重,但却绝不会彼此发生冲突。因为这些解读都是依据文本的。如果学生根据生活经验认为小兄弟说忘记的往事是为了不给哥哥悔过的机会,因而作品也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就缺乏文本的依据。
尊重学生独特体验,不是廉价的认同和赞赏,而是要重视,要严肃对待,要以学生的独特体验作为条件和起点,借助文本,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发挥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深广的影响作用。所以当学生的独特体验与作者的生活体验发生冲突的时候,教师有责任引导学生深研文本,循路识真,使学生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又扩展其间接的生活经验,而不是一味地让学生的独特体验“篡位”,凌驾于作者和作品的意义架构之上。
就中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而言,个性化阅读的意义主要在于借助上下文互相注释、互相说明的语言环境,借助经验和想象,添补作品的空白点,。如林海音《爸爸的花儿落了》,作者开头讲,爸爸病倒了,后文没有直接交待爸爸的病情,这对读者来说,就是空白点,这一空白点,读者就可以凭着老高说了半截的话、爸爸护理花的情节以及文章结尾“爸爸的花儿落了”的委婉语等,判定爸爸去世了。这里的判定,也有生活经验的介入,只有这种与作品相容的生活经验对解读文章才是有效的。爸爸去世,“我”的心情怎样?作品也没有明示,这同样是空白点。有的学生能根据作者特别点出告诉“我”消息的老高是“缺了一根手指头”的厨子老高,想象失父之痛如同人失去手指一样难受填补这一空白。而有的学生却根据这一信息想象老高一定是因为非常着急才把应该掩饰起来的断指露了出来。这匪夷所思的想象尽管比前者要曲折的多,但却背离了上下文语境对意义的控制。续写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很多学生想象皇帝会严惩两名骗子,虽愿望良好,却没有抓住作者所揭露的生活本质。有人把这种脱离文本的“创造”称作是“无中生有式创造性阅读”,而把依据文本的想象创造称作“有上生新式创造性阅读”③。我们认为,语文教学的个性化阅读,应该是“有上生新式创造性阅读”,而“无中生有式创造性阅读”则与文学作品的个性化阅读关系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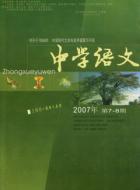
- 论语文教材编制的现代化 / 温立三
- 现代化视阈中口语交际教学的理论依托 / 李子华
-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渗透口语交际训练的研究 / 刘锦慧
- 梁启超语文审美教育思想浅析 / 程春梅
- 语文课程改革的现状与前瞻 / 胡根林
- 语文学习的阅读品质刍议 / 童县城
- 语文阅读技能评价的原则和方法 / 蔡正栋
- 自读课教学的四点思考 / 刘 祥
- 从阅读鉴赏到鉴赏表达 / 张希辉
- 语文书,学生记住了什么? / 余养健
- 个性化阅读的底线 / 吕茂峰 郑丽丽
- 关于“多元解读”的解读 / 曹胜娟
- 走出“前理解”的尴 / 曾令团
- 作文教学应贴近生活 / 李本华
- 怎样分析和感悟材料 / 魏永雅
- 让学生尽情“倾吐”的教学艺术 / 杨永钢
- 仿写与扩写在作文教学中的运用 / 鄢淑云
- 从矛盾的角度浅析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 陈文平
- 新课标下作文评价的发展性策略 / 王福生
- 新课改背景下高中作文评价构想及实践 / 张永飞
- 立足课 / 许晓红
- 枯寂与闲适:三重视界下的情感传达 / 王树文
- 胡屠户在塑造范进形象中的作用 / 张晓勇
- 文言文教学宜删繁就简 / 左培棣
- “剑”是怎么“铸”成的? / 王明建
- 《归去来兮辞》二题 / 杨盛峰
- 文学作品的错位解读 / 崔国明
- 赋情为 / 张静美
-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课堂实录与评点 / 余映潮 钟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