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7期
ID: 356202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7期
ID: 356202
枯寂与闲适:三重视界下的情感传达
◇ 王树文
《约客》是南宋被称为“永嘉四灵”之一的赵师秀(1170—1219)的传世名作,谢枋得《千家诗》题为《有约》,《宋诗纪事》称作《绝句》,素以写景清新明了,体物精细,抒情含蓄而余味深长著称。
通过仔细阅读本诗,我们可以发现,在短短28字的描绘中,《约客》实际上包含了三个世界:室外、室内和诗人的内心世界。在诗中,这三个世界本来是浑然一体的,我们在这里把它们分开来讲,考虑的主要是分析的方便明了,而绝不是对其进行肢解,并且在分析过程中也会时刻关注到这三者之间的联系。下面我们就以这三个世界为框架,以前人的批评为依据,来对它进行细读式批评。
一、叠意与喧闹:室外世界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这句是描写的窗外环境,因其寥寥两句就极其传神地描绘了江南初夏景色,颇具特色,因而倍受称赞。胡仔曾说:“‘梨花一枝春带雨’,‘桃花乱落如红雨’,‘小院深沉杏花雨’,‘黄梅时节家家雨’皆古今诗词之警句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但这个名句却不是作者偶思得之,而是在前人基础上的翻新。江南春末夏初,梅子黄熟季节,阴雨连绵,叫“黄梅雨”,或“梅雨”。诗人对此多有描写。可以说,“梅雨”、“青草”、“池塘”、“蛙声”这都是在古典诗词中被广泛应用的意象。《柳溪诗话》评说此诗“意虽腐而语新”颇为中的。“意腐”指的是“梅雨”“青草”“池塘”和“蛙声”在此之前的古典诗词中,都是被广泛运用的意象,如“三春日日黄梅雨,孤客年年青草湖”(韩偓),“杜鹃啼出血成花,梅子黄时雨如雾”(寇准),“水国春深梅子雨”(唐庚),“前山后山梅子雨”(范成大)等,赵师秀则说“黄梅时节家家雨”。“家家雨”,写家家户户都被烟雨笼罩着,也是极言雨水很多,到处都是。由于雨水充足,因而青草茂盛,池塘水满,青蛙就长得更快,叫得更欢。宋人因此又写有“池塘夜雨听蛙鸣”(黄庭坚《病起次韵和稚川进叔倡酬之什》),“池塘水满蛙成市(方岳《农谣》),“草根肥水噪新蛙”(周密《野步》)。如果说上面所列举的那些诗句对赵师秀来说只是意象的启发的话,那么对于“低帘闲幕家家雨,淡淡园林处处花”(吕本中《春晚郊居》)就是直接的句法套用了。在这么多著名的诗句面前,要想打破读者的阅读预设就必须推陈出新而不落窠臼。那么作者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下面试图从微观的角度对其加以剖析。
首先是叠字的运用。“家家”和“处处”两个叠字的运用,在这里起到了两个作用:(一)表明“蛙声”、“雨声”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更突出了室外世界的喧闹程度,与下文室内的静形成了更加强烈的对比。(二)情韵倍增,诗味愈浓。本来黄梅时节雨的特征,就是连绵不断,与盛夏“东边日出西边雨”大不相同,青草池塘的青蛙的叫声,从来不是只有一处,这些是人们都知道的。但诗人却偏偏说这是“家家雨”、“处处蛙”,这样就把江南水乡梅雨时节的气候景物渲染地愈加浓醇了。
其次,这两句不是简单的为写景而写景,而是景中寓情,使得上下文浑然一体。联系下面两句“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及题目“约客”,我们可以知道原来作者是在等一位朋友,他关注屋外世界主要也是在眺望故人身影,倾听其走来的脚步声。这样就超出了单独景物描写的局限,兼而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作者等待友人的迫切心情。而“家家雨”却又有暗示友人有可能为雨所阻隔,不能前来赴约的隐含之意,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那么,为如此喧闹的室外景致所环绕的室内又是如何一番景象呢?
二、静寂与雅致:室内世界
前两句从室外之景着笔,以听觉写雨声蛙声,说明诗人此时正在等待友人来临因此对室外动静特别关注。不过这满耳的雨声蛙声中,并没有友人光临的迹象。于是诗人不免失望,不免心绪不宁,于是第三句就点明失望,视线转到室内。“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与屋外比较喧闹的世界相比,屋内却完全是一片静的世界。
首先,作者约客的目的是来下棋,而棋本身就是一种很高雅的文人游戏,所谓“琴棋书画”,不会是喧闹的。而邀约的客人却又并未到来,只有作者一个人,而更显其静,或者甚而至于会有些冷清孤独的感觉。
其次,是这种静却又是动中之静,动的最突出的表现就在“敲”与“落”两字。陆机说:“课虚无而责有,叩寂寞以求音。”作者为了突出室内的静,就采取了这种以动写静的手法,因棋声而写夜之静,因灯花落而现体物之细。诗中的这些声音、活动,既加深了静的氛围,又非于静中不可得。这是灵动的静,不只是物的静,更是心灵的静。经由它传达出的心境,是寂寞?是愉悦?无从分明。
读这两句诗时,我们似乎能听到棋子“丁丁”的轻响,看到灯花悄然落下。这和室外的喧闹相比,分明是两重天。
上面做了对室外的“闹”和室内的“静”做了具体的分析,处于对比分明环境中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又会是怎样的呢?
三、枯寂与超然:内心世界
这首诗借环境表现人物的心情的描写上,与一般的同样方式的诗是不同的,它并不只是以冷清的环境表现枯寂,以喧动的气氛表示不安,而是让这两种气氛同时存在借以形成一种既对立有统一的特殊的艺术氛围。于是,环境的复杂性也就造成了人的心境的复杂性和多解的可能性。所以对于作者的内心世界,历来存在着争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关于作者当时心境的看法主要有两种:
1.表现了一种枯寂无聊的心情
作者的心境主要是通过“闲”、“敲”、“落”三个字表现出来的。直接出现在诗中的“闲”是与“敲”字连在一起的,表现的是一种百无聊赖的枯闲。为什么说是百无聊赖的枯闲呢?让我们回到本文。作者约客,而客人爽约,自己却一直在等,直等到夜半,这固然表现了自己的重约和对朋友的友情,但这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却是表现了自己心情的“空闲”。正是为了解闲,才约朋友来会面,可是朋友却偏偏没有来,这不是旧闲不去反添新愁吗?因闲而愁,因愁而寂,此时诗人的处境和心情不难想见了。再看“闲”与“落”。若非闲而至极,安能关注到此无声无息之灯花飘落。唐代王维有《鸟鸣涧》一诗,其中有“人闲桂花落”句,很为人称道。我们可以拿它来与此句做比较阅读。其中人皆“闲”;物,一“灯花”,一“桂花”,其落声都轻而不可闻,可又都能为作者灵敏的感知所清晰地捕捉到。外界的细微变动正因内心之“闲”而悟得,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闲”一“敲”一“落”三字,体物精细,状人传神,不言寂寞,而寂寞尽在其中矣。
我们还可以试着从诗的后面倒着读到前面,再从前面顺着读到后面,我们就会发现,诗中所表现的诗人的寂寞是一条曲折迂回的圆,圆心是“闲”,而周围是顺着“因雨而空闲——因空闲而因朋友来解闲——朋友不至反而心情更荒闲——因荒闲至极而枯寂”①这样的轨迹。读之,一种缠绵反复、割而不断的闲情愁绪,极自然的撩动着读者的心弦。
北宋初郑文宝亦有《爽约》诗:“吟绕虚廊更向阑,绣窗灯影背栏干。燕栖莺宿无人语,一夜萧萧细雨寒。”意境与此类似,也是等候约客不至的的失望,凄清寂寞。“相比之下,似不及赵师秀此诗这么精警而馀意深长。”②个中原因就是与之相比较,《约客》含义更为丰富。郑诗至凄清寂寞意已尽,而《约客》却还完全可以作第二种解读。
2.表现了一种超然的闲适
我们从“不来”、“夜半”和“落灯花”可以看出诗人知道要约的“客”是不会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从当时的时间看。因为“夜半”说明夜已很深,应该远远超出了约定的时间;第二,从“灯花”这个意象看。所谓“灯花”就是,古时用油灯,灯芯燃烧时结成的花状物,叫灯花。在文学上多用来指代喜事或者有客人要来。现在说灯花已经落了,意思也就是表明客人不会再来了。
那既然已经如此,为什么作者还不去休息,却“闲敲棋子”看灯花落呢?我们从诗文可以看出,诗人邀客人来的目的是下棋,而下棋本身就是一种高雅的文人游戏,表现着一种静谧的氛围。客人最终没有来,但静谧的氛围却已经为作者所得,或者可以说此时他已经不是在单纯的等待,而是转为主动地享受这只属于自己的静夜。在这里最突出的就是,一个“闲”字使全诗的顿时节奏很自然地舒缓下来。此时,四周传来的传来的蛙鸣、雨声和室内轻扣棋子的声响似乎打破了深夜的寂静,又似乎增加了深夜的寂静,正所谓“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时,对于主人公来说,等与不等的界限已开始变得模糊,功利性的等待逐渐被无目的的审美享受所取代,从而与整个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道家所谓的“心斋”、“坐忘”和“丧我”即是指此等物我两忘的境界。
通过上面对主人公内心的世界所做的两种不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诗的情感是比较朦胧的,想象是比较不确定的。古人云,“诗无达诂”,也就是说,诗歌是没有唯一正确的阐释的。而一首“好诗,不但要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而且对有不同的个性和经历,不同的文化背景、心理特点的读者,可以调动起不同的经验,完成诗的想象”③。以上两种解释都是立足与文本,在本文允许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上面所提到的两种解读方法都是各自成立的。
结语:让我们再从整体观察这首诗,探讨三重视界下的情感传达,对诗中所包含的三个世界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首诗的独到之处就在于运用普通意象而独抒新意,密切注意情与景的和谐交融,从而达到一种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独特审美效果。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称其“意境浑融”,“生活气息较浓,又摆脱了雕琢之习,清丽可诵”④。实在是当之无愧了。
注释:
①陈友冰、杨福生:《宋代绝句赏析》,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09—310页。
②张鸣:《宋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③孙绍振:《文学性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④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205页。
[作者通联: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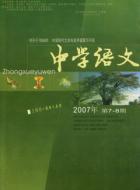
- 论语文教材编制的现代化 / 温立三
- 现代化视阈中口语交际教学的理论依托 / 李子华
-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渗透口语交际训练的研究 / 刘锦慧
- 梁启超语文审美教育思想浅析 / 程春梅
- 语文课程改革的现状与前瞻 / 胡根林
- 语文学习的阅读品质刍议 / 童县城
- 语文阅读技能评价的原则和方法 / 蔡正栋
- 自读课教学的四点思考 / 刘 祥
- 从阅读鉴赏到鉴赏表达 / 张希辉
- 语文书,学生记住了什么? / 余养健
- 个性化阅读的底线 / 吕茂峰 郑丽丽
- 关于“多元解读”的解读 / 曹胜娟
- 走出“前理解”的尴 / 曾令团
- 作文教学应贴近生活 / 李本华
- 怎样分析和感悟材料 / 魏永雅
- 让学生尽情“倾吐”的教学艺术 / 杨永钢
- 仿写与扩写在作文教学中的运用 / 鄢淑云
- 从矛盾的角度浅析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 陈文平
- 新课标下作文评价的发展性策略 / 王福生
- 新课改背景下高中作文评价构想及实践 / 张永飞
- 立足课 / 许晓红
- 枯寂与闲适:三重视界下的情感传达 / 王树文
- 胡屠户在塑造范进形象中的作用 / 张晓勇
- 文言文教学宜删繁就简 / 左培棣
- “剑”是怎么“铸”成的? / 王明建
- 《归去来兮辞》二题 / 杨盛峰
- 文学作品的错位解读 / 崔国明
- 赋情为 / 张静美
-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课堂实录与评点 / 余映潮 钟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