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4期
ID: 356092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4期
ID: 356092
英雄最后的独舞
◇ 倪 岗
许多老师在设计《斑羚飞渡》的教学时常常把重点放在中间部分的“怎样飞渡”上。其实,《斑羚飞渡》一文最具有诗意最耐人寻味的应该是结尾部分。文不长,照录如下:
最后伤心崖上只剩下那只成功地指挥了这群斑羚集体飞渡的镰刀头羊。它孤零零地站在山峰上,既没有年轻斑羚需要它做空中垫脚石飞到对岸去,也没有谁来帮它飞渡。只见它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那道绚丽的彩虹。弯弯的彩虹一头连着伤心崖,一头连着对岸的山峰,像一座美丽的桥。它走了上去,消失在一片灿烂中。
试想,崖上最后只剩下头羊,这难道是碰巧吗?如果真是双数,就算做“垫脚石”,那也只是重复了前面飞渡的场面,让人索然寡味。如果头羊先做了“垫脚石”,最后剩下的是另一只斑羚,真不知道该怎样收场。而作者巧妙设计使头羊最后落入“既没有年轻斑羚需要它做空中垫脚石飞到对岸去,也没有谁来帮它飞渡”的“孤零零”的绝境。头羊是在从容指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以死换生”的大逃亡后陷入“孤零零”的尴尬。这时,从羊自身而论它已经彻底无用。而正是在这“无用”中升华出了令人荡气回肠的“大用”。在英雄般的集体群舞——群羊生死飞渡的场面不断冲击着旁观者和读者后,紧接着更震撼人心的是头羊在生死线上自由的独舞——它以自戕完成对人类的反抗。于是,“孤零零”的头羊迅速将文章推向高潮——慢镜头幻化这位精神领袖的崇高壮美。至此,完成了英雄的升华。这正如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所言:“英雄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击败。”足见作者“无用之用才是大用”的审美匠心。
其次,作者这样描写头羊跳崖:“它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那道绚丽的彩虹。”“它走了上去,消失在一片灿烂中。”无独有偶,之前文章的第三段恰好也有段老斑羚跳崖的描写:“在离对面山峰还有一米多的空中哀咩一声,像颗流星似的笔直坠落下去,好一会儿,悬崖下才传来扑通的落水声。”除了哀咩声外,实际上两者的情景应该是一样的。但作者的描写却大相径庭。其实老羚羊的跳崖才符合真实,而对头羊近似神话般的描写更多的是对真实的变异。作者借助了彩虹完成了变异,使读者产生强烈的震撼力,形成了审美的快感。此时如果真实一描写,直面残忍的现实,反而破坏了文章的和谐美、崇高美、艺术美。
现实要变异,才能获得诗性或诗意效果。也正因为变异,读者才更能明晰,更深切地感受到导致这种变异的情感的强度和深度。变异后可能并不符合“事实真实”,却更符合“心理真实”,反映了人们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
类似这种情感导致对真实的变异手法,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台湾作家陈启佑在《永远的蝴蝶》中这样描写未婚妻被车撞死的场面:“随着一阵拔尖的煞车声。樱子的一身轻轻的飞了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冷的街面,好像一只夜晚的蝴蝶。”哀婉的化蝶,淡化了血腥味,更诗意,感情也更浓烈。
课文在结尾处戛然而止,意味深长。“走了上去”以后呢?猎人会是什么反应?只字不提。其实,此时语言的力量是苍白的。不着一字,给人留白,反而让人玩味不已。空白之美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感受注入作品,参与作品的完成。当然,也要求读者能于无声处听出乐音、于无形无色处观得画意、于无字处悟出诗境。这就是文学艺术最美妙的境界。最后的场景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含蓄隽永犹如一幅古典的山水画。
在那美丽彩虹做背景的舞台上,残酷的现实和美好的梦想交织,绚烂与悲怆辉映,一个智慧果断、从容沉着的英雄——镰刀头羊,独舞于彩虹之上,独舞于心灵之中,情感与形象水乳交融,尽得风流。如繁急的琵琶,在铮铮作响的最高亢处绝响,留给人怔怔的回味和袅袅余韵。
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雅克布森曾说:“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同样,文学作品的教学必须尽可能挖掘其中的诗性,才能尽显文学之美。
[作者通联:广东深圳宝安区教科培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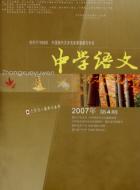
- 语文教师有必要了解叶圣陶 / 徐龙年
- 传统语文教学“批评热”中的理性思考 / 孙建军
- 审丑:缺失的话语方式 / 刘德海
- 语文教师要创造性的使用教材 / 杨益民
- 怎样教学“问题探讨”类课文 / 华德阳 卢士国
- 有一种阅读叫细读 / 杜长明
- 追寻诗性的教学 / 余 萍
- 农村写作教学资源开发摭谈 / 王加武
- 故事,想说“新编”不容易 / 石修银
- 幸福与痛苦的较量 / 周长生
- 英雄最后的独舞 / 倪 岗
- 一首精神家园的恋歌 / 冷占平
- “抄检”闹剧与角色错位 / 李兴茂
- 《口技》教学实录 / 余映潮 李 光 陈玲玲
- 谈多媒体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 王瑞华
- 古诗鉴赏应教给学生程序性知识 / 姚尚春
- 《项脊轩志》中容易被忽视的两处细节描写 / 王经军
- 课文学习的多向延伸 / 张慧蘋
- 警惕:“主题”标签让学生表达能力窒息 / 郭家海
- 高效“课堂讨论”三招 / 李 骥
- 新课标初中语文九年级(上)第六单元教案 / 毛以斌 余映潮
- 试说新词二则 / 郝媛媛
- 《触龙说赵太后》中的注释和翻译疑难剖析 / 刘精盛
- 高考诗歌鉴赏命题角度例析 / 王学华
- 为文“画龙”需“点睛” / 周 新
- 科技文阅读的设题特点与答题技巧指津 / 王建明
- 文言语句翻译题的命题思路及解题技巧探微 / 朱学明
- 命制中考语文“综合性学习”试题的相关探索与实践 / 黄 霞
- 中美语文教材之比较 / 高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