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11年第7期
ID: 146801
语文教学之友 2011年第7期
ID: 146801
《孔雀东南飞》二题
◇ 张怡春
一、兰芝再聘体现了中国式浪漫与幽默
刘兰芝被婆婆焦母硬生生休回家,“还家十余日”后先后就有县令和太守派人来替各自的儿子提亲,这正像刘兄所言,“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真的让人目瞪口呆。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读高中时疑惑过,后来教这篇课文时一届一届的学生也这么问我:既然兰芝这么的好,为什么在嫁小吏焦仲卿之前就没有大官(比如县令、太守之类)家来提亲呢?反而现在却这么走俏呢?实在有点不近人情、不合常理。
其实,这种写法是中国民间文学惯用的技法,是为了取得衬托作用,却不能对事情本身过多纠缠的。铺陈排比,将老百姓心中所能有的理想全聚集在一个人物身上,以此来实现现实当中不可能实现的追求,求得生活的甜头,这就是中国式老百姓的浪漫与幽默,是带泪的笑,是凄苦的理想之美。《孔雀东南飞》是这样,《陌上桑》也是这样,所谓“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根本就是老百姓的一种理想,以想象的美来抵挡和掩饰现实生活的无奈,从而求得心理平衡。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一个十分能隐忍的民族,与这种民族心理不无关系。再苦再难的处境,中国老百姓都能想办法轻轻遮掩过去,而在自己设计的内心乐土中尽情享受。这就是这种技法之所以为中国老百姓惯用的心理根源。当然,它有(强烈的)衬托作用,能反映出老百姓的好恶情感,能更好地表现主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人活在世上其实是不怎么自由的,社会的运转总得有它既定的规矩,所以人的理想其实有时候很难实现。焦、刘爱情理想就碰到了现实的尴尬,“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礼记》)。父母有权任意让儿子休妻,在这种既有体制之下,一般人是无可奈何的。焦母、刘母、刘兄遵循封建礼教,按封建礼教办事,其实焦仲卿、刘兰芝骨子里何尝不是如此?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但焦、刘爱情悲剧又是值得同情的,人们内心里是潜藏着追求爱情自由幸福的种子的,所以就只好这么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同情,委婉地批评焦母、刘母和刘兄的行为。我们只要认真读一下兰芝临出焦家门前精心打扮,兰芝被休回家,县令、太守派人求婚以及结尾焦、刘两家求合葬那几段文字,就不难发现,人们之所以要这么写,要这么铺陈排比,其实就是在平衡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反映的就是这种中国老百姓式的浪漫与幽默。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不论什么事都那么地喜欢大团圆式结局了。
二、焦、刘为何不私奔
每次教《孔雀东南飞》,学生们总会为焦、刘爱情悲剧扼腕叹惜,总会热心而急切地为他们出主意:前辈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不是早就做出榜样了吗?焦、刘为什么就不这样做呢?私奔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待到焦母哪天回心转意了,夫妻双双不就可以把家还了吗?办法总比困难多啊,他们为什么就一定要去双双殉情呢?
应该说,私奔的办法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要看哪样的人。刘兰芝有这种可能,她“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因袭的社会束缚不会太多,况且性格也较焦仲卿刚烈坚强得多,做事果断得多。但焦仲卿就不同了,作为本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的他来说,因袭的东西太多,性格远较兰芝懦弱。这一点我们从诗中可以完全看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就不同。司马相如很主动、很大胆,以琴挑卓文君;而新寡的卓文君也一样大胆。这样,两人一拍即合,说走就走了,干脆利落得很。这种事其实要的就是这种干脆利落劲儿,是犹豫不得的,一犹豫就没戏了。这样看来,焦、刘私奔的关键其实在焦仲卿这儿,而焦仲卿则太缺乏私奔的胆识和勇气,他压根儿就不是司马相如似的男人!
当然,作为独子的焦仲卿也是有难言之隐的。自己一走,老母咋办?孝道可是中华传统美德,弃母而去、与人私奔这种事,懦弱的焦仲卿是绝对干不出来的。即使他这么做了,那么这件事也就绝不会如双双殉情那样得到人们的普遍同情了,因为当时的人们还是固守封建道统的,司马相如、卓文君的举动不就引来过一些人的微词吗?况且,焦仲卿对母亲是抱有希望的,你看他一再对兰芝说,“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死不相负!”这些话一方面反映出了他对兰芝的真挚情感,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母亲的幻想,幻想母亲最后能回心转意,准许自己接回兰芝。他最后之所以选择殉情,“故作不良计”,“令母在后单”,实在只是看到母亲回心转意无望而自己又实在割舍不了与兰芝的真挚情感,是迫不得已的下下之策。有人说焦仲卿既然有死的勇气,怎么就没有私奔的勇气呢?其实对懦弱的焦仲卿来说,在做不通母亲思想工作、母亲始终不松口的情况之下,死倒是一种最好的解脱,是坚守与兰芝坚贞爱情的最好的也是惟一的办法,而私奔对他来说则是一种罪过,绝不是他这种家庭出身和懦弱性格的人所能做得出来的。他终究只是个小吏,不是司马相如那样的大文人。汉魏六朝的文人特别是有点名气的文人,那是很通脱潇洒的,所谓魏晋风度,他们是常常能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反常的事情来的。而焦仲卿不行,他不是那样的文人,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懦弱的小吏而已,所以想要他能有司马相如一样的表现,只能是白日梦。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举动不是社会常态,而焦、刘的处境和思想认识则是社会常态,代表了一般人的共性,尽管他们最后双双殉情的举动超出了常人(一般人自然是屈服于社会,不会选择死,只会选择离),但总的来说还是符合一般人的思想行为的,所以他们的爱情悲剧就更能得到一般人的同情。
人的个性受到环境的制约,人的个性又制约着人的行为。焦仲卿不选择私奔而选择殉情,是与他的个性相符的,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作者单位:隆回县第二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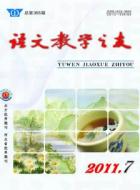
- 语文教学中培养直觉思维的特殊意义 / 杨泉良
- 关于教师之角色的思考 / 任道华
- 语文教学需体现文体特征 / 张兵
- “情”之所至 金石为开 / 刘伟娟
- 年少时让我们学习爱情 / 唐艳丹
- 语文教材应该有一定的娱乐性 / 赵爱琴
- 初中语文教科书范文也应择时编排 / 赵振文
- 浅谈朗读教学中“三种境界”的追求和营造 / 王卫然
- 语文课中的“韵味”语词教学 / 倪燕
- 浅谈名著阅读指导的有效性 / 叶国炎
- 例谈高中文言文阅读教学的五个层次 / 张正平
- 初中语文预习案的编写与使用 / 陈涛
- 辨象寻味 以味论诗 / 李超群
- 《咏雪》中的现代教育理念 / 刘凡保
- “习”是 “复习”吗 / 姜永国
- 三“解”《庖丁解牛》 / 张素梅
- “老先生”是谁 / 王静贤
- “五柳先生”应该怎么喝酒 / 孙志强
- 高水平的观众方显高水平的演唱 / 杨一成
- 运用之妙 细细思量 / 高传利
- 关于《林黛玉进贾府》的几点思考 / 牛蕾 胡建华
- 谈谈《最后一课》的爱国情韵 / 施长华
- 赫留金:一个可恨又可怜的小人物 / 何显强 邹金平
- “借书满架”之“借” / 陈开毅
- “曾”字究竟该读何音 / 文喜东
- 称呼之中显个性 / 欧阳振有
- 《孔雀东南飞》二题 / 张怡春
- 文本阅读与写作教学联姻之“四步法” / 俞申杰
- 管窥新课改下作文教学的系统性缺失 / 黄义飞
- 误读造成的悲剧 / 戴秀琴
- 桃花依旧笑春风 / 桑进林
- 切莫小觑秦武阳 / 杨卫东
- 命题作文的审题该审出什么 / 严爱军
- 抓住几组关系提高阅读质量 / 唐仲开
- 抓住切入点 轻松解诗歌 / 史宏升
- 作文卷面切不可小觑 / 白守双
- 句号的书写形式应该规范统一 / 袁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