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6期
ID: 136232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6期
ID: 136232
如何依据文本体式确定阅读教学内容
◇ 步 进
主持人简介:王荣生,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学科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执行主持简介:胡根林,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博士,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09年,以王荣生先生及其团队为主的语文教育工作者继续大力倡导和致力于有关语文教学内容的研究,研究呈现出逐渐深化的趋势。“这体现在:从探讨一节课的教学内容,到探讨这节课和其他课之间教学内容的连续性;从着眼教学内容本身,到着眼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关联;从分析教学内容,到上溯教材内容和课程内容,从课程论的宏观视野来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等等。”①纵观2009年的语文教育教学报刊,笔者认为,研究聚焦于“教学内容的确定性”。研究者们正在试图打开这一问题的种种复杂性,力求有所突破,比如胡根林《确定阅读教学内容的三个维度》(《中学语文》第3期)、叶黎明《根据现实阅读需要创生合宜的教学内容》(《语文建设》第7-8期)等,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章。当前的基本共识是,确定合宜的教学内容,应该依据文本的体式,应该根据学生的学情,本文拟就“依据文本体式确定阅读教学内容”这一论题,选取王荣生先生的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评议文章】王荣生《依据文本体式确定教学内容》,原载于《语文学习》第10期。
【原文提要】阅读是一种文体思维,即对某一种特定体式、特定文本的理解、解释、体验、感受。阅读能力≈阅读取向+阅读方法。阅读取向,是指抱着什么样的目的、以怎样的姿态看待文本;阅读方法,就是对某种体式的文章,应该看(注视点)什么地方,从这些地方看出(解码和解释)什么来。阅读教学要做到两方面的工作:指导学生抱着合适的目的去看待特定的文本;指导学生在特定体式的文本里,能从重要的地方看出所传达的意思和意味来。文本的教学解读,是指教师在备课时需要依据文本体式来解读课文,进而确定合宜的教学内容。
这篇文章是《语文学习》杂志2009年刊载的王荣生先生的专题系列讲座的第二讲。《语文学习》当年连续刊载了王荣生先生的三次讲座,讲座的主题是“以‘学的活动’为基点的课堂教学”,分若干专题,第一个专题是“教学内容的选择与教学环节的展开”,包括三讲,分别是:第一讲《教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学生学》(第9期),第二讲《依据文本体式确定教学内容》(第10期),第三讲《根据学生学情选择教学内容》(第12期)。在第一讲中,王荣生先生指出,“以‘学的活动’为基点的课堂教学”,是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方向;语文教师备课应有两个关注点——合宜的教学内容、有效的教学设计,合宜和有效,必须以“学”的活动为基点。接下来的第二讲和第三讲都是对“教学内容的确定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其中第二讲《依据文本体式确定教学内容》,重点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依据文本体式确定阅读教学内容”,代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引领研究方向。
这篇文章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对阅读、阅读能力、阅读教学三个概念的重新梳理;第二是讨论文本的教学解读——依据体式,作正反两方面的分析;第三是研究支玉恒老师的一堂课《只有一个地球》,通过这堂课来探讨如何从文本体式确定适宜的教学内容;第四是从文本体式的角度,讨论了“共同备课”主题教研活动中的几堂课。
文章指出,阅读,是某种特殊体式的具体文本的阅读。阅读教学,是指导学生抱着合适的目的去看待特定的文本,并且在特定体式的文本里,能从重要的地方看出所传达的意思和意味来。这是文章立论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如何依据文本体式确定阅读教学内容?王荣生先生认为,就是依据文本体式对课文进行教学化解读,这需要做到两点:第一,阅读取向常态,也就是像正常人(具有较高阅读能力的人)那样来读一个作品;第二,阅读方法要契合这种文章体式本身对读者所提出的要求,即这种体式的文章应该读什么,应该读哪些地方,应该怎样读,都是有法则可依据、有理据可遵循的。
可以看出,想要清晰、透彻地理解这一观点,关键是对“体式”这一概念内涵的把握。
笔者认为,“体式”,也可称为文体或体裁,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指文本的类别,即文类,“每一文类都拥有其特殊标志,被赋予了某种足以使其相对独立的性质;这些标志试图指示出某一种文类独一无二的身份,以便让它的家族成员共享一种相似性”②。这层内涵强调了不同类文本之间的区别及同类文本之间的相似。我们知道,文本的分类只有相对的标准,而没有绝对的或单一的标准,比如文学作品,我们通常采用“三分法”——叙事文学、抒情文学和戏剧文学,或者“四分法”——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再如从教科书编撰和语文教学的角度,我们将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分为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等。“体式”在这个层面的内涵是广为人知的,一谈到体式、文体或体裁,我们通常首先就会想到这层意思,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层内涵当作“体式”含义的全部。当然,这是不全面的,因为“体式”还有第二个层面的内涵,即指单个文本的特定样式,也就是个体文本所具有的特殊的表现形态。而这层内涵,笔者以为,正是王荣生先生所强调的重点。正如文中反复提到的:“阅读,是某种特殊体式的具体文本的阅读”,“‘阅读是对某一特定文本进行解码和解释的具体而自愿的行为’,而在这段话里,应该特别关注‘某一特定文本’这几个字。”
从构成上讲,体式是文本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从性质上讲,体式又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既要具有某一类文本的共性特征或类的特征,又必然具有其个性的、独特的表现形态,我们说“依据文本体式来解读课文,来把握一篇课文的教学内容”,是指,文本的教学化解读不仅要考虑某一篇课文作为类的共性特征,更要把握其个性特征,而对课文个性特征的解读,往往是确定教学内容的关键。比如《只有一个地球》,虽然可以说是一篇说明文,具有说明文的一般特点和共性特征,但是更有自己独特的体式——用抒情性的语言来进行说明,正如支玉恒老师所说:“这不是一篇普通的说明文,是一篇饱满情感的说明文”;而这种个性的体式特征,恰恰应该成为确定这篇课文教学内容的依据。那么,这篇课文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能当作一般的说明文来解读和教学了,因此,支老师教这一课,并没有教什么说明的对象、说明的方法、说明的顺序等内容,而是去教阅读的感受,引导学生体验被课文唤起的情感。
接下来,文章进一步指出,依据体式进行文本的教学解读,确定教学内容,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文本体式共性特征层面内容的把握,意义是很有限的,应该努力开掘文本体式个性的特征,将其作为教学内容。文章援引《七根火柴》的课例研讨来说明这一观点。《七根火柴》的教学内容应该是什么?一开始,老师们认为,本课作为小说,当然是教小说的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所有小说的共性特征)。但是,小说的人物很单薄、概念化,情节也很简单,都不需要教。有教师提出,那只有教“环境”了。教师们所指的“环境”,主要还不是小说内的环境,即起着推动情节发展、丰富人物形象作用的“环境”,而是指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这个“背景”。给学生提供这种背景知识,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完全是教小说。看来,人物、情节、环境,作为教学内容,哪个都不太合适。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开掘,思考《七根火柴》是一篇什么体式的小说(这篇小说的个性特征)。原来,它是一篇革命现实主义小说,通俗地讲,就是“主题先行”的小说,它的主要亮点,是主题的表现。因此,教学内容应该确定为,小说是如何通过语言、形象来表现主题的;在教学设计上,一种有效的选择,是引导学生聚焦在“火”这个字上,以“火”为线索,让学生感受、理解这篇小说所表现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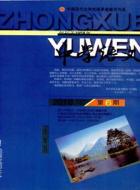
- 爬梳剔抉 探微求新 / 田 水
- 如何依据文本体式确定阅读教学内容 / 步 进
- 语文能力的层级区分 / 吴永福
- 阅读情意:文本解读的动力 / 张悦群 冯惟勇
- 浅析语文教学目标“四化”对有效教学的影响 / 朱冬民
- 语意教学的语用原理 / 王元华
- 高中语文阅读分层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 孙周通
- 语文有效教学过程的价值取向及其策略 / 唐海波
- 诵读——品读——研读 / 明学圣
- 论语文的教学内容 / 王 飞
-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教学实录与评点 / 余映潮 黄向阳
- 布鲁纳编码系统理论在语文学习中的运用 / 谭慧慧
- 说谎作文,我们到底该否定什么 / 梅其涛
- 体验式作文教学的透视 / 曹明海 张志刚
- 回归写作的原生态 / 祝泉洲
- 《论语》中的成语 / 韦志成
- 以改促写提高快 / 李震海
- 山水文学中的三种文人情怀 / 陶 涛
- 以时事激活高中应试作文的写作 / 林 瑛
- 巧用成语,叩开文言语法之门 / 万启霞
- 鲁迅作品的色彩艺术探微 / 雷冬梅
- 激发学生探究兴趣例谈 / 杨文清
- 试析柳宗元《永州八记》的审美内涵 / 白沁文
- 近十年高考作文题的题型分类\变化 / 潘 涌 王 婷
- 魅力桃花源 / 陈颂善
- 从“无我”走向“有我” / 曹伯高
- 高中《语文》中的特殊引用 / 卢卓群
- 母语危机:教育之痛与文化之忧 / 李兴茂
- 《长江三峡》比喻辞格的意图阐释 / 林忠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