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6期
ID: 136264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6期
ID: 136264
试析柳宗元《永州八记》的审美内涵
◇ 白沁文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在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被贬永州时所写的一组游记散文。当时柳宗元身处荒僻的永州且官赋闲职,这对于胸怀大志的他来说,政治人生走入了低谷,追求和抱负无法实现,内心无疑是痛苦的,加之远离亲朋好友,孤独郁闷,为了排遣被贬谪、被迫害的抑郁和苦闷,柳宗元只好寄情于永州的山水,用游山玩水来打发时光,并试图在大自然中寻觅人世间无法找到的精神慰藉,借寻山访水、描摹景物之机,来寄托自己的孤愤之情,抒发他对现实的不满,同时也折射出他内心的崇高和人格的美。
“八记”是描绘永州山水的一副长画卷,每一篇皆是雕刻众形,“语语指划如画,千载之下,读之如置身于其际。”①在这八篇先后相接的优美散文中,既写出了永州山水的动人之处,也抒发了自己发现山水之美的喜悦,同时还含蓄地表达出在大有作为之年却不得不在山水中消磨时日的无奈和悲愤。在对自然景象进行精细刻画的同时,将自身的坎坷遭际与忧愤之情寄于山水木石、鸟兽虫鱼的声色动静描绘之中,情景相契无间,物我妙合自然,写的是自然之美,达到的是美的自然。
一、美的发现与再造
通读《永州八记》,仿佛在柳宗元高尚的人格境界引领下,作了一趟愉悦的永州之旅。在柳宗元笔下,永州的山水宛如小家碧玉,“养在荒郊人未识”,柳宗元俨然是一个高明的导游,引领读者探胜寻幽,于荒僻处,以独到眼光和细致观察发掘美。循着柳宗元的游踪,那些原本隐于平凡处的山、石、木、水、鱼等等,渐渐拂去“面纱”,令人眼前一亮,叹为惊艳。游览途中,曲径通幽之处,别有奇特山水,往往有意外偶得之惊喜之意趣,令人乐此不疲,心向往之,进而品赏美,最终感悟美。
在柳宗元之前,东晋陶潜《桃花源记》中有渔人寻路而得“世外桃源”: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柳宗元也是一位善于发现美景的“渔人”,且看:
《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一路辛苦,披荆斩棘,终于到达目的地,“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果真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荒山野林中的小石潭,本不为人知,柳宗元是从小丘往西“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之后,才于偶然间发现这一美妙去处的,写得这样曲折迂回,因此也就引人入胜。
《袁家渴记》中,“舟行若穷,忽又无际”一句写行船过程中貌似绝望之际,突然又峰回路转的感受,不免使人猜测,后人陆游《游山西村》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句很可能是受此句启发而得。
“八记”各篇,美,无处不在,俯拾皆是,但只有像柳宗元一样有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兴致盎然地寻踪觅迹,才能于蛮荒野郊处领略山水之奇美。
柳宗元不仅善于发现美,而且用心体会美,从而通过其独特的视角改造美。他在《永州八记》好几篇中都记叙了自己对风景的再造。永州山水本已颇具意趣,经过柳宗元匠心独运的风景再造,或删繁就简,或刈杂留精,使永州山水之美更加凸现。
《钴鉧潭记》中,柳宗元兴致勃勃地“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经过加高台面,延伸栏杆,疏导高处的泉水使其坠落入潭中的一番改造之后,潭上景色尽收眼底,特别是到了中秋时节赏月更为适宜,可以看到天空更高,视野更加辽远,钴鉧潭及其周围景物尤显高旷悠远之美。柳宗元失意远贬,本来是“不乐居夷”、“不忘故土”的,现在却因为得到了这个潭,竟至乐于居夷,忘怀故土,可见其对钴鉧潭的偏爱。
《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柳宗元“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当铲刈焚烧之后,“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嘉木、美竹、奇石一下子展现在新主人面前,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而且:“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作者的悠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石渠记》中,柳宗元一番劳作,“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酾而盈。”石渠之水因此更加充盈。
《石涧记》中,柳宗元突发奇想,“揭跣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真是洞天之中又有无穷洞天。
由此可见,在柳宗元那里,自然之美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人的精神境界相互呼应的,这应该说是他发现美、体会美并再造美的基石。
二、山与水的审美空间
细读《永州八记》,可以发现,柳宗元的审美取向,是由内而外的;他的审美空间,在观山,在赏水,最终也在塑造内心人格。
(一)观山
欣赏永州的山,需要多视角切入:既需远望总览,又要近观细察;不仅要作全景鸟瞰,还须特写凸显;当然还少不了扭转头颈或仰看高上,或俯视低下,或环顾四周。
《始得西山宴游记》西山的高险和邈远,正是通过登山后的鸟瞰、眺望,将眼前见到的尺寸千里的景物侧面衬托出来:“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 这番描绘,没有直接着力于西山本身的景物,而是依据透视原理着力刻画登临眺望中尽收眼底的远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映衬,以及生动的比喻色彩的渲染,构成一幅绚丽多姿萦青缭白的山水图画。
《袁家渴记》的景色是全景式描绘,从大处着眼加以概述,然后把笔墨集中在一个景色特别优异需要重笔描绘的小山上。柳宗元引导读者的视线从大到小,由远而近,“渴上”、“渴下”、“其中”,层次分明,疏密错落有致。
《小石城山记》中,柳宗元引领读者翻山越岭,歧途回返,兴致盎然地探胜寻幽,登高望远:“土断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奇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也。”清乾隆年朱宗洛评价这段话时说:“由山出石,由石写城,由城及旁,由旁及门,由门而上,既上而望,因望而异境”。②优美的风景“千寻万探始出来”,别有一番情致。
山间常藏石,“八记”中的石很多,可谓是步步有石,柳宗元用丰富形象的比喻,对各处的石头进行惟妙惟肖的描摹,使得大大小小的石头呈现出浮雕般的立体感,群石千姿百态,各具风致,绝无雷同:
《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群石奇形异态:“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化静为动,平添趣味。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小石潭“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从而揭示出潭水清澈的原因。
《石涧记》中的涧石有的平坦宽阔“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有的“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还有形态奇异的“龙鳞之石”, 由于柳宗元采用了多种比喻精确形象地进行描绘,所以读者赏来毫无重复之感。
欣赏完了“八记”中的群石图,使人领悟到,要想欣赏到美,不仅要像柳宗元一样有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还要像他一样有一颗慧心,用丰富的想象化平凡为奇特,从而无限地拓展审美的空间,获得丰厚的审美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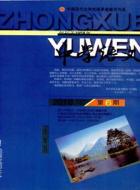
- 爬梳剔抉 探微求新 / 田 水
- 如何依据文本体式确定阅读教学内容 / 步 进
- 语文能力的层级区分 / 吴永福
- 阅读情意:文本解读的动力 / 张悦群 冯惟勇
- 浅析语文教学目标“四化”对有效教学的影响 / 朱冬民
- 语意教学的语用原理 / 王元华
- 高中语文阅读分层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 孙周通
- 语文有效教学过程的价值取向及其策略 / 唐海波
- 诵读——品读——研读 / 明学圣
- 论语文的教学内容 / 王 飞
-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教学实录与评点 / 余映潮 黄向阳
- 布鲁纳编码系统理论在语文学习中的运用 / 谭慧慧
- 说谎作文,我们到底该否定什么 / 梅其涛
- 体验式作文教学的透视 / 曹明海 张志刚
- 回归写作的原生态 / 祝泉洲
- 《论语》中的成语 / 韦志成
- 以改促写提高快 / 李震海
- 山水文学中的三种文人情怀 / 陶 涛
- 以时事激活高中应试作文的写作 / 林 瑛
- 巧用成语,叩开文言语法之门 / 万启霞
- 鲁迅作品的色彩艺术探微 / 雷冬梅
- 激发学生探究兴趣例谈 / 杨文清
- 试析柳宗元《永州八记》的审美内涵 / 白沁文
- 近十年高考作文题的题型分类\变化 / 潘 涌 王 婷
- 魅力桃花源 / 陈颂善
- 从“无我”走向“有我” / 曹伯高
- 高中《语文》中的特殊引用 / 卢卓群
- 母语危机:教育之痛与文化之忧 / 李兴茂
- 《长江三峡》比喻辞格的意图阐释 / 林忠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