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14年第6期
ID: 358880
语文建设 2014年第6期
ID: 358880
简易功夫终久大
◇ 徐兴无
黄厚江老师某次谈起他要写一本《论语读人》的小书,我说题目很有趣。今天他已写好,命我写个小序。匆匆读后,最直接的感受是,厚江老师的这本书纯以简易之法读经典,从而将经典读成了平易近人的书。
古人平时读的书很少,孔子以前贵族才能受教育,读的也只是《诗》《书》而已。这两部经典是从乐师和史官手上的文献中选编出来用于公民教育的教科书,很像我们的《语文》教材,但古人还有一种文化资源,就是“古人之言”。从《左传》《国语》等春秋时代的史书中可见,古代贵族说话时,除了引称《诗》《书》之语,就是“古人有言曰”“古之人曰”“史佚有言曰”。因此,古人只说话,不著书,春秋时代人们所说的“三不朽”包括“立德”“立功”“立言”三大项,前两项是圣人和圣王们的事业,后一项君子、贤人、士人皆可以做。孔子也依循这个传统,只说话,至多编写教材,所谓“述而不作”。孔子的学生平时和他交流或上课时,总是将老师的言行或上课讲解经典的内容及时记录下来。孔子死后,学生将他的言行录集中起来编成《论语》,从此,中国的文献里就出现了许多“子曰”。
介之推说:“言,身之文也。”孔子也认为,真正能立得起来的“言”是德行的体现,与人的行为修养不可两分。他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巧言令色,鲜矣仁!”他的课程大多是实践课,比如教学生行礼、奏乐、射箭、驾车,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学生和他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孔子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其中翘楚者十人,分属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只占其一。因此,学生除了记录老师和同学的言论,也记录老师和同学的德行。我在上文学史课时,曾经问学生,为什么《论语》中的人,话说得很简易,但孔子师生的形象却十分鲜明,而后来的《孟子》《荀子》,话越说越复杂,老师和学生的形象反而越来越暗淡?原因就是,后来的儒家,只知道记录老师的思想和言论,不知道记录老师的德行,不知道如何深入生活,访问调查。古往今来读《论语》者,大多关注其中的“言”,厚江老师的书另辟蹊径,给我们揭示了《论语》的另一面:人是言行的统一体,读人才是对《论语》全面的阅读。
陆象山诗曰:“简易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易浮沉。”然简易亦须有功夫,厚江老师的读法不是学究式的,而是感发和个人的。为了避免主观的误读和过度阐释,他首先综合前人定说加以评判,便之简易凝练,在此基础上加以创发。其创发多联系自家经历与当下生活,文字平易,道理亲切,多令人会意颔首。在他的阅读中,孔子和他的弟子这些古代的圣贤“大人物”被还原为“一般的人”,既体现了对“经典”和“大人物”的现代反思,也体现了对“经典”和“大人物”的现代敬意。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将大哲学家分为四组,第一组是思想范式的创造者,包括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四人,因为他们“被证明了千余年来一直不断地在发挥着影响”(《大哲学家》)。如果说孔子给中国的思想创造了什么范式的话,那就是他让中国人的思想始终关注在如何做人、如何生活的问题上。厚江老师的这本小书,讨论的正是这些问题。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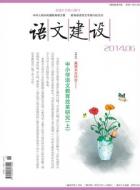
- 卷首 / 佚名
- 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研究的基本构想 / 任翔
- 语用观指导下的语文教育改革整体设计 / 李宇明 姜丽萍 王帅臣
- 批注式阅读教学反思研究 / 倪燕 朱婷
- 重心转移与范式重建 / 毋小利
- 例谈语文教材中小说的三种故事模式 / 刘俐俐
- 发挥语言唤醒功能,提高教学有效性 / 冯现冬 张伟忠
- 提高课堂效率途径摭谈 / 吴燕
- 课堂追问“四法” / 魏永胜
- 以学生为本 以专业为本 / 邵岩
- 挣不脱精神“套子”的悲喜剧 / 孙绍振
- 《诗经·邶风·静女》主题新探 / 彭超
-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误读辨正 / 陈加宏
- 傲岸的人格与“特立”的西山 / 徐晓岚
- “SOLO”评价法与古诗词教学 / 汤振纲
- 高考作文等级评分标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 郑玉财
- 新中国成立前后小学语文教科书概述 / 杨建国
- 语文课程性质的历史论争及当代启示 / 蔡可
- 小议“高端大气上档次” / 方寅
- “敖包”不是蒙古包 / 董越
- 语文课堂拒绝“课工” / 肖君健
- 语文的“是”与“非” / 程振理
- 让更多人知道规范的原因和根据 / 许嘉璐
- 简易功夫终久大 / 徐兴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