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14年第6期
ID: 358862
语文建设 2014年第6期
ID: 358862
例谈语文教材中小说的三种故事模式
◇ 刘俐俐
作为艺术作品的小说,是创造性精神活动的产物,怎么与故事模式相关?换个角度说,如果认可小说艺术有某些故事模式,合理性在哪里?从故事模式角度分析,对小说艺术作品有哪些更深刻体悟?本文就来讨论这些问题。
一、故事模式的含义和形成
1.故事模式的含义
为了说明故事模式,需要先介绍民间故事学中的故事类型和母题概念。“母题是故事中最小的叙事单元,可以是一个角色、一个事件或一种特殊背景。类型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类型是由若干母题按照相对固定的一定顺序组合而成的,它是一个‘母题序列’或者‘母题链’。这些母题也可以独立存在,从一个母题链上脱落下来,再按照一定顺序和别的母题结合构成另一个故事类型。”[1]即故事类型是一个完整并独立存在的传统故事。一个故事类型可由多个母题组合,母题可变化与转移。小说的故事模式与故事类型及母题有相似之处。
理解故事模式的含义需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因为读者喜欢某种传统故事,所以,小说家才选择此种故事模式创作;第二,故事模式寓于小说并借助于小说文体,讲述传统的完整故事;第三,故事模式可变化,这既缘于小说艺术是创造性产物,作家均有自己的艺术追求,追求创新是常态,又缘于故事模式具有组合多个母题的能力。
2.故事模式的形成
第一,来自小说家的艺术经验。一般说来,小说家都有较固定的创作领域,在固定领域创作而获得特殊的人生经验和体悟,更知道哪些故事有趣,适合放置在小说中讲述,读者会喜欢。小说家频繁选择的故事,久而久之成了传统故事。第二,来自小说的特性。小说是一个陈述句的展开。某些故事与小说陈述句特质及其基本故事语法更加吻合,与小说家长期耕耘的题材领域、人文体悟吻合,小说家有施展空间。第三,来自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辩证心理。故事模式让读者熟悉,熟悉产生优越阅读心理;同时,小说家总会在故事模式中有故事、叙事话语、思考意蕴等方面的创新,让读者产生探究的意愿,于是,在熟悉又陌生的阅读心态中读到了新奇又熟悉的故事。
文学理论可以对自然形成的故事模式发现和概括。本文暂且总结出“故乡与返乡”“最后一个”“进城”等几种故事模式,分别介绍。
二、“故乡与返乡”故事模式
1.“故乡与返乡”故事模式与小说艺术的吻合之处
第一,具有空间移动性。故乡与他乡,都是地理上某个地方的空间概念。故乡与他乡对应,或者从故乡到他乡,或者从他乡返回故乡,两种情形均为空间移动。当陈述句展开从某地到某地,并呈空间移动时,与特定时间相对应。空间移动让人产生观感和心理活动。《荷马史诗·奥德赛》等即是。第二,故乡属于特定、有血有肉的人物。当某人物从故乡前往他乡,或者从他乡返回故乡,人物与行程景物、经历等就发生了关系,所见所闻所感、各种思绪自然产生,心理世界就有了丰富的内容。第三,易于形成故事。返乡或者离乡,都注定有目的,无论目的伟大还是平庸,追求目的实现的过程,必定遭遇各种影响,易于形成故事。《荷马史诗·奥德赛》最典型地证明了“故乡与返乡”模式适合讲故事。
2.鲁迅《故乡》的“故乡与返乡”模式分析
先看鲁迅是如何讲述“故乡与返乡”故事的。《故乡》采用以“我”为立足点的内聚焦叙述模式。“我”如同取景框,外在行程的景物、事件通过取景框进入叙述视野。“我”有两个身份:返乡变卖老屋带着母亲离乡的“我”,少年时与闰土玩耍的“我”。即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的两个主体:回忆主体和体验主体。返乡的“我”是回忆主体,少年的“我”是体验主体。两个“我”交叉叙述其所见和感受。表层叙述线索交叉着回忆和体验两条具体叙述线索。
再看鲁迅的《故乡》可以产生怎样的理解。儿时情境,和闰土有趣的往事、场景、对话,传递寻找儿时的梦想、重温田园浪漫,既有人文气息,又合乎人类回忆往事、怀旧的情感需求。返乡看到诸般景色,借所见的故乡破败,抒发对时局的不满和感叹,体现了作者对现实审视与批判的人文精神;返乡后遇见的各种人物,通过对话和交道,“我”深切体验了故乡人们的尖刻、狭隘和麻木,体现了对国民性的批判。这些理解都可成立。还有怎样更深刻理解的空间?生命轮回感与悲剧性的幻灭感。少年时代和闰土相处的情景,与现在水生与宏儿相处的情景,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产生了生命轮回韵味。轮回感有慰藉、温暖一面,体现了生命的魅力。可是,生命轮回又预示悲剧命运再次发生,传递了宿命感,哲理油然而生。“我”究竟是希望轮回还是相反呢?这就涉及关于“希望”的思考。有所谓“希望”吗?“希望”究竟是什么?每个人的“希望”相同吗?这是故事展开与发展必然涉及的又一哲理问题。由此体现了鲁迅的“自我辩驳的性质”,阅读《故乡》的体悟已经验证了这个推想。鲁迅的“故乡与返乡”故事:不重复他人,也不可复制。
三、“最后一个”故事模式
1.“最后一个”故事模式与小说艺术的吻合之处
第一,“最后一个”是偏正词组“偏”的部分,其“正”的部分,有多种可能:一种职业、一种手艺、一种工艺、一个夜晚、一个农场……,换句话说,“最后一个”适合的题材领域宽广。第二,具有追溯、正视、前瞻三个时间维度。人、事、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职业等,均意味此前存在很久或很多。从最初的很少到较多,再到很多,再到现在的最后一个,三个时间和空间维度均可展开:追溯“最后一个”之前;“最后一个”的此时;“最后一个”的未来。因此,这一模式特别便于讲故事,便于渗透时间和空间感悟。第三,适宜传递挽歌情调。“最后一个”意味某个类型事物即将消失,从此再也不会有了。讲述“最后一个”故事,表明人类就此有珍视、遗憾、舍不得等感情,让小说带上了挽歌情调。美学家已经发现,人类本性中原本就有哀挽和悲伤的基因,在哀挽和悲伤中,人类能体会到悲凉的情调,乃至悲凉之美。所谓“写忧而造艺”是也。
2.都德《最后一课》的“最后一个”模式分析
先看都德是如何讲述“最后一个”故事的。都德以第一人称内聚焦形式叙述故事。故事讲述巧妙:顺着时间先后的顺序,一个淘气小学生“我”迟到,得知是最后一堂法语课,到课堂完结。线索清晰简洁,却叙述出了外在情节和内心活动两个层面。外在情节,展开了故事开始、进入、发展与结束:早上“我”不想上学;还是去了,去学校路上看到镇公所的布告牌;跑到教室后发现与往日气氛不同,入座,韩麦尔先生没有批评“我”,发现了许多镇上的人;韩麦尔先生正式说明“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韩麦尔先生叫到“我”的名字要求“我”背书,“我”不会且很难过;先生没有责备并说了许多话;先生继而将话题引到法国语言;语法课后又上习字课,又上历史课;课堂教学完结,先生宣布下课、放学。如果只有这些功能单位,那么“最后一课”,决不能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小说。标志性单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即小弗朗士看到、听到外在情节后内心的理解、思索和发挥的部分,始终随外在行程和情节变化,标志单位也随时调整,富有弹性和感染力。功能单位和标志单位共同成就了“最后一个”故事模式的丰厚意蕴和理解空间。
再看都德的《最后一课》可以产生的理解。让小弗朗士突然间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立意改变自己,传递出学生应努力学习,不要荒废光阴,以免留下遗憾的劝诫意义;刻画了韩麦尔先生立足于本职,热爱祖国语言、热爱教学的敬业精神和品德;让在课堂上听课的所有人,由最后一堂法语课感受了国家存亡旦夕的危机,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这些理解都可以成立。此外,还有更深刻的理解空间。是否可将祖国、民族、语言三个关键词,通过小弗朗士切身感受的故事,抽象为更具形而上特点的理解?语言是人类本能,每个人自出生就与母语紧密相连。母语蕴含民族历史和文化,保存民族记忆。从教授和学习母语权利的被剥夺,体悟丧权辱国的痛苦,乃为最深的痛苦。母语、民族和祖国内在的宿命关系就在这样的联系中抽象为某种哲理。
四、“进城”故事模式
1.“进城”故事模式与小说艺术的吻合之处
第一,具有空间移动性。“进城”作为动词,是主谓句的谓语部分。完整的主谓句应是“某某进城”。某主体进城,与小说陈述句性质吻合。在这点上“进城”模式与“故乡与返乡”相似,适合叙事作品展开情节、描写场面、叙述所见所闻、抒发感慨甚至生发议论等。第二,具有刻画人物、拓展文化思考的空间。中国文化语境中,农村落后、偏远、文明程度差,农民少见识没有文化,愚昧封闭;城市热闹、繁华、富庶、文化信息较多,城里人文明、信息灵通。“进城”可以讲述各个历史阶段文化环境中的故事,可以刻画各种时代背景、文化范围的人物形象。第三,作家叙事文学可以借用民间故事类型而有更多艺术创造。丁乃通编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有“进城”故事类型,标号为“1337【乡下人进城】·各式各样的误解和窘况,有时他是去访问富人的”[2],还有“1681*【笨拙的模仿者】·一个农民(有时是一个呆女婿)自己想或者有人告诉他,去模仿城里人(或者高雅的亲戚)的风度”[3]。两个类型常常相互结合,但是民间故事类型仅有故事梗概。作家叙事文学则精心设计功能单位,并精心设计标志单位,以气氛渲染、描写心理活动乃至潜意识等。质言之,作家可借鉴该故事类型,创造性地讲述更富人文精神的“进城”故事。
2.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的“进城”模式分析
先看高晓声是如何讲述“进城”故事的。《陈奂生上城》采用说书体小说叙事方式。叙事时间上采用连贯叙述,叙述角度上采用全知视角,叙事结构上以情节为结构中心。此外,标志单位设计非常独到,具有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比如,陈奂生一路进城心理活动的描写,灵活机动又生动真切地交代了陈奂生的家境、性格特点,为后面情节铺垫。再如,刻画沉重历史文化环境积淀而成的人物复杂性格。陈奂生的某些隐秘心理,是漫长农村文化的贫瘠共同造成的。标志类单位发挥了特殊功效。比如,花了五块钱房钱,他很不平衡,所以“脱不脱鞋”引发了隐秘的心理活动:“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农民的狭隘、眼光短浅被刻画得活灵活现。花了冤枉钱,回家如何和老婆说?是陈奂生最发愁的事情。最后的落脚却别有意味:他回去后,要挺直腰杆地和家人乃至全村人说:“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这个心理过程,填补了功能单位的空白,即陈奂生上城之后处境发生变化的缘由。意蕴非常丰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再看《陈奂生上城》可以产生怎样的理解。讲述了有趣的农民进城故事,描写了农村的变化,农民自由做生意的乐观饱满精神头,从而赞美改革开放政策;陈奂生上城遭遇困境并得到吴书记帮助,描写和展示了新时期基层党的干部熟悉农村,与农民保持着水乳交融的关系,让读者看到生活变化与美好前景;赞美了当代农民,也写出了农民随时代不断前进的历史趋势。这些理解都可以成立。此外,还有更深刻理解的空间:此番进城奇遇改变了陈奂生的精神生活和现实处境。不仅是经济处境,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他另眼相看了,“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比以前有劲得多了”。这个变化的结尾饶有意味。人有自尊自爱并渴望得到他人尊重的精神需求。进了趟城,陈奂生找回了自尊,赢得了他人的尊敬。陈奂生上城故事,形象地诠释和印证了随着农民经济翻身而来的必定是精神翻身和更高精神追求。这个理解和阐释,涉及对人和中国农民的理解,对农村改革前景的理解等。
参考文献
[1]刘守华.比较故事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83.
[2][3][美]丁乃通编著,郑建成等译.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352-353,4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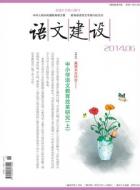
- 卷首 / 佚名
- 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研究的基本构想 / 任翔
- 语用观指导下的语文教育改革整体设计 / 李宇明 姜丽萍 王帅臣
- 批注式阅读教学反思研究 / 倪燕 朱婷
- 重心转移与范式重建 / 毋小利
- 例谈语文教材中小说的三种故事模式 / 刘俐俐
- 发挥语言唤醒功能,提高教学有效性 / 冯现冬 张伟忠
- 提高课堂效率途径摭谈 / 吴燕
- 课堂追问“四法” / 魏永胜
- 以学生为本 以专业为本 / 邵岩
- 挣不脱精神“套子”的悲喜剧 / 孙绍振
- 《诗经·邶风·静女》主题新探 / 彭超
-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误读辨正 / 陈加宏
- 傲岸的人格与“特立”的西山 / 徐晓岚
- “SOLO”评价法与古诗词教学 / 汤振纲
- 高考作文等级评分标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 郑玉财
- 新中国成立前后小学语文教科书概述 / 杨建国
- 语文课程性质的历史论争及当代启示 / 蔡可
- 小议“高端大气上档次” / 方寅
- “敖包”不是蒙古包 / 董越
- 语文课堂拒绝“课工” / 肖君健
- 语文的“是”与“非” / 程振理
- 让更多人知道规范的原因和根据 / 许嘉璐
- 简易功夫终久大 / 徐兴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