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14年第6期
ID: 358868
语文建设 2014年第6期
ID: 358868
《诗经·邶风·静女》主题新探
◇ 彭超
《静女》,出自《诗经·邶风》,是《诗经》中的爱情佳篇,其诗云:“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1]
第一章中“静女”之“静”,释义颇众,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解释为贞静、不轻佻等。毛《传》曰:“静,贞静也,女德贞静而有法度,乃可说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言志往而行正。”郑《笺》云:“女德贞静,然后可畜美色,然后可安,又能服从,待礼而动,自防如城隅,故可爱之。”[2]毛、郑解“静”为“贞静”,言女子虽内心渴望与男子约会,但是行为上毫无超越礼教之处,“自防如城隅”,强调了女子有德守礼法。第二类解释为闲雅、安详、幽静。欧阳修《诗本义》以为:“据文求义,是言静女有所待于城隅,不见而彷徨尔。”朱熹《诗集传》:“静者,闲雅之意。城隅,幽僻之处。不见者,期而不至也。踟蹰,犹踯躅也。”[3]闻一多《风诗类钞》亦解“静女”为“幽静之女”。这是位天性安静的女子,“从男女互相吸引、互相爱慕的角度,指出男子看中的是女子文静娴雅的内在气质”[4]。“静”重在指女子气质之娴雅、性格之幽静。第三类为假借义释,是指善女、淑女。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静女其姝……《艺文类聚》引《韩诗》‘有静家室’。静,善也。郑诗‘莫不静好’,《大雅》‘笾豆静嘉’,皆以‘静’为‘靖’之假借,此诗‘静女’亦当读‘靖’,谓善女,犹云淑女、硕女也。故‘其姝’‘其娈’皆状其美好之貌。”[5]认为“静女”其实就是指相貌美好的淑女。第四类以“静”为“情”之假借,当作“通情”解。证据有“静”与“情”在古音里同属耕部、从母,平声,为同音字,其互通符合古音通假原则。《逸周书》卷七《官人解》篇,周公曰:“饰貌者不静。”卢文昭校曰:“静,《大戴》作情,古通用。《表记》:‘文而静。’郑云:‘静或为情。’”《白虎通》卷三《情性》亦有云:“情者静也。”“静”通“情”,“静女”实为“情女”。此说可为一解。
此女子既与男子期于城隅,且故意躲藏起来,急得男子搔头徘徊,可见女子天性中的那份调皮与活泼。俟人于城隅的行为实在不是“能执彤管以为诫”的女史所为;又与性格安详、气质娴雅的文静女子有异;至于貌美之说,与下文“姝”重义,不能说美丽的女子很美丽。观察该女子行为,倒是不失为一位多情的少女。可以想象,女子看到恋人等候已久,急躁不安地走来走去,躲藏着的她心中充满爱情的甜蜜。“静女”实是“情女”,与情人约会在城隅,为多情女子。将“静”解释为“情”,想来离诗的本义不算太远。
第二章中“彤管”有笔赤管、乐器、红管草三解。一说,彤管为笔赤管。毛《传》、郑《笺》持此观点。毛《传》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炜,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郑《笺》:“彤管,笔赤管也。”[6]《周礼·天官·女史》:“女史掌王后之礼职,掌内治之贰,以诏后治内政……凡后之事,以礼从。”贾公彦疏引郑注,云:“女史,女奴晓书者,是以掌王后礼之职事。”《左传·定公九年》引“君子”的话说:“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静女》有邪,唯“彤管”可做“无邪”的发挥。这些都是从经学礼教角度出发,认为彤管是女史所持的红色之笔,借以宣扬女德,以刺世风。一说,彤管为乐器。段玉裁引《风俗通义》云:“管,漆竹,长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说文》:“六孔,十二月之音;物开地芽,故谓之管。从竹,官声。”高亨《诗经今注》:“彤,红色。管,乐器”,“彤管当是乐器,《诗经》里的管字,都是指乐管”。从当时音乐发展状况而言,乐器说似有可能。一说,彤管为红管草,即茅芽,与“荑”同物。“管”与“菅”同义,《说文》:“菅,茅也。从艸,官声。”20世纪30年代的辩论中,顾颉刚认为是“红管子”;魏建功与刘复认为是“乐器”;刘大白认为是植物,为“红色的茅苗儿”;董作宾亦主张“管”和“荑”同物,指初生的茅芽。[7]余冠英也认为:“彤管是红色管状的初生之草。郭璞《游仙诗》:‘陵冈掇丹荑’,丹荑就是彤管。”[8]依此说,此章的彤管就和下章的荑同指一物。
朱熹《诗集传》解释:“彤管,未详何物。盖相赠以结殷勤之意耳。炜,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悦怿此女之美也。”[9]没有指出彤管究竟为何物。《诗经》的年代距今久远,固然不能确定“彤管”为何物,但是考虑到《诗经》重章叠唱的特点,或许它就是第三章中的“荑”,即红管草。不然的话,就无法理解作为女史的女子为何将王宫女史之笔送人,也无法解释女子在一次约会当中为何送给男子两件礼物,更无法体现第三章与第二章之间的密切联系(试想,第二章为男女见面,女子赠红管草;第三章写男子与女子分别后,手持女子所赠茅草,思念爱人之美)。
第三章中“荑”的解释与“牧”联系密切。或说,“荑”为茅草嫩芽,“荑”与“彤管”是同一物。毛《传》:“荑,茅之始生也,本之于荑,取其有始有终。非为其徒说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遗我法则。”[10]欧阳修《诗本义》:“自牧田而归,取彼茅之秀者,信美且异矣,然未足以比女之为美,聊贻美人以为报尔。”朱熹《诗集传》:“荑,茅之始生者。女,指荑而言也。言静女又赠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异,然非此荑之为美也,特以美人之所赠,故其物亦美耳。”[11]各家在“荑”为茅芽这一点上取得一致,但是关于荑之来源及送荑女子存在争议。
这就涉及“牧”的解释。毛《传》:“牧,田官也。”[12]郑《笺》释“牧”为“牧田”。朱熹《诗集传》:“牧,外野也。”方玉润《诗经原始》:“牧,郊外也。”[13]《尔雅·释地》:“郊外谓之牧。”《孟子·公孙丑下》:“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注:“牧,牧地。”由“牧”的不同解释可得三种释义:“静女”,或为女史,恋爱对象为“田官”;或为牧羊女,在牧田放牧,采荑送给男子;或为乡间少女,在郊野采荑送给恋人。
考虑到“彤管”的解释,窃以为还是以“牧”为“郊野”适合。试想,女子在约会情人之前,可能是在郊外劳动或者是野游,于是顺手采集了茅草,打算约会时候送给男子。更何况,古代有赠白茅表示爱情婚姻的习俗,“白茅已经成了顽强生命力和旺盛繁殖能力的象征”[14],作为“茅管”的“荑”具有植物崇拜和生殖崇拜的特殊意义。这样理解的话,于男女身份和当时环境都是合情合理的。
《静女》主题的不同说法,和上面释义密切相关。其一为刺时说。《诗序》曰:“《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郑《笺》:“以君及夫人无德,故陈静女贻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15]方玉润《诗经原始》:“刺卫宣公纳伋妻也”,“城隅,即新台地也。静女,即宣姜也……宣姜初来,未始不静而且姝,亦未始不执彤管以为法。不料事变至于无礼,虽欲守彤管之诫而不能,即欲不俟诸城隅而亦不得也……(宣公)无如世间尤物殊难自舍,则未免有‘佳人难再得’之意,竟不顾惜廉耻,自取而自纳之,亦‘说怿女美’之一念陷之也”。[16]讽刺了卫宣公纳儿媳为妃的好色无礼、逆理乱伦丑态。
其二为约会说。欧阳修《诗本义》:“此乃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朱熹《诗集传》:“此淫奔期会之诗也。”[17]姚际恒《诗经通论》:“此刺淫之诗也。毛、郑必反之,牵强为说,不知何意。”高亨《诗经今译》:“诗中的主人公是个男子,抒写他和一个姑娘甜蜜的爱情。”余冠英《诗经选》:“这诗以男子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乐趣。”[18]此诗为“男女相悦”“男女相赠答”“男女相与歌咏”之辞,甜蜜约会之歌,勾画和谐爱情之美。
此外,有为人君求贤妃说。[19]毛《传》:“既有静德,又有美色,又能遗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正义》:“三章皆是陈静女之美,欲以易今夫人也,庶辅赞于君,使之有道也。”[20]也有怀才不遇说。《说苑·辨物篇》:“(贤者)伤时之不可遇也,不见道端,乃陈情欲以歌。”还有女史恋爱说。陈子展《诗经直解》:“《静女》,诗人热爱卫宫女史之作。”均可备一说。但是,最主要的观点还是要数前面刺时说和约会说两种。
综观前代各家学说,窃以为《静女》应为民间男女相赠之辞,是一首欢快的情歌,用男子口吻道出幽会密约的有趣情景。这首男女约会的诗既写出了焦急的等待,又描绘了欢乐的会面,还有幸福的回味。
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美丽画面:在一个春天的傍晚(或许是其他时间,考虑到“人约黄昏后”,姑且设定为傍晚),痴情的男子前往城隅赴约,期盼见到心爱的女子,以诉衷肠。俏皮的女子手持从野外采集的茅草,明明已到,偏要悄悄地躲藏起来,看着男子搔头徘徊(这大概是女子考察此男子的一种方式)。由于不忍看着恋人焦急等待,可爱的女子现身了,并郑重地将茅草送给对方。男子欢乐地接过女子手中茅草,发现茅草赤色如女子红颜,无限美丽。然而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可是女子所赠的茅草在二者暂时分别后,延续了两人的情意。男子回家后,看着手中的茅草,不禁想起女子的柔情,心中涌起无限美好,因为经过女子之手,连这茅草也变得“美且异”。
毫无疑问,《静女》是一首爱情诗。我们不应该拘泥“静”字,强解为“女德贞静而有法度”,专从经学角度出发,完全抛弃文学的眼光;也不可纠缠“彤管”之意,硬说是宫室女史恋爱之作,或是专门用来讽刺君王无德而作此诗。试着将眼光从“经”移回到“诗”本身,我们就会更好地品味诗中所含的美好感情。当《静女》女主人公由“王宫女史”变为乡间少女时,“淡化了情诗的美刺色彩,而多了民间情歌的气息”[21],这也就回归到诗的原始,一切也就会因其中蕴含的爱情而变得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2][6][10][12][15][20]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57:254-256.
[3][9][11][17]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26.
[4]匡鹏飞.从《静女》看《诗经》毛亨朱熹解释的差异[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2).
[5]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156.
[7]陈俐.《静女》主题辨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5).
[8][18]余冠英.诗经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33.
[13][16]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9,148.
[14]杜凤坤.《静女》中的“管”“荑”文化新探[J].现代语文,2008(9).
[19]杨合鸣,李中华.诗经主题辨析[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
[21]刘展.欧阳修《诗本义》“淫奔诗”说解读——以《静女》诗为例[J].科技信息,2008(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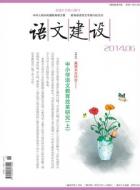
- 卷首 / 佚名
- 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研究的基本构想 / 任翔
- 语用观指导下的语文教育改革整体设计 / 李宇明 姜丽萍 王帅臣
- 批注式阅读教学反思研究 / 倪燕 朱婷
- 重心转移与范式重建 / 毋小利
- 例谈语文教材中小说的三种故事模式 / 刘俐俐
- 发挥语言唤醒功能,提高教学有效性 / 冯现冬 张伟忠
- 提高课堂效率途径摭谈 / 吴燕
- 课堂追问“四法” / 魏永胜
- 以学生为本 以专业为本 / 邵岩
- 挣不脱精神“套子”的悲喜剧 / 孙绍振
- 《诗经·邶风·静女》主题新探 / 彭超
-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误读辨正 / 陈加宏
- 傲岸的人格与“特立”的西山 / 徐晓岚
- “SOLO”评价法与古诗词教学 / 汤振纲
- 高考作文等级评分标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 郑玉财
- 新中国成立前后小学语文教科书概述 / 杨建国
- 语文课程性质的历史论争及当代启示 / 蔡可
- 小议“高端大气上档次” / 方寅
- “敖包”不是蒙古包 / 董越
- 语文课堂拒绝“课工” / 肖君健
- 语文的“是”与“非” / 程振理
- 让更多人知道规范的原因和根据 / 许嘉璐
- 简易功夫终久大 / 徐兴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