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9期
ID: 356264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9期
ID: 356264
《孔雀东南飞》注释商补六例
◇ 韩 肖
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中《孔雀东南飞》一诗的注释,吸取了古今各家的研究成果,在浅显通俗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笔者认为编注者对其中几个词语的处理似乎未尽完善,现提出来加以探讨,以就教于该诗的编注者、广大语文教师和专家们。
1.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
“十三能织素”,教材翻译为“十三岁就能织精美的白绢”,句中“能”字,编注者直接以今义译之,盖以其字面普通,故未予注释。其实不然,古籍中“能”字常用作“善于,擅长”义。《玉篇·能部》:“能,工也,善也。”《荀子·劝学》:“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杨倞注:“能,善。”《管子·五辅》:“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不能为政者,田畴荒而国邑虚。”句中“能”与“善”字互文见义。后秦道略集《雜譬喻经》卷一:“时南天竺有一畫师,亦善能畫。”同经又:“有一醫师,善能治病。王即召来,令治己病。”《齐民要术》卷六《养牛马驴骡》:“(马)股欲薄而博,善能走。”“善能”连言,是同义字复用。方一新、王云路先生《中古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即认为这句诗中的“能”字当为“擅长”义,“十三能织素”翻译为“(我)十三岁擅长织精美的白绢”,更能突出刘兰芝的聪明能干。
2.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相见常日稀”一句,教材未注,不少译文把这句话翻译为“我们见面的日子实在少得很”,笔者认为不够准确。“常日”是中古时期的常用词语,有“平日,平时;往日,以往”等义。如《三国志·魏志·仓慈传》:“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又《南齐书·高帝纪》:“常日乃可屈曲相从,今不得也。”唐韩愈《贺太阳不亏状》:“虽隔阴云,转更明朗,比于常日,不觉有殊。”皆其例。故这句诗应该翻译为“我们平日见面稀少”。
3.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大人故嫌迟”,教材翻译为“婆婆总是嫌我织得慢”,其中“故”字,教材注释为“总是、老是”。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也选录了此诗,该句中“故”字释为“故意”。而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下册(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则释为“仍然”。到底那一种解释更切合文意呢?细品此句,并参看下文“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笔者发现,若把“大人故嫌迟”解释为“婆婆总是嫌我织得慢”或者“婆婆还故意嫌我织得慢”,则文章不仅显得直白无味,而且也不符合刘兰芝这种聪明女子说话委婉含蓄的特点。若把“故”字解释为“仍然”,则前两句是质疑,是摆事实(我三天织了五匹布,那么快,婆婆仍然嫌我慢,为什么呢),后两句是答疑,是总结(其实并不是我织得慢,是你家的媳妇难做啊)。这样讲,既前后逻辑严密,语意通畅,也符合说话者的性格。而且中古时期“故”字作“仍然,还是”解多有其例,不是个别现象,如《史记·龟策列传》:“江淮间居人为儿时,以龟支床,至后老死,家人移床,而龟故生。”又陶渊明《拟古》(其三):“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皆其证。因而此句的“故”字,应该注为“仍然、还是”。
4.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
“恐此事非奇”,教材翻译为“恐怕这事这样做不合适”,编者注曰:“奇,似应为‘宜’,非奇,不宜。”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郭锡良等《古代汉语》和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都认为“奇”字乃是“嘉,善,美好”之义,“非奇”就是“不佳,不好”的意思。闻一多《乐府诗笺》亦曰:“奇事,犹佳事也。”“奇”本义指特殊,稀罕,不寻常,《说文·可部》:“奇,异也。”由珍异义引申出美好、美妙的意思来,此义古书常见,如《史记·殷本纪》:“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又《西京杂记》卷二:“梁孝王苑中……,奇果佳树,瑰禽异兽,靡不毕备。”宋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上揭例句中“奇”与“美”、“善”、“佳”、“好”相对成文,其义显而易见。教材中的“奇”字解释为“嘉,善,好”,正切合诗意,根本没必要以“宜”字来替换之。况且遍查字书、韵书,未见“奇”字假借作“宜”字的用法;而且二字字形相去甚远,传抄笔误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所以笔者认为编注者这样处理殊为不妥。
5.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卿当日胜贵”,教材翻译为“你将会一天比一天富贵起来”,郭锡良等《古代汉语》“日胜贵”注为“一天比一天更高贵”,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为“一天比一天贵盛起来”。对于“胜”字,三书均未作特别交代,从其注释来看,也很难看出“胜”字到底是与哪个词语相对,故而下面作一些补充说明。诗中“胜贵”当是同义并列,义指“显贵”,“胜”也是“贵”的意思。古籍中“胜”有“美好,佳妙”之义,如胜会、胜侣、胜友中的“胜”字都是此义。又由此引申出“有名的,上等的”之义,如《北史·白建传》:“男女婚嫁,皆得胜流。”“胜流”即“上流”,“有名的,上等的”也就是“显贵的”。“胜”“贵”二字中古时期经常连用,义指“显贵;显贵者”,如《晋书·郗鉴传》:“又沙门支遁以清淡著名于时,风流胜贵,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又《全隋文》卷三三释彦琮《通极论》:“或胜贵经过,或上客至止,不将虚心而接待,先陈出手之倍数。”皆其例。有时也写作“贵胜”,如《魏书·故叟传》:“每至贵胜之门,恒乘看牸牛,敝韦挎褶而已。”又《北齐书·邢邵传》:“尝有一贵胜,初授官,大集宾客。”
6.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
“恨恨”二字,教材注为“愤恨到极点”,笔者认为不确。“恨恨”这里当为“惆怅,忧伤”之义,此义中古常用。如东汉秦嘉《重报妻书》:“车还空反,甚失所望,兼叙远别,恨恨之情,顾有怅然。”三国魏王修《诫子书》:“自汝行之后,恨恨不乐。何者?我实老矣,所恃汝等也。”西晋陆云《与杨彦明书》:“彦先来,相欣喜,便复分别,恨恨不可言。”《隋书·孝义传·薛浚》:“但念尔伶俜孤宦,远在边服,顾此恨恨,如何可言。”此皆其证。联系上下文,焦刘二人最后相约以死抗婚,这是一种消极的非暴力的不合作态度,而不是咬牙切齿的无比愤恨的抗争,当时的情形应该是绝望,是无奈,是无比惆怅,而不是激烈的愤怒,况且无比愤恨也不合乎焦仲卿那种一向忍辱负重、懦弱无能的人的性格特征。
[作者通联:河北邢台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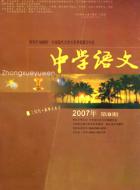
- 分析方法的可操作性(上) / 孙绍振
- 论内隐学习理论对语文教育的启示 / 屠锦红
- 语文教学之症结与出路 / 曹建召
- 关于孔子与《论语》的问答 / 韦志成 卢 欢
- 谈阅读向写作的有效转化 / 于树华
- 说原生态阅读法 / 陈友良
- 视野融合 / 毕泗建
- 论语文教材创造性使用的组合艺术 / 付 宁
- 与感性文本的理性对话 / 凌 志
- 让学生创造性地阅读文本 / 何汉池
- 作文教学方法策略探究 / 赵东阳
- 学会思 / 王祖德
- 写好细节,让作文飞扬起神采 / 徐地仁
- 一支振聋发聩的警世曲 / 洪 峻 邓应学
- 多一个视 / 张德勤
- 《风筝》文本的语文读解 / 王元祥
- 名送实 / 陆精康
- “闹”字下的“温柔一刀” / 喻 婷
- 请首先悲悯我们的孩子 / 王 君
- 《狼》教学实录与评点 / 余映潮/执教 庞荣飞/评点
- 从对面生情 / 郭振海
- 从联想到诗意的表达 / 孙正磊
- 蜩鸠之“笑”与宋荣子之“笑” / 徐新祥
- 语言观和语言教学 / 陈漪娟
- 非比喻句中“像”的表意功能 / 王恒娟
- 风之舞者 / 肖 科
- 《孔雀东南飞》注释商补六例 / 韩 肖
- “面向”?“背向”? / 毛 林
- 《离骚》一条注释商榷 / 董国志
- 创新总是在继承中进行 / 林志强
-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究竟“综”在何处? / 崔益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