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7期
ID: 143296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7期
ID: 143296
《归去来兮辞》重要词语考辨
◇ 王旭东
《归去来兮辞》中的“归”“鸟”“松”“自然”等词,是陶渊明诗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关联着陶渊明的哲学思考和人生态度。不能透彻地理解这些词,就不能深刻地理解作品;而一旦领会了这些词的意蕴,就掌握了解读作品的钥匙。
一.归去来兮——“归”是徘徊后的抉择
陶渊明诗文中,“归”字共出现了55次。根据他的诗文研究他的归向,可以把“归”的内涵分为二个层次:一、回归田园。回到远离世俗、远离官场、远离尘嚣的农村,过躬耕自给的生活。如《归园田居 其一》:“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二、回归自然。回归到人的自然本性,过一种无拘无束、自然而然的率真生活。如《归去来兮辞·序》:“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归园田居》其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三、离开人世,终归空无。陶渊明认为人是秉大块之气而生,死亡不过是“托体同山阿”,最彻底地回归到自然的状态。如《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园田居》其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徘徊——回归”是陶诗的重要主题。陶渊明在晋宋易代期间最混乱的八年(398—405年)中,先后投身到桓玄和刘裕等人幕府,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从青年时代出仕一直到辞去彭泽县令,他徘徊了多年,终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田园。陶渊明在此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集中体现了“徘徊——同归”主题:他在文中设想一种新生活,筹划一个新开始;他宣告了徘徊的结束,也宣告了回归的决心。这种在徘徊与回归之间抉择的过程,使作品情感丰富,有一种矛盾的美。
二.鸟倦飞而知还——“鸟”是归隐的象征
陶诗中屡次出现归鸟意象,如《饮酒》:“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归园田居》其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咏贫士》:“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读山海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归鸟》:“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
鸟归以前,四处觅食求饮,为物所累。推及言之,陶渊明囚屈己役于外物而使生命产生负累,待到归鸟趋林率性和鸣之时,诗人也“投冠旋旧墟”(《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高歌“归去来兮”,人鸟各遂其性,各得其所,都从外在对象的追逐中回到了生命的本真状态。诗人由鸟之归息,悟出自然真朴之哲理,这其中关键在“还”字,“还”就是返本。飞鸟日落犹知还巢,人生何独不然?“鸟倦飞而知还”深刻诠释了陶渊明逃离樊笼、返朴归真的生命价值取向。
诗人借着眷恋山林的归鸟,用一种无比依恋的感情,表达了他的向往。从此以后,陶渊明再也未曾出仕,归耕生活成为他的全部,陶渊明之后的大部分作品都展现出一种纯粹、自然的美。
三.抚孤松而盘桓——“松”是感情的寄托
陶诗中几次出现松意象,如《和郭主簿》其二:“芳菊开林耀,青松冠严列。”《拟古》其五:“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饮酒》其八:“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四时》:“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
孤松的形象最集中地表现在《饮酒》其四:“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这棵“孤生松”在强劲寒风的摧折之下,“众芳芜秽”之时,居然在劲风中没有凋残。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当草木都一样青翠的时候,无法知道谁的秉性是坚贞的。必须等到一年中最冷的季节,你才能注意到松柏的常青。“失群鸟”终于选择了一株孤独的、秀美的、坚强的松树作为自己清洁高远的感情的落脚之处,诗人真正找到了一个愿意停下来把自己的身心交托给它的所在。从此以后,不管外界再有什么变化,诗人永远也不会改变了。
陶诗中的松树是理想的地方,是清白的所在,是他在精神上所找到的安身立命之所,有了这个所在之后,他就再也不徘徊彷徨了。直面人生的悲哀苦难,陶渊明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饮酒》其八:“青松在东园……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看来,“东园”可能是实有一棵青松的,陶渊明把感情寄托其上,常常“抚孤松而盘桓”。
四.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自然”是人生的追求
首先,陶渊明所谓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一种自在的状态。他希望返归到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大真的性情,犹如一株树、一只鸟、一座山那样自然而然地生存着。陶渊明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意思是说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不受绳墨,只能依照自己的本性生活,维持自己本来的状态。
其次,陶渊明所谓自然,含有自由的意味。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是说在樊笼里不得自然也不得自由,归园田居才复得自然复得自由,不能简单理解为返回大自然(自然界)。
最后,陶渊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把“自然”当作医治人生各种弊端的良药。如《形影神·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
在陶渊明看来,只有返回山林田园,躬耕以谋生,而无求于世俗,才能真正得“自然”,从而也得到了自由。返回山林田园是“返自然”的前提。
五.聊乘化以归尽——“乘化”是生活的态度
陶渊明诗文中的“化”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宇宙间事物迁徙的过程,如四时的运行、朝代的更替、人类从生到死等。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归园田居》其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二是不可抗拒的万物自身变化的规律。如《悲从弟仲德》:“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形影神》:“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化”是一种规律,只能“乘”之,不能“腾”之;只能顺从,不能超越。
“归尽”就是死。“化”因具有不可抗拒性,人就不必为死亡的到来而忧虑,也不必为死后的未知而困惑。死虽不可知,但生是可以由自己掌握的,以自然的态度对待生,以泰然的态度对待死,这就是陶渊明的生死观。清吴淇《入朝选诗定论》:“‘委心任去留’,正是乘化,尤妙。在前有‘抚孤松而盘桓’,是妙于乐此余生也。”陶渊明以“乘化”的思想来化解生死困惑,使他的诗有了一种旷达的气度。
六.乐夫天命复奚疑——“天命”是哲学的基础
“天命”多见于儒家言论。儒家认为天决定人的命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联系上文“乘化以归尽”,其思想倒与道家一致。《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列子·力命》:“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又说:“农有水旱,商有得失,丁有成败,仕有遇否,命使然也。”此所谓“天命”,不是宗教里所说的有意志的主宰者或上帝的命令,而是人力无可奈何的“自然”及其力量。生死祸福,得失成败这些社会现象,完全由天命决定,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是徒劳。
颜延之回忆陶渊明真正面临死亡时的情景,说:诗人“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素幽告终,怀和长毕”(《陶征士诔》)。既已自知不起,便平和地委运任化。元嘉四年(427)九月,渊明作《自祭文》,说自己“乐天委分,以致百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生斯化,可以无恨”。同时期所作之《挽歌诗》三首写得尤其旷达,诗中自拟死后之种种情形,更是充分表现了他彻底的乐天知命思想。
“天”往往是陶渊明对“自然”的另一种表述,它更清楚地表明陶渊明相信有一种超乎“人”的自然力量,左右着人的生活和命运,而人必须顺应“它”。顺应“自然”的方法是保持自己的自然状态,以达到自由的人生境界。
《归园田居》中,那只“恋旧林”的“羁鸟”,栖止在《饮酒》中那株“独不衰”的“孤生松”上。读《归去来兮辞》,我们感受到,陶渊明在仕与隐的疑问、困惑、彷徨中,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以“乘化”的智慧安于“天命”,以悠然的心境躬耕田园,以求达到自在、自由的“自然”境界。陶渊明最终完成了三十年出与处的徘徊之后的回归。
参考书目:
[1]北大、北师大师生:《陶渊明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陶渊明:《陶渊明集》[M],逯饮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3]叶嘉莹:《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4]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王旭东,语文教师,现居湖北荆州。本文编校:剑 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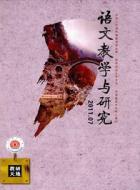
- 作文教学中的宏观驾驭与微观把握 / 陈文华
- 以生活为切入点进行作文教学 / 司徒妙英
- 作文中的描写技巧 / 褚兴梅
- 寻找多元解读的可能性 / 侯红宝
- 基于生活视域的语文作业设计策略 / 沈寿鸿
- 对一道思考题的思考 / 杨锦全
- 我们要砸烂作文新八股 / 魏润身
- 作文写作与感性美学 / 谭根稳
- 作文新八股结构批判 / 万永翔
- 材料作文易出现的误区及应对策略 / 林勇
- 警惕背离人本的作文教学 / 王俊杰
- 试论语文的情趣教学 / 张绍琼 李文忠
- 微语文教与学的基本特点 / 鲍国富
- 试谈课堂教学的点缀艺术 / 宋国侠 杨志勇
- 古典诗歌教学的三重目标 / 王万平
- 语言品味应紧扣那些细处 / 杨帆
- 使用标点符号应注意的问题 / 祝佩华
- 语文课堂教学实施有效管理研究 / 赵国卿
- 语文板书五法 / 马昭文
- 从山城到都市 / 邓方
- 语文课堂不能是中庸的和谐 / 尹磊
- 校园文学社团与校园文学报刊 / 晓苏 刘德旺
- 《渔父》中屈原“宁赴湘流”的另类解读 / 孟凡军
- 对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冷思考 / 卢卫东
- 近五年中考文史结合题型分类例说 / 吴霞霞 刘伟
- 《归去来兮辞》重要词语考辨 / 王旭东
- 文本解读中叹词添加微探 / 刘志勇 刘丽丹
- 《赤壁赋》和《游褒禅山记》比较阅读 / 金雅萍
- 《智取生辰纲》创新教学设计 / 刘宏业
- 阅读教学中切入点的选择和运用 / 陈海
- 黄家山上桃李芬芳 / 刘豫 李永健
- “闰土”与“旧毡帽”的形象比较 / 袁善来
- 鲁迅小说中的死亡现象举隅 / 李秀君
- 耕耘在这片红色热土上 / 张少莉 宋金华
- 站在三个层面上学好语文 / 吴数金
- 语文教学中自然科学知识的教学 / 谢英杰
- 回国观感 / 汤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