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7期
ID: 143298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7期
ID: 143298
《赤壁赋》和《游褒禅山记》比较阅读
◇ 金雅萍
苏轼的《赤壁赋》和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可视为富有理趣的游记文学的代表作。这两篇文章不同于一般的游记,描写重点不在山川风物上,而是借题发挥,因事说理;又不同于一般议论文的写法,而是通过具体记叙来阐发道理。所以两文都是从眼前环境中取材,叙议结合;但在具体行文构思过程中,又有其各自的特色,体现出两位作家不同的性情及行文风格。
一.记游的描写重点不同
《游褒禅山记》是王安石任职于舒州所作,写的是一次未能“极夫游之乐”的游览。王安石在游览过程中虽也看到了一些景物,但并没有尽探华山洞之胜,未见到更“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因此深感后悔、遗憾。作者的立意不在引导读者去领略褒禅山的风光,而在于托事寓理,因此,记游部分轻描淡写,一掠而过。
《赤壁赋》则写的是苏子与客在一个秋天的晚上夜游赤壁,泛舟江上的情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这八个字,清淡疏朗,写出一种静谧舒畅的艺术意境;“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中,“徘徊”二字,形象地描绘出柔和的月光好像对游人极为依恋的形态;在皎洁的月光下,白茫茫的雾气笼罩江面,水面和天光连成一片,让人想起“秋水共长天一色”。这赤壁之上,有清风、白露,有高山、流水,有天光、月色,令他们陶醉,竟产生了一种飘飘然变成神仙的感觉。景色的描写极其优美,同时又景中含情,为下文抒情蓄势。
二.行文的具体形式不同
《游褒禅山记》重在叙述游览过程与感受过程,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最后得出结论,使用的是“因事说理”的方法。文章从介绍褒禅山得名之由入手,接着简要地叙述了华山的前洞和后洞,然后详细地描写他们进入幽暗深邃的后洞的经过,写出了作者“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的真切感受。这既是对游洞实景的描写,也是对全文中心论点的暗示。最后,作者又用入洞越深、记游者越少的事实来强化自己的切身感受,慨叹自己在“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的情况下,却随着人群半途而废,乃至追悔莫及的惆怅之情。
文章从客观的记游向主观的议论逐渐自然过渡,记叙和议论紧密结合。上下文一气呵成,显得气势流畅。
《赤壁赋》是一篇散体文赋,它融诗、赋、文为一体。文中,写景部分主要抓住清风、明月、江水这三个方面,随后运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写对人生的思索和感叹。客人从眼前的景象发出感叹,历史上的那些风云人物,当年再怎么不可一世,但现在都已烟消云散,何况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呢?人生是多么的短暂,又是多么的渺小啊!苏子则巧妙地就眼前的江水和明月来生发议论:用相对论的观点来看,宇宙万物和人生都既是变化的,又是不变的,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就用不着去羡慕长江的无穷而哀叹人生的短促了。既然如此,应该到大自然中去,尽情地享受那清风明月之美。
总的来说,文章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四者紧密结合,情感波折,层层深入,创造了一种既充满诗情画意、又含寓着人生哲理的艺术境界。
三.文笔风格不同
《赤壁赋》一文,写景部分,文笔优美,充满诗情画意,即使主客问答、议论人生部分,也是不离眼前景,就眼前的江水和明月来生发议论,既贴切自然,又十分生动巧妙。整篇文章优美、流畅又十分紧凑。
而王安石的文章则风格迥异,他较少注意文章气氛的酝酿,不从感情上去打动人,而是紧紧围绕前文展开议论,最后得出明确主张。他的文章主要胜在语言简练、逻辑性强、分析深刻,而在形象性、艺术感染力方面稍逊一筹。
四.体现的性情、襟怀不同
《赤壁赋》是苏轼于“乌台诗案”获释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所作。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苏轼努力从这种精神苦闷中解脱出来的思想矛盾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消极颓废,“客喜而笑”,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身处逆境而依然洒脱、旷达的形象。
作为一位政治家,王安石的理想应该就是立志高远,他后来在政治上大刀阔斧的改革不就是探寻“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吗?朱自清说“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示人”,的确如此。在《游褒禅山记》中,他提出一件事情要成功需要“志、力、物”三个条件,其中,“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又充分地表现出他作为政治家,志向坚定、执着专注、力求成功的一面。
苏轼的一生,宦海沉浮,几起几落,但都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热情,贬谪生活反而使他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他的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胸怀让我们深深景仰;王安石以他坚定执着、敢为人先的精神,在北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后世梁启超曾肯定他“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给予了他最完美的评价。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们的才华是令人仰慕的,他们的精神更会光照千秋。
金雅萍,语文教师,现居湖北孝感。本文编校:黄碧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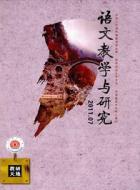
- 作文教学中的宏观驾驭与微观把握 / 陈文华
- 以生活为切入点进行作文教学 / 司徒妙英
- 作文中的描写技巧 / 褚兴梅
- 寻找多元解读的可能性 / 侯红宝
- 基于生活视域的语文作业设计策略 / 沈寿鸿
- 对一道思考题的思考 / 杨锦全
- 我们要砸烂作文新八股 / 魏润身
- 作文写作与感性美学 / 谭根稳
- 作文新八股结构批判 / 万永翔
- 材料作文易出现的误区及应对策略 / 林勇
- 警惕背离人本的作文教学 / 王俊杰
- 试论语文的情趣教学 / 张绍琼 李文忠
- 微语文教与学的基本特点 / 鲍国富
- 试谈课堂教学的点缀艺术 / 宋国侠 杨志勇
- 古典诗歌教学的三重目标 / 王万平
- 语言品味应紧扣那些细处 / 杨帆
- 使用标点符号应注意的问题 / 祝佩华
- 语文课堂教学实施有效管理研究 / 赵国卿
- 语文板书五法 / 马昭文
- 从山城到都市 / 邓方
- 语文课堂不能是中庸的和谐 / 尹磊
- 校园文学社团与校园文学报刊 / 晓苏 刘德旺
- 《渔父》中屈原“宁赴湘流”的另类解读 / 孟凡军
- 对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冷思考 / 卢卫东
- 近五年中考文史结合题型分类例说 / 吴霞霞 刘伟
- 《归去来兮辞》重要词语考辨 / 王旭东
- 文本解读中叹词添加微探 / 刘志勇 刘丽丹
- 《赤壁赋》和《游褒禅山记》比较阅读 / 金雅萍
- 《智取生辰纲》创新教学设计 / 刘宏业
- 阅读教学中切入点的选择和运用 / 陈海
- 黄家山上桃李芬芳 / 刘豫 李永健
- “闰土”与“旧毡帽”的形象比较 / 袁善来
- 鲁迅小说中的死亡现象举隅 / 李秀君
- 耕耘在这片红色热土上 / 张少莉 宋金华
- 站在三个层面上学好语文 / 吴数金
- 语文教学中自然科学知识的教学 / 谢英杰
- 回国观感 / 汤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