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7期
ID: 143303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7期
ID: 143303
鲁迅小说中的死亡现象举隅
◇ 李秀君
阿Q之死
示众这个热闹的死亡场景,反衬了民众对生命意识的淡漠与人性的缺失。鲁迅通过看客如同不远不近的跟定了他的眼睛折射出大众因为仇视异端或渴求刺激甚至习以为常的嗜血欲望。而此时的阿Q只是为自己没能在临死前唱出几句戏文娱众而羞愧,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排解现实生活中的不幸遭遇时,以为得到了自我安慰,其实终是自我戕害。中国人的生死大抵正如阿Q所想“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也未免要杀头的”,现实与历史叠加在一起表明阿Q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衰败的世界,而阿Q们还处于不自知的状态中浑浑噩噩,他们的死并非个体的悲剧,活得无用,死也无益,死亡现象仅仅是个体生命的消亡与生命进化的淘汰。小说中诉求的冷漠意向远比死亡本身更值得关注。
华小栓之死
人血通常被看成一个人的生命之精华和原本,在小说中暗喻人之生命。而延续人生命的人血馒头竟然与他人的死亡融为一体,含蓄而深刻的揭示了“人吃人”的主题。篇末用清明节时,华大妈和夏四奶奶一同出现在坟场为自己的儿子上坟烧纸一场来解构“人血馒头”“药”“坟”这三个死亡意象,放大并引申出新的意义。“人血馒头”中隐含着“坟”的意象,坟“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坟场景象又与茶馆事态相连构建各个死亡的内在联系。在前后呼应的氛围描写中,开篇以乌蓝的天,青白的灯光,灰白的路,突出清冷的色调,勾勒出阴冷神秘的轮廓,为华老栓刑场取“药”铺垫了恐怖的氛围;结局出现的荒凉坟场,则是与刑场相对的又一个死亡场所,死一般的寂静,枯草的颤抖,呆立的乌鸦,两个惊恐的老妇人,都把前后的死亡恐惧推向了极致,并且传达出自身深邃的死亡观。死亡意识是人类产生的最后标志,它代表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类对生存的理解正是从对死亡的感受中来。鲁迅对人物死亡的关注并非对普通人的生老病死现象的描写,而是对肉体死亡和精神死亡的分别对待,探索人物性格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挖掘死亡事件蕴涵的意义,是对人性生命的终极关注。
孔乙己之死
写孔乙己的死,鲁迅是动了点感情的,所以末尾用了“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作结,即便“死”未果,也不能活的揣度了。在小说的中间部分,酒客议论孔乙己偷了举人家的东西,被打折了腿的一段中,已经有人说过“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说孔乙己“许是死了”的话。但这个揣测被推翻了,因为中秋过后,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里来喝过一次酒。从此以后,孔乙己再也没有出现过。酒店掌柜在年关和第二年的端午时还一直惦记着孔乙己所欠的十九个钱,然而到了中秋却不再说起,这就含蓄地表明掌柜对这十九个钱已不存指望了,因为掌柜已经猜测到孔乙己这回可真的“死了”,可见死神是以常态徘徊在孔乙己身边的。最后“我”终于断定“孔乙己的确死了”,“的确”一词,是承前文而来的,这种对孔乙己结局的交代。从孔乙己这个悲剧人物的命运来看,他在那个时代不可能获得别的结局。腿未打折时,他的生计已是艰难,折腿之后,除了穷死,别无生路,“的确”一词让孔乙己的悲剧走向必然。鲁迅“大约”是不想亲见或是听说孔乙己的死亡的,所以孔乙己的死讯仅是个莫可名状的揣测。因为在咸亨酒店里出入的人谁也没有看见过孔乙己死了的现场,谁也没有听到过孔乙己死了的音讯,人们本来就没有关心过他,所以只是小伙计悬想而已。
祥林嫂之死
与孔乙己的死无对证不同,沦为乞丐的祥林嫂死在“祝福”之夜的漫天风雪中。祥林嫂只是一个旧中国的农村劳动妇女,她具有旧中国劳动人民的忍耐力,也有所有旧中国劳动人民的愚昧和不觉醒。形象的白描或小说构思的典型性都左右不了她被吞噬的命运,所以鲁迅给我们的又是一部展示死亡过程的小说,那走向死亡的因由或长或短,那奔赴死亡的速度或快或慢,都是鲁迅对当时社会的认识和表达。祥林嫂面临的人生困境是无法选择的困惑。活着生不如死,贺老六和阿毛都离她而去,连自己的痛苦也被咀嚼成渣滓而丢弃;被鲁四老爷视为“谬种”“不洁之物”而失去了参加祭祀的权利,甚至被赶出鲁家,沦为乞丐;选择死又怕有地狱,而且柳妈诡秘地对她说“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生而不得死亦不能。然而鲁迅终是让祥林嫂死了。“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没人知道她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没人去关心她是怎么死的。鲁迅依然用开放式文本去解构她的死,至于祥林嫂是自杀、病死、饿死,终是解构的任务,也是鲁迅值得终生阅读的原因。
李秀君,语文教师,现居四川广元。本文编校:左晓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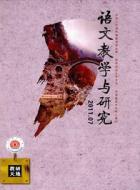
- 作文教学中的宏观驾驭与微观把握 / 陈文华
- 以生活为切入点进行作文教学 / 司徒妙英
- 作文中的描写技巧 / 褚兴梅
- 寻找多元解读的可能性 / 侯红宝
- 基于生活视域的语文作业设计策略 / 沈寿鸿
- 对一道思考题的思考 / 杨锦全
- 我们要砸烂作文新八股 / 魏润身
- 作文写作与感性美学 / 谭根稳
- 作文新八股结构批判 / 万永翔
- 材料作文易出现的误区及应对策略 / 林勇
- 警惕背离人本的作文教学 / 王俊杰
- 试论语文的情趣教学 / 张绍琼 李文忠
- 微语文教与学的基本特点 / 鲍国富
- 试谈课堂教学的点缀艺术 / 宋国侠 杨志勇
- 古典诗歌教学的三重目标 / 王万平
- 语言品味应紧扣那些细处 / 杨帆
- 使用标点符号应注意的问题 / 祝佩华
- 语文课堂教学实施有效管理研究 / 赵国卿
- 语文板书五法 / 马昭文
- 从山城到都市 / 邓方
- 语文课堂不能是中庸的和谐 / 尹磊
- 校园文学社团与校园文学报刊 / 晓苏 刘德旺
- 《渔父》中屈原“宁赴湘流”的另类解读 / 孟凡军
- 对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冷思考 / 卢卫东
- 近五年中考文史结合题型分类例说 / 吴霞霞 刘伟
- 《归去来兮辞》重要词语考辨 / 王旭东
- 文本解读中叹词添加微探 / 刘志勇 刘丽丹
- 《赤壁赋》和《游褒禅山记》比较阅读 / 金雅萍
- 《智取生辰纲》创新教学设计 / 刘宏业
- 阅读教学中切入点的选择和运用 / 陈海
- 黄家山上桃李芬芳 / 刘豫 李永健
- “闰土”与“旧毡帽”的形象比较 / 袁善来
- 鲁迅小说中的死亡现象举隅 / 李秀君
- 耕耘在这片红色热土上 / 张少莉 宋金华
- 站在三个层面上学好语文 / 吴数金
- 语文教学中自然科学知识的教学 / 谢英杰
- 回国观感 / 汤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