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7期
ID: 143293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7期
ID: 143293
《渔父》中屈原“宁赴湘流”的另类解读
◇ 孟凡军
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五中选取了《渔父》一文。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发现很多高中语文教师在教材的解读中有一个问题比较纠结:在渔父“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等的反复规劝下,屈原到底为什么依然要“宁赴湘流”,而甘愿“葬于江鱼之腹”?对此,很多高中语文教师简单依从了教学参考书的说法,借用教材中的表面文字“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来简化理解,即:因不愿与污俗的社会同流合污而自投汨罗江。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总觉这种说辞过于简单,没把屈原“宁赴湘流”的深层原因解析出来,从而使得屈原其丰满的形象大打折扣。
另外,一些文章家和教学参考书对屈原投江赴死的原因分析归结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这一主流观点,认为是因于楚国腐败,奸臣排挤迫害等,屈原自杀是以死抗争,决绝于世俗,不愿同流合污。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就是“伏清白以死直”。这种说法固然有其合理因素,但问题是,中国古代社会环境比当时楚国艰难的比比皆是,忠臣良臣被排挤打压贬官流放甚至迫害至死的更是多若牛毛,而为什么屈原做了文人自杀的第一人?
下面从人格社会学角度对屈原之死进行分析探究,希望能够为广大高中语文教师提供一个另类的教材解读。
一.屈原人格形成的基础
人格是社会学术语。社会学这样对人格进行定义:人格,即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的统合模式,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
人格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卑俗式人格,保守式人格,创造式人格。卑俗式人格,即人格缺乏高尚的道德情操,人格表现为低劣庸俗。如东方朔、元稹、纪晓岚等人。保守式人格,其人格二元化表现明显,有一定的志节,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但缺乏直面矛盾的勇气和主动解决问题的进取精神,在矛盾激化时以回避冲突、逃避现实、洁身自好为首要选择。如庄子、陶渊明、王维等。创造式人格,这是一种伟大的人格,富有想象力,有独到见解,对传统敢于怀疑,有大无畏精神。如屈原、李白、辛弃疾、关汉卿、龚自珍等。
屈原的人格因素中,有这样几个元素:美政,执着,自我实现,不妥协。事实也证明,屈原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其美政之执着、其爱国之忠贞,无时不彰显着伟大的创造式人格。
性而需,需而求,求而哲,哲而格,格而行,行而习,习而性。人性结构决定人性需求,人性需求决定人生追求,人生追求决定人生哲学,人生哲学决定人的性格。古语云:“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积性成命”,即同此道理。追根溯源,屈原这种创造式人格源于他独具的先天禀赋以及崇高的内美追求。
《离骚》开篇即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原在《离骚》开篇如此看重自己的血统和出身,他不是以先祖的高贵出身和丰功伟绩作为炫耀的资本,而是以此来明确自己人生的重大责任:勤修能、行美政、统天下。
这种责任感甚至于表现在给他的起名中。《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平”是平正之意,“正则”就是公正而可以法则,“原”是广平博大之意。屈原名如此,实是要求屈原以天、地为效法对象,追求社会的公正和协调。
基于此,我们就不难解释,屈原早年为何如此好奇服,爱花草,甚至有些异端表现。屈原以此喻指优秀品质的培养,是以此来表明自己独立不迁、深固难徙、廓其无求、俗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的高尚人格。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屈原一生忠君爱国,上下求索,九死未悔!屈原在《离骚》中所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些内美和背负的厚望成为了屈原伟大人格理想形成的内在原因,这也正是屈原一生独好修为、完善人格,勤美政、勇敢无畏的强大动力,使他立下了推行美政、振兴楚国的政治理想。于是,他为自己规划了人生轨迹:勤修能、行美政、统天下。由此,屈原的创造式人格发展就有了两条线:一是追求美政、竭忠尽智、独立无群的自我人格;二是执着无畏、以死殉道、九死无悔的政治人格。
西方有名言:“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屈原的这两种人格决定了屈原的一生命运!
二.屈原的自我人格:勤政尽职,独立无群
屈原的这种求美政、忠职守的自我人格决定了他人生理想追求的执着与不放弃,也决定了他人格上“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独立无群。
首先,我们有必要来看看屈原的仕途经历。可用三个词语来概括:竭忠尽智,忠贞报国,独立无群。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襄王三个时期,早时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论国事,参与法律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同时主持外交事务。因性格耿直,遭到群小的谗言与排挤,渐被怀王疏远。后来,怀王两度向秦出兵,均惨败,屈原不计嫌隙,危难中出使齐国,以一己之力重修齐楚旧好。而怀王目光短浅,轻于防范,竟欲与虎狼无信的秦国结为昆弟之国,屈原高瞻远瞩,坚决反对,再被楚王嫌弃,疏出郢都,流落汉北。但屈原初衷不改,作《离骚》明志。怀王27年,秦召怀王武关会盟,屈原看透秦国阴谋,卧辙死谏,但怀王不听,结果被秦扣留,次年客死秦国。楚襄王即位后实施亲秦的投降政策,屈原又为国谏言,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荒地十多年,但屈原爱国痴心不改。楚襄王21年,秦攻破郢都,楚国灭亡,屈原在绝望与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用一生的奔走操劳和鞠躬尽瘁,向后人诠释了其人格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如此,在追求美政的政治生涯中,屈原的人格始终保持着独立和尊严。
面对楚王,屈原不是盲目地去为君主效“犬马之劳”,而是要以其“独清”、“独醒”的人格优势为君主“导夫先路”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价值。在屈原“受命诏以昭”时,他之所以“忽奔走以先后”,是希望怀王能“及前王之踵武”以防“皇舆之败绩”。但当楚王为群小所围,听不进屈原的忠言而“怒”并“远迁”他时,他不是选择“屈心抑志”、投君主之所好而调整自己的自我人格,而是坚守自己的信念:“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为此,屈原不惜自疏汉北。
面对楚国,屈原更是表现出了赤子般的炽热情怀和宏阔的政治追求,我们可以在诗句中感触到诗人不懈追求政治理想的热情与崇高人格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离骚》中说:“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为了楚国的强盛,诗人奔走操劳,希望君王能赶上前代圣君的脚步;《涉江》中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屈原在“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仕途已陷入山穷水尽的窘境,这时尚不忘“修身”;《哀郢》中说,“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之忘反”、“冀壹反之何时”,即使楚国已经四面楚歌,屈原年老体弱,但他还时刻不忘返回郢都为国效力。
就是面对奸佞是非,在其独立人格与现实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的情势下,屈原也没有调整自身的人格去寻求安身立命之所,而是更加认同并坚守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决不妥协:“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在险恶政治环境的重压下,他不是去调整自己的独立人格以适应楚王君臣,也不是牺牲自己的价值观去进行世俗的追逐,而是“凝滞于物”,拒不“与世推移”,“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最后以“托彭咸之所居”的壮举保全了自己完美的人格。
即使被打击,人格依然高洁;即使被流放,但屈原的爱国情怀和政治追求不变。诗人反复表示:“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求美政,忠职守,社稷至上,这种人生追求是屈原伟大人格的核心;独立不迁,百折不挠,这种不妥协是其人格尊严的具体体现。只有这样的人格才有这种信念,只有这种信念才有这样的追求,才具有了伟大、崇高等审美价值。对此,史学家司马迁的评价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这种竭忠尽智、勤政尽职的美好的自我人格,也造就了屈原以死殉道、九死无悔的政治人格!
三.屈原的政治人格:以死殉道,九死无悔
政治人格是政治主体在政治文化和现实政治环境的双重影响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持久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高尚的的政治人格会产生出一种令人崇敬的人格魅力,从而产出巨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折服力。但遗憾的是,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因为政治文化和现实政治环境的普遍非理想化,这种高尚的政治人格常常演变成社会悲剧。
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杜尔凯姆研究归纳了自杀三因素,其中之一是“利他型”。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利他型自杀有一个重要原因:政治人格与社会政治环境的不调适。即社会政治环境给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狭窄,造成知识分子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一般的紧张和冲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理想与现实有巨大差别,个人充满了对现实的极度失望。
很显然,屈原之死是源于高洁的人格、高尚的美政追求和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不被社会的污俗所容,屈原的自我人格和政治人格无法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调适。
有三组不可调适的矛盾无法被屈原的政治人格所容忍,这也导致屈原最终选择了“以死殉道,九死无悔”。
一是智和昏。这是屈原和楚王之间的矛盾,是屈原的美政理想与楚王的昏庸短见之间的矛盾。楚怀王昏庸、短见,对外亲齐亲秦摇摆不定,盲目信任虎狼之秦;对内则宠任奸佞,听信谗言,疏远贤能。屈原虽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才能,但不被重用,反而被疏远。“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屈原修德立行,忠心耿耿,原想导君于尧舜之治,可是怀王竟然不识,反而信谗疏远,屈原心中有怨;对楚王的昏庸,《离骚》中“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一句,正深刻地反映了楚国政治环境;看着楚国一天天地倒向秦国,屈原在《抽思》中说“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屈原责备怀王太叫他失望。
屈原理想的君主政治人格,是希望楚王能像三王五伯那样做自己整顿吏制、救济民生、实现“美政”理想的坚强后盾。然而现实的楚王与屈原理想的君主政治人格之间相差太远。他寄予厚望的楚怀王却是“交不忠”、“期不信”、“曰黄昏以为期”而“中道改路”、“后悔遁而有他”的一个为“君子所鄙”的人。可以说,楚怀王的昏庸阻断了屈原实现美政理想的道路,给屈原的人生命运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灰色。但屈原的追求不能让他以智从庸!
二是正和邪。这是屈原和楚国奸小之间的矛盾,是屈原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环境发生的尖锐对立与
严重冲突。这种矛盾不可调和。
当时,楚国的贵族政治日趋腐化,楚国王室“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权贵们沆瀣一气,党同伐异,出现了“众踥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的局面。上官大夫、郑袖等人嫉贤妒能,频繁搬弄是非,使屈原被疏远,被放逐。屈原处在奸党的围攻之中,四面受敌,势单力薄,处境艰难。但他并没有低头屈服,屈原愤怒控诉了贵族当权派的无耻:“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他痛斥他们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玄文幽处兮,蒙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兮,鸡雉翔舞。”他指斥他们将要把国家弄到濒于危亡的地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可以说,楚国奸小的无耻阻碍了屈原美政理想的步伐,给屈原的人生命运又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但屈原的独立人格让他无法以正屈邪!
三是希望与绝望。这是屈原一生政治理想和楚国终极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直接导致了屈原对楚国的绝望,以及政治理想的彻底破灭。
如果还原历史,当时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夏历五月五日,进人垂暮之年的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披头散发,在汨罗江畔的长堤上行吟,嘴里叨念着:举世皆浊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啊,而我独醒。这时,一群逃难百姓涌来,难民伏地哀哭:秦兵挥师直逼郢都城下。楚国君臣仓皇逃走,将士纷纷奔城而去。秦军冲入郢都,已将秦国国旗高高插在郢都城楼。听此消息,屈原他顿足捶胸,大呼羞对先公,愧对后人。屈原的心碎了,他疯狂地跑到一座颓废的楚王庙里,把一个个木偶神像掼在地上。然后神志恍惚,并咬牙切齿地诅咒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跑到沉沙港口一株树下,他抱起一块岩石,纵身一跃跳进了汨罗江。
屈原的人格追求依赖于他的美政追求,而美政追求又依赖于楚国的存在,即使楚国千疮百孔,即使楚国岌岌可危,他也不离不弃。可刚烈的屈原遇到了昏庸的楚王,正直的屈原遇到了嫉贤妒能的楚国肖小。如果前两组矛盾还不足以毁灭屈原,可如今楚国灭亡了,屈原的人格追求和美政理想彻底失去了价值实现的载体。人格的独立与不屈,无法让他选择苟且地活着;理想的破灭,让他觉得生命也失去了意义。此时,早已不堪重负的心灵终于在刹那间轰然碎裂,带着撕心裂肺的痛,屈原选择了投江。这一刻,屈原选择的也许是让自己的美政理想和高尚人格成为永远的定格而不是放弃!
歌德在其《歌德谈话录》中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从根本而言,屈原投江,不是为君尽忠,也不是以死抗恶,而是“殉道”!这个“道”,是国家!是理想!是人格!
所以,屈原之殇,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愤恨,也不是“伏清白以死直”的愚忠,而是对现实政治环境的彻底失望,是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痛彻心肺。屈原的悲剧,不是个体的悲剧,而是当时楚国政治环境的悲剧,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悲剧!
创造式人格赋予了屈原大无畏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催使屈原最终宣告了与当时政治环境的彻底决裂。这个结论,也许能为《渔父》教材解读提供一个注脚。
孟凡军,语文教研员,现居江苏邳州。本文编校:左晓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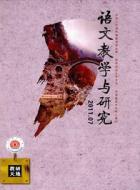
- 作文教学中的宏观驾驭与微观把握 / 陈文华
- 以生活为切入点进行作文教学 / 司徒妙英
- 作文中的描写技巧 / 褚兴梅
- 寻找多元解读的可能性 / 侯红宝
- 基于生活视域的语文作业设计策略 / 沈寿鸿
- 对一道思考题的思考 / 杨锦全
- 我们要砸烂作文新八股 / 魏润身
- 作文写作与感性美学 / 谭根稳
- 作文新八股结构批判 / 万永翔
- 材料作文易出现的误区及应对策略 / 林勇
- 警惕背离人本的作文教学 / 王俊杰
- 试论语文的情趣教学 / 张绍琼 李文忠
- 微语文教与学的基本特点 / 鲍国富
- 试谈课堂教学的点缀艺术 / 宋国侠 杨志勇
- 古典诗歌教学的三重目标 / 王万平
- 语言品味应紧扣那些细处 / 杨帆
- 使用标点符号应注意的问题 / 祝佩华
- 语文课堂教学实施有效管理研究 / 赵国卿
- 语文板书五法 / 马昭文
- 从山城到都市 / 邓方
- 语文课堂不能是中庸的和谐 / 尹磊
- 校园文学社团与校园文学报刊 / 晓苏 刘德旺
- 《渔父》中屈原“宁赴湘流”的另类解读 / 孟凡军
- 对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冷思考 / 卢卫东
- 近五年中考文史结合题型分类例说 / 吴霞霞 刘伟
- 《归去来兮辞》重要词语考辨 / 王旭东
- 文本解读中叹词添加微探 / 刘志勇 刘丽丹
- 《赤壁赋》和《游褒禅山记》比较阅读 / 金雅萍
- 《智取生辰纲》创新教学设计 / 刘宏业
- 阅读教学中切入点的选择和运用 / 陈海
- 黄家山上桃李芬芳 / 刘豫 李永健
- “闰土”与“旧毡帽”的形象比较 / 袁善来
- 鲁迅小说中的死亡现象举隅 / 李秀君
- 耕耘在这片红色热土上 / 张少莉 宋金华
- 站在三个层面上学好语文 / 吴数金
- 语文教学中自然科学知识的教学 / 谢英杰
- 回国观感 / 汤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