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7期
ID: 143278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7期
ID: 143278
作文写作与感性美学
◇ 谭根稳
在第十二届“新世纪”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评奖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认真阅读了十二篇特等奖入围作文。读了这些优秀作文,我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每篇都充满了感性之美。由此,我不禁想到了作文写作与感性美学的关系。
美学,作为一门精致的学问,却是起源于粗糙的感性世界。中国的美学,更是来自人们的直观现实而不是具体感性的一种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所依托的世界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世界,所要表现的世界也是生生相续的诗意世界,而非科学的、逻辑的、实用的功能世界,而一切表现生命世界的创造,首要的精神便是尊重感性,尊重整体,尊重关联,尊重性灵。
但在这个新陈代谢极为迅速的时期,文学却遭遇了一个最基本的美学问题,就是如何审美感性世界。这个问题反映在当下中学生的作文写作领域,又格外地直接、突出、广泛。对于中学生作文写作,我们已经头疼了很多年,我们总是很困惑,为什么青青葱葱的孩子们写出的作文,大量的总是空洞洞的、薄亮亮的、干瘪瘪的、冷冰冰的、硬邦邦的、死板板的,为什么总是丢不下灰扑扑的故纸堆,扔不了臭烘烘的三段论,容不下热闹闹的大时代,放不开活泼泼的真自我?那明亮亮的眼睛、激灵灵的脑袋、峭楞楞的个性、真切切的体验都去了哪里?是什么导致作文写作流行假大空、干冷硬的痼疾?是什么导致孩子们执迷规范、盲从技艺却反而丧失了基本的真诚和期待?又是什么导致笔端的世界总是一沟绝望的死水?然而,真正要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还要从如何审美感性世界说起。
真诚:尊重感性真实
尊重感性真实,是美学的起点,也是其意义归宿。感性生命,不仅是天地万物一切生命的结晶,也是一切流动的生命所体现出来的内在规律和复杂联系。尊重规律,起于尊重现象。作文写作,重要的是体现尊重。
尊重感性真实的写作,孳生于一种真诚的生命态度。这种真诚的生命态度,包括对一切感性真实的尊重,对人,也对物,还对二者之间的复杂联系。于人,既包括对亲近的人,也包括对陌生的人,包括对当下的人,也包括对过往的人;对物的态度,既包括对静态的物,也包括对动态的物,包括对自然的物,也包括对人文的物,包括对平常之物,也包括对非常之物。任何一种特定的认识感知和情感体验里,都应洋溢着一种感性世界真实的美,一种尊重感性真实的诚恳的美。这一届“新世纪”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中,一些成功的作品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个精神。
以黄顺意同学的《小心眼》为例,文章不足600字,篇幅短小得可爱,题材小气得可爱,文字稚嫩得可爱,心理真实得可爱。之所以处处可爱,从根本上来说,是小作者顺应了自己内心的本意,以真诚的态度再现了自身体验到的一种感性真实。相比这种写作状态,我们倒总是容易陷入由理性逻辑来驾驭真实事情的写作思维,总是企图用确凿的分析、既定的结论来掌控事态、人物和主题,我们以为这样是更加成熟的做法,却总是捉襟见肘、处处犯难,我们总在忍受追逐理性逻辑的过程中遇到的痛苦,却逐渐忽略、削减、丧失了对感性真实的最大尊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中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就越难顺应本意地写作,就越难真正成功地产出真诚而灵秀的作品。
《小心眼》“真”得可爱,还在于孩子的天地也反照着成人的世界。对成人世俗世界的反思,是我们读者透过孩子清澈的眼睛而得到的,是通过孩子真诚的声音而触发的。从写作的动机上来说,小作者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要反映成人的世俗世界,但从阅读的空间上来看,这个简单的小天地又衍生出了另一个既相对立又相衔接且彼此影响的大世界。以最朴素的真诚去尊重感性真实,不独这种真诚会打动我们,表现的感性真实也是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的一面镜子。
天真,并非无知或愚蠢,而是人与感性世界作出的一种真实联系,是一种比理性意义更为优先的心理经验。就像在书法美学中,天真、古拙反而是至为完备的“古法”,而这种“古法”,却从未在初学的孩子手中断绝。再联及在文学创作里颇具影响力的天真叙事法,那种尽量去掉理性操控、力求接近感性真实的原生状态以让天真世界和经验世界之间形成对话的艺术手法,又何尝不是一种返璞归真呢?这是一种非常健康而自然的态势,可以说作文写作中散发出来的这种“真”美不仅深深地打动着读者,也激发了我们去认真反思教师对感性真实的尊重状态。——面对青少年的写作空间,我们又是否在起点上做到了尊重感性真实呢?对理性逻辑的锤炼近乎偏执地追求时,我们是否就已经迷失了最根本的写作精神与审美土壤?对一己所认可的有限真实与理性经验之外,我们是否也对他者的生命体验予以了最大程度的尊重?
尊重感性真实,对作文写作而言,意义恐怕并不止于对真诚态度的极大珍视、对写作灵性的精心呵护、对生命写作的精神和意义的积极倡导,从社会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我们自身存在的真实世界最基本的尊重,从创作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创作活动的源泉和审美活动的起点作着重新审视。
相遇:珍视感性关联
尊重真实的感性世界,尊重个体独特的感知和体验,我们自然也会珍视事物之间感性的关联,而非一味斥拒所谓“无关”。唯有胎生于感性真实的写作,才能珍视感性关联,才能迥异而出,独具陌生惊奇之象,唤起读者多元的生命体验,并留有不断再生的空间。因而,破除绝对理念,放下离析惯性,珍视感性关联,才有可能扯开魔幻的帷幕才能进入写作的化境。
所谓“月落百川,处处皆圆”,生命之间的联系总是相互融通的。“以一物而观万物,以一圆而达万圆”,以生命个体而观生命整体,而知生命结构之共通、圆足,物物人人之间的关联便绳绳相续,绵绵再生;又如佛家所言“因陀罗网”,着一花而得净土,着一土而晤如来,物物人人之间,一便是一切,一切便是一,真意就在一花一土的感性之中。
纵观近年泛滥的说理性作文写作,正是不着一花一土而裸求真意,致使物物之间不能通,人人之间不可融,结果落得个刻意求真意反倒失了真意的下场。胎生感性真实、珍视感性关联的写作却常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方玉倩同学的《躺在床上》便是一篇典范之作。《躺在床上》着点只是一个普通民工、一张普通床、一个普通需求,却映照了一个无穷大的世界,以及物物人人之间无比深广复杂的关联。
一个特定人、一件寻常事,读者却能从中看到无数人的影子,——这无数人与这个特定人之间,突破了民工的身份或贫穷的身份或底层的身份或病人的身份,而是所有在现实生活中有着简单的需要和真挚的愿望的人,所有在通往愿望的路上会经历挫折或伤害的人,所有在愿望和现实之间会遭遇出乎意料的事情的人,所有在自己的意念与旁人的思维之间会有屏障的人。
一张普通床,却能让读者看到无数张具体意义或隐喻意义上的床,床是每个人在现实与梦境之间的一个重要承载体,而一切在现实与梦境之间供予人栖息的领域,我们也都可以理解出床的意义。好莱坞的大床,能被解读为梦想的温床,它横在一切人眼中,却又给人一切可能的意义。这里,一张放不稳折了脚的床,一张供予不能行走的人躺卧的病床,一张博大、包容、温馨的地床,三者之间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将读者卷入到对人生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对命运的思考,甚至还会有对我们自身生命存在的思考、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思考。“躺在床上”也就隐寓了一种普适的意义,即我们每个人都躺在某一张床上,这张床可能让我们苦恼,也可能让我们幸福,可能预示着不幸,也可能给予着安适,并且这张床紧紧地连接着两个有距离的世界,成为我们的生命不可逃离的托盘。而“躺着”最大的意味,则是意念的世界和行走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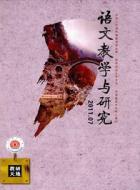
- 作文教学中的宏观驾驭与微观把握 / 陈文华
- 以生活为切入点进行作文教学 / 司徒妙英
- 作文中的描写技巧 / 褚兴梅
- 寻找多元解读的可能性 / 侯红宝
- 基于生活视域的语文作业设计策略 / 沈寿鸿
- 对一道思考题的思考 / 杨锦全
- 我们要砸烂作文新八股 / 魏润身
- 作文写作与感性美学 / 谭根稳
- 作文新八股结构批判 / 万永翔
- 材料作文易出现的误区及应对策略 / 林勇
- 警惕背离人本的作文教学 / 王俊杰
- 试论语文的情趣教学 / 张绍琼 李文忠
- 微语文教与学的基本特点 / 鲍国富
- 试谈课堂教学的点缀艺术 / 宋国侠 杨志勇
- 古典诗歌教学的三重目标 / 王万平
- 语言品味应紧扣那些细处 / 杨帆
- 使用标点符号应注意的问题 / 祝佩华
- 语文课堂教学实施有效管理研究 / 赵国卿
- 语文板书五法 / 马昭文
- 从山城到都市 / 邓方
- 语文课堂不能是中庸的和谐 / 尹磊
- 校园文学社团与校园文学报刊 / 晓苏 刘德旺
- 《渔父》中屈原“宁赴湘流”的另类解读 / 孟凡军
- 对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冷思考 / 卢卫东
- 近五年中考文史结合题型分类例说 / 吴霞霞 刘伟
- 《归去来兮辞》重要词语考辨 / 王旭东
- 文本解读中叹词添加微探 / 刘志勇 刘丽丹
- 《赤壁赋》和《游褒禅山记》比较阅读 / 金雅萍
- 《智取生辰纲》创新教学设计 / 刘宏业
- 阅读教学中切入点的选择和运用 / 陈海
- 黄家山上桃李芬芳 / 刘豫 李永健
- “闰土”与“旧毡帽”的形象比较 / 袁善来
- 鲁迅小说中的死亡现象举隅 / 李秀君
- 耕耘在这片红色热土上 / 张少莉 宋金华
- 站在三个层面上学好语文 / 吴数金
- 语文教学中自然科学知识的教学 / 谢英杰
- 回国观感 / 汤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