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2年第5期
ID: 136876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2年第5期
ID: 136876
语文学科的理性回归之路
◇ 郑文华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都表现为范畴的逻辑体系。这个范畴的逻辑体系,必定含有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抓住了这三点,才算抓住了一门科学理论的‘纲’”①。它们“在方法论上具有特殊的意义”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对此做过科学阐述。他的这些思想,为我们建构语文学科理论体系,探索语文学科的理性回归之路,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指导性线索。
本文着重讨论语文学科的逻辑终点问题,期望借助逻辑思辩,在语文本体、语文内涵、学科性质和学科对象等方面形成一些新的认识。
一、语文学科逻辑终点的形成过程
语文学科既然以语言作品为逻辑起点,就意味着语言作品要经历一个辩证的否定的过程,直到“在终点中实现”它自己。这个辩证的否定的过程,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的行程”,它包含在作为逻辑终点的语言作品中。
1.抽象的开端
语文是由语言和言语、文章和文学诸要素构成的一个整体,其中每个要素相对于整体来说都属于具体的东西,都是多样性、多规定性的统一,事实上已经有多个前提了,因而它们都不能作为整个语文学科的起点范畴。只有在语言学、言语学、文章学和文艺学的概念框架中,它们才是最抽象的,才构成各自学科的起点范畴。语文学科的起点范畴,只能是上述全部要素的最后抽象,即它们的上位概念范畴——语言作品。
作为起点范畴的语言作品,只具有简单的规定性,如它是成篇的话语、发生并作用于人与人之间、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等。尽管如此,它却内在地包含了语文学科的全部规定性,包含了思维进程中的全部发展,因而它是“全部科学的根据”。同时,它又以终点范畴为目的,以实现了多样性、多规定性统一的“语言作品”为归宿,唯有达到了这个目的和归宿,它才是语文学科体系的“现实的起点”。
2.具体的结果
从最初的、抽象的语言作品出发,不过是向具体的、表面的语言作品返回,在思维的进程中,一个规定性一个规定性地复原丰富的整体。例如从语言作品起点范畴出发,根据其形式范畴可以演绎出语言和言语范畴,显现出语文的工具性;根据其内容范畴可以演绎出文章和文学范畴,显现出语文的人文性(思想性、审美性)。
作为终点范畴的语言作品之所以“具体”,就是因为它从“抽象”始,以“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语言和言语、文章和文学,以及阅读和写作、听话和说话等“具体的再现”,它是许多规定性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③需要注意的是,由抽象始到具体终,是科学任务的完成过程,它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正是在这里,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具体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④
作为起点范畴的语言作品,是尚未展开的、尚未实现的语言作品;作为终点范畴的语言作品,是已经完成了的、各种规定性全面复归了的语言作品,它整个地表现为一个圆圈,即最初的东西展开为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东西也将是最初的东西。这个思维的进程与历史的进程是一致的。语文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语言作品的发展历史,而语言作品的发展历史就是其内在矛盾的展开过程,如从最初的语言现象,到索绪尔区分的语言和言语;从最初指一切口头或书面的语言行为和语言作品的文学,到后来逐步区分开来的实用文章和纯文学。“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的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⑤因此,通过语言作品起点在终点中的实现,语文学科在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中完成了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抽象。
3.话语的中介
根据法国思想家福柯等人的研究,语言作品是指由语言和言语结合而形成的、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即话语或话语实践⑥。所谓话语,是指在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含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把语言作品不简单地看作是语言或言语,而是视作话语,是为了突出语言作品的基本属性:它绝不只是个人的东西,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活动;它也决不只是个人的言语行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话语实践。
语言作品本质上属于话语实践,属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其最终根源就在于人的自由创造。话语实践事实上就构成了贯通语文学科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的逻辑中介。
二、语文学科逻辑终点的基本特征
如上所述,语文学科以抽象范畴的语言作品为逻辑起点,以具体范畴的语言作品为逻辑终点才是科学的。那么,作为逻辑终点的语言作品范畴具有哪些基本规定或特征呢?
1.语言作品终点是最丰富的范畴
我们知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马克思把它概括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把具体复制出来”的过程。作为起点范畴的语言作品,是最单纯的、最无内容的、最少规定的范畴,是“最简单的形式”、“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在那里,还没有语言和言语之分,也没有文章和文学之别)。在从抽象起点到具体终点的辩证的否定的过程中,将逐步加进语言和言语、文章和文学的规定性,从而使单纯渐次变得丰富起来。“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因为结果包含着自己的开端,而开端的运动用某种新的规定性丰富了它……在继续规定的每一阶段上,普通的东西不断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了什么,丢下了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物,使自己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认为黑格尔的这段话,对于什么是辩证法的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总结。⑦
2.语言作品终点是最复杂的范畴
作为抽象范畴的语言作品,因为最少内容和最少规定性而变得简单。与此相反,作为具体范畴的语言作品,却因为规定性增多、内容丰富而变得复杂。话语交际范畴实际上就是人们心灵交往关系的理论表现。借用哈贝马斯的话来描述,这种关系就是围绕着作品这个中心,作者与世界、读者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话语伙伴关系,它包括作者与自我、现实他者(自然和社会等此岸世界)、超验他者(彼岸世界)、潜在他者(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可见这个丰富的范畴,表现着多种交往关系的相互渗透,以及各种原生和派生关系的相互交错,我们谓之“交际关系”。当然,由最简单上升到最复杂,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辩证的否定的过程,因而作为终点范畴的语言作品虽然最复杂,但也必定是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排列的,必定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
3.语言作品终点是最现实的范畴
作为抽象范畴的语言作品,是对具体、实在即现实范畴的更切近的规定,以至达到“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稀薄”、直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与此相反,作为具体范畴的语言作品,是对抽象范畴的语言作品的更切近的规定,以至最终达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个丰富的总体,就是对现实的最终返回,是对现实的再现、复制。⑧在范畴的逻辑体系中,也只有最具体的范畴更接近话语的现实,接近话语实践的表面、实在。
4.语言作品终点是归宿性的范畴
既然在思维的进程中,已经将现实的丰富的交际关系综合起来,那么对交际关系的特定考察的任务就告完成。这样,作为具体范畴的语言作品就必然“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⑨不过,结果性、归宿性、终至性,只具有逻辑体系的意义,它并不表示现实的话语实践在此终止。相反,逻辑终点只是向逻辑起点的回归,具体的终点本身就隐伏着新的“抽象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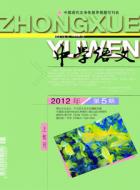
- 语文学科的理性回归之路 / 郑文华
- 语文课堂“诗化教学”论 / 毕泗建
- 语文教师专业知识发展的有效路径探索 / 陈元辉
- 欣赏小说的表达技法 / 余映潮
- 以表现性评价引领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实施 / 胡根林
- 亲情的呼唤,渐悟的愧怍 / 何庆华
- 关注文本言语特征探寻文本细读点 / 陈金兵
- 长江大桥之“大” / 张文敏
- 简约背后的精彩 / 陈华琴
- “四单导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毛高阳
- 说“小X” / 赵曼卡
- 从《鉴赏家》看汪曾祺笔下的人情美 / 顾乐远
- 散文教学内容确定的理据分析 / 成龙
- 说“各行其道” / 许金玲
- 例说《外国小说欣赏》教学内容的确定 / 林文源
- 阅读教学中强化“差别感受性”的途径 / 钱建江
- 对话充分 激情洋溢 / 李良永 李爱梅 李茂国
- 以说辩促写作 以写作促阅读 / 王湘英
- 确立课程视角 坚持语文本体 / 杨高旺
- 立体思维的三个维度 / 明学圣
- 关于语文“导学案”若干不足的反思 / 陈松泉
- 我这样教《欧也妮.葛朗台》 / 庄学培
- 作文评价要关注学生的写作心理 / 李彬
- 借得批注三分味 添与阅读一缕香 / 宋登水
- 一部有效教学研究的力作 / 王光龙
- “笨”字原本无贬义 / 陈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