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1期
ID: 136435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1期
ID: 136435
作为交际方式的语文
◇ 郑文华
要科学把握“交际问题”,关键在于准确理解“交际”的含义。
在常识层次的概念框架中,“交际”是一个多义词,英语称之为Communication,有“通讯、交流、传达(意见)、交换”等多种含义。汉语中“交际”的“交”有结合、通气、赋予的意思,“际”有接受、接纳、交合、会合、彼此之间的意思,“交际”泛指人与人之间的应酬。①这是人们以一种依附于经验的表象思维方式,对行为方式的“交际”所作出的解释,它是科学层次的“交际”概念赖以形成的基础和前提。
在科学层次的概念框架中,“交际”概念具有不同于常识层次的性质。例如,在行为科学中,交际是指“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感情、思想、态度、观点等的一种行为。”②在语言学中,交际是指“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使用一套代码传递或交换信息的过程。”③而在文艺学中,交际被理解为“沟通”,“是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通过文本阅读而达到的相互了解或融洽状态,这是话语活动的目的”④。这些“交际”概念有一个相同点,就是立足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把“交际”理解为彼此之间传递信息的行为或过程。
但是,哲学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概念”都只能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中获得相互规定和自我规定,实现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⑤。语言学和文艺学,虽然跟语文学联系最为密切、最为复杂,但由于概念框架不同,它们之间,以及它们跟语文学之间,其“交际”概念的内涵应该具有差异性。语言学中的“交际”概念,与语言、言语等概念相互规定和自我规定;文艺学中的“交际”概念,与话语、审美等概念相互规定和自我规定;语文学中的“交际”概念,同样必须并且只能在语文学特定的概念框架中,与语言、言语(文章、文学)等概念相互规定和自我规定,才可能获得其意义。
可令人遗憾的是,“语文”独立设科百年,却一直没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名为“语文学”的学科,人们通常把语言学、文艺学和文章学这三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逻辑基础,也并没有纳入一个更大的独立系统的研究范畴”的学科,当作“语文”的学科基础⑥。也就是说,语文学并没有自己特定的概念框架。在这种情况下,“交际”这个事关语文学科根本性质的概念,长期以来就只能到语言学中去“拿来”。这种“拿来”,一方面固然落实了“交际”寓之于外的内涵——传递信息;另一方面却回避了“交际”寓之于内的内涵——创造信息。这样与其说是对学科之间同一性原理的运用,不如说是语文学科个性的自我放逐,因为它取消了语文学科内部的主要矛盾——信息传递(言)和信息创造(意)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瓦解了语文学科的概念运动,无法通过语文学科特定的概念框架,实现“交际”等概念的相互规定和自我规定、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这或许就是语文独立设科百年却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的核心概念的真正原因。
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作为学科的核心概念,必须能告诉人们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这门学科的原因,以及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而这些,语文学科都无可奉告。语文学科没有自己的核心概念。核心概念是概念对象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在一类对象中,扬弃每一个具体对象的个别性和特殊性,抽象出该类对象共同具有的、本质的和普遍的属性。语文学科的“一类对象”,是语言、言语,言语之下是文章、文学。文章的本质在于创造思维信息,文学的本质在于创造审美信息,二者统一于信息创造,并以语言形式下的信息创造进入言语范畴。言语是交际行为,语言是交际工具,二者因个别性、特殊性——“行为”和“工具”而彼此分立,又因共同的、本质的和普遍的属性——“交际”而成为一个整体,这个“交际”的整体就是“语文”。这样,“交际”就构成了语文学科“一类对象”的最后抽象,构成了语文学科概念自身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交际”概念的形成过程,其中所用的方法,逻辑学上叫做“逻辑抽象”。
当然,“逻辑抽象”只能让我们获得属于最后抽象的概念,却不能让我们明确反映这个概念中的对象的本质属性。因此,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运用“语文的”思维方式,对“交际”这个概念的内涵作出明确界定。
上述“逻辑抽象”过程表明,“交际”的内涵主要由两种思维要素构成:一种是传递信息(语言),一种是创造信息(言语)。从人的实践上看,它们具体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目的指向:一种是与他者的沟通指向,它体现着社会学意义上的交往价值;一种是与自我的创造指向,即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他自身”,它体现着哲学意义上的人的价值。在“交际”范畴内,“沟通”寓之外,“创造”寓之于内,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前提。没有“沟通”的发生,就不会有生活意义的“创造”;反之,没有生活意义的“创造”,“沟通”也只能是痴人的胡言乱语。对于“交际”而言,这两种指向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不并意味着“交际”的两种指向必然会同时出现在人们的认识视域中,恰恰相反,不同的学科视角会带来不同的“交际”指向。例如,在语言学中,“交际”明确指向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生活意义的创造则以背景方式存在;在哲学中,“交际”明确指向生活意义的创造(“意义即使用”),而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则以背景方式存在。但是,语文学毕竟不是语言学,也不是哲学。语文课的基本目的在于培养“听说读写四项本领”,这个基本目的决定了语文课必须把“交际”看作是一个整体,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有目的和有意识的“自由创造”。它具体表现为主体在实践中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对象化”为一种客体实在——言语作品,用来满足他者的阅读(聆听)需求,并且在自己所创造的言语作品中“直观他自身”,用来体现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力量。这两方面因素既相互矛盾、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依存、互为前提,“交际”就是这种矛盾统一的关系,以及这种矛盾的普遍必然性的深刻体现。它意味着语文课必须且只能是“沟通”和“创造”的辩证统一,是“沟通中的创造”或“创造中的沟通”,由此产生语言的必需和言语的必行,产生文章的思想和文学的审美,产生人与语言、人与世界、人与他者、人与自我的结构性联系,以及作为这种结构性联系的产物的言语作品。归而言之,语文课的“交际”,就是在一定的言语范式主导下交际主体运用语言创造并传递信息的过程。其中,“创造并传递信息”是“交际”概念的基本内涵,因而也是反映在“交际”这个概念中的语文的本质属性,我们称之为语文的“交际性”。所谓“交际问题”,在现象层面上就是指“怎样听说读写”的问题,而在本质层面上则是指“怎样运用语言创造并传递信息”的问题。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其一,“交际”内含传递和创造,但它不是传递和创造,更不是传递或创造,而是传递和创造的关系性存在。“交际”只存在于传递和创造的特定关系中,离开这种特定关系,“交际”就不具有“语文的”本体论意义;同时,“交际”使传递成为“这个”传递,也使创造成为“这个”创造,离开“交际”,传递就不再是“语文的”传递,创造也不再是“语文的”创造。其二,“交际”的传递和创造,当类似于人的左眼和右眼,隔而未隔、界而未界,存在着视域融合。“艺术开始于形式开始的地方”(维戈茨基),但是“要一句‘新’的诗出现,还得依赖一种‘新’的思想生成”(威廉斯),因而作为“交际”概念的两种思维要素,传递和创造总是协同存在的。其三,“交际”涵盖语言和言语,但它不是语言和言语,也不是语言或言语,而是关于语言和言语的本质抽象。“交际性”规定了工具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但它不是“语言的工具性+言语的思想性”。其四,“交际性”规定了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的统一,它使形式成为“这个”内容的形式,又使内容成为“这个”形式的内容,所以人们常说“形式即内容”,“在艺术作品中,形式变成内容,反之亦然。喜剧、小说是靠形式而成为文学作品”(马尔库塞)。其五,“交际性”规定了语言和言语(文章、文学)的存在及其位置,并把它们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它是关于这个整体的本质规定,体现多种规定性的统一,让语文最终“成为他自己”,把语文课和非语文课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但是,它不能取代或者消解各组成部分的个别性质。此外,也不能把作为现象的“交际”和作为本质的“交际”混为一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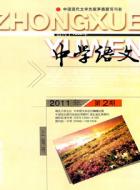
- 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与语文课程改革 / 吴格明
- 作文的本源及其对应的训练体系 / 王相武
- 困惑中思索:语文教学的可能走向 / 杨 旸
- 活化教法,提高教学效益 / 章移珠
- 高三,记叙文写作的瓶颈及应对策略 / 钟 斌
- 作为交际方式的语文 / 郑文华
- 谈“小贵” / 肖 兆
- 思想的蜕变与超越 / 贾小林 晓 喻
- 话说课文修改及其他 / 张厚感
- 物量词“个”的动量化 / 刘 慧
- 语文教科书中幽默语篇稀缺现象之透视 / 黄志军
- “裸”的新义和“裸X”新词 / 李 淼
- 何谓懂得语文教学 / 余映潮
- 《道士塔》的语言表达特色 / 李 华
- 向度 尺度 效度 / 袁 菊
- 要有会看夜的眼睛 / 钱理群
- 《药》教学实录 / 刘永康 朱大伦
- 字形考点:注意测试的综合性 / 李德伦
- 关于细读文本的三点新思考 / 施清杯
- 语言的局限性与活动的可能性 / 胡根林
- 谈选修课的引导探究之道 / 孙志玲
- 为孩子播下思索的种子 / 李爱梅
- 《选读》课堂教学面临的问题与出路 / 杨仕威 应慈军
- 语文教学中的学生主体参与 / 葛德均
- 作文应该是淌出来的 / 杨云法
- 高效课堂的核心 / 陈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