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2年第5期
ID: 136885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2年第5期
ID: 136885
关注文本言语特征探寻文本细读点
◇ 陈金兵
语文教学就是要引导学生在听、说、读、写的综合学习实践活动中理解和运用好祖国的语言文字,提高对语言的敏感度、感知力,用语文的方法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发掘、捕捉显性和潜在的语言信息,不断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
但是,在考试分数的利益驱动下,一些语文课变成了考题解剖课、技术分析课,老师和学生都已经没有耐心来关注文本,更谈不上细读文本,谈不上关注语言文字的表达形式。语文课丧失了之所以作为语文的基本特征,“语文味”荡然无存。
语文老师应该如何坚守“语文”的阵地?
一、关注言语特征,回归语文本真
语文教学中应该聚焦于什么?王尚文教授曾说:“语文教学的聚焦点应该是‘言语形式’即‘怎么说、怎么写’,而非‘说什么、写什么’”。因此,着眼于文本的言语特征进行细读,回归到体现语文自身特征的语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当前责任。语文教学只要守住了“言语形式”这个门槛,那语文课就一定能上成语文课,而不是别的什么历史课、环保课、班会课了。但是,文本的言语特征又是为人难以关注、难以发现的,语文教师就是要善于发现文本呈现的言语特征的秘密而采取可行的方式进行教学,引领学生在文本的细读中品味语言艺术,体味文本内涵,感受文本核心价值,形成学生相应的“语文素养”。
二、基于言语特征,探寻文本细读点
从言语出发,关注文本的言语特征,使文本的研读有所依托,为细读文本创设教学路径。王先霈所指的“细读一定要从文本实际出发,紧扣文本的文字”就是指要紧贴言语特征,“引发一种对语言的敏感”。而言语特征是文本写成以后自然呈现出来的词句、文法特征,体现了作者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思维特征和个性风格等。不同文本的言语特征也是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面对一个全新的文本,从怎样的路径开始细读文本?笔者在多年的教学中发现,可以从言语呈现出来的形式特征、内容特征、情感特征三方面寻找文本的细读点,深入文本的言语世界,潜心细读,用心品味,带领学生沉醉于语文的世界。
1.关注言语的形式特征,探寻形式的细读点。
一个独立的文本,在言语表达上必然呈现出一些形式上的特征,比如词语方面口语俚语、书面语、文言雅词、褒贬词等的运用,句式方面整句与散句、反问句、双重否定句、主动句与被动句等的运用,修辞方面比喻、排比、反复等的运用,写法方面对话体、书信体、第一人称、正反对比、衬托渲染、先抑后扬、象征等的运用,表达方式方面抒情、描写、记叙、议论、说明的选用等,都呈现出明显的形式特征,也正是这些形式,将原本一个个彼此独立的词语连缀在一起,形成富有一定意义的“语言流”,“统率”起文本内容,成为深刻、丰富的“思想流”。语文教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引导学生关注这些形式特征,让学生学会从言语的形式中发掘文本的特殊信息。这样的形式特征,表现出的面貌是多样的:
(1)词语统领。文本中的一些词语,往往在言语形式上成为具有关键性作用的词语。如在《沁园春·雪》中,“望长城内外”中的“望”统领了此下的几句: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下阕的“惜”字也一样,统领后面的诗句。
“望”与“惜”二字还在结构上,形成上下两阕遥相对应的形式特点,循着这样的形式特征进入文本的细读,显然就容易多了,词人借用这两个词所承载的思想内容、情感价值全在其中。“望”是写眼前所见之景,“惜”是抒发心中所感之情,“望”的是北国广袤辽阔的高原雪景,“惜”的是历代建立文治武功的赫赫帝王,由景到情,由所见到联想,由实到虚,词作所包容的革命豪情、英雄气概、雄心壮志跃然纸上。这样的关键词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引导学生自主慢慢发现,用心细细品味,一定能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追求的那样,让“词深入到儿童的精神生活里去”,“使词在儿童的头脑和心灵里成为一种积极力量”,成为“他们意识中带有深刻内涵的东西”。
(2)句子串联。文本中的一些关键性句子,往往承担了串联全文、连缀结构的作用,从这样的句子出发细读文本,同样事半功倍。《岳阳楼记》中的几个关键句子别具意味:
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带着学生找出它们,放在一起,不难发现作者写景抒情的思想脉络了:先总的发问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有无异同,再分写“霪雨霏霏”、“春和景明”两种特质迥异的景色,表达“感极而悲”和“喜洋洋”两种色彩迥异的心理感受,由总而分的文章结构一目了然,由晴景而喜、由雨景而悲,自然与结尾的“古仁人之心”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超然就顺势成为了文本思想境界最合理的提升。这样的关键句,在文本的言语形式上所形成的特征,比较显著,学生也易于发现,教会学生抓住这些特征,逐步领悟语文学习的妙诀。
(3)段落对应。文本段落呈现出来的形式特征往往也不容忽视。王先霈教授在《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一书中提及“曾经有俄罗斯诗人认为,研究诗歌形式要从诗行着手”,“在文本细读中,汉语诗歌的诗行也还是应该注意研究”,就是指明了文本段落章节排列上的形式特征,也是我们教学的价值所在。这在诗歌中比较多见。人教版九年级上册的《星星变奏曲》是江河的一首有代表性的朦胧诗,此诗共有两个小节,在印刷出来的课本纸面上前后排列,并无稀奇,稀松平常,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如果把这两小节诗放在同一个页面,左右排列,你会发现(如图1):
每节都是16行,行数相等;再进而会发现,每节的第1——4行都是“如果大地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光明/谁还需要星星,谁还会/在……中/寻找……”,每节的第13行都是“谁不喜欢……”;更奇妙的是,第1节的第5行、第10行分别是“谁不愿意”和“谁不愿意……”,而第2节的第5行、第10行则分别是“谁愿意”和“谁愿意……”。如上,句式在段落中的规律性出现,隐性地构成前后段落对应呼喊的关系,两节诗中相同的是都以假设关联词“如果”开头,在两个“如果”的反复中强调“大地的每个角落”还没有“都充满了光明”,强调了创作本诗的事实起点;两节中“谁不愿意”句和“谁愿意”句的对比表达,使这种原本句式的对比上升到了段落的层面,构成了段落间结构与诗意在整体上的对比应答,形成强大的结构张力和反问力量,把诗人对理想的渴盼和对现实的控诉与无奈,一一呈现在诗行。
言语在词语、句子、段落上呈现出来的这些形式特征,给读者提供了进入文本、细读文本的线索。线索所在之处,就是文本的细读点。从此出发细读文本,便于学生快速进入文本的世界,对话文本,感受语文的魅力。
2.关注言语的内容特征,探寻内容的细读点。
言语形式不可能脱离言语内容。“面对同一个事实,不同的人可能会用不同的言语形式去表述”。因此,本文关注文本言语上的特征,并不排斥言语内容的显性存在;言语特征也有内容性特征的表现,从内容维度表现出来的言语特征,是文本的重要言语特征,是文本的重要存在形式,也必然透露了内容所选择、所依托的表达特征。发现这些特征,也可以及时确立细读点。
(1)列举分承。文本在铺陈某种场面时,或在阐述一种观点时,常常在内容的出现上表现为“列举分承”的特点。人教版八年级下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第3节,一共5句,则分别写了“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四大场景,不紧不慢,一路悠悠叙来,分个列举,分别描写,把太守与民同游、同宴、同饮、同醉的太守形象生动而全景式地刻画了出来,致使“与民同乐”的太守形象、“与民同乐”的太守治理、“与民同乐”的太守理想的三大主题内容清晰、全面呈现。在如上内容的呈现中,我们可以从言语的造句法中看到内容所依托的媒介:“滁人游也”、“太守宴也”、“众宾欢也”、“太守醉也”,四句后都跟了个“也”字,在言语形式上构成判断句,且是典型的主谓句,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所呈现的内容却围绕“与民同乐”的中心而环列四面,这样独特的言语在内容上所表现出来的内容特征,何尝不是文本细读的蹊径?如果此种特征出现在议论文中,内容上的“列举分承”就常常表现为围绕中心论点而作的分论点阐述。同样的,虽然言语是从内容入手而写,但呈现于文本,就难免不显露出言语特征的蛛丝马迹。一旦为读者捕获,就成为了解读文本的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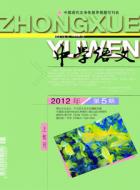
- 语文学科的理性回归之路 / 郑文华
- 语文课堂“诗化教学”论 / 毕泗建
- 语文教师专业知识发展的有效路径探索 / 陈元辉
- 欣赏小说的表达技法 / 余映潮
- 以表现性评价引领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实施 / 胡根林
- 亲情的呼唤,渐悟的愧怍 / 何庆华
- 关注文本言语特征探寻文本细读点 / 陈金兵
- 长江大桥之“大” / 张文敏
- 简约背后的精彩 / 陈华琴
- “四单导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毛高阳
- 说“小X” / 赵曼卡
- 从《鉴赏家》看汪曾祺笔下的人情美 / 顾乐远
- 散文教学内容确定的理据分析 / 成龙
- 说“各行其道” / 许金玲
- 例说《外国小说欣赏》教学内容的确定 / 林文源
- 阅读教学中强化“差别感受性”的途径 / 钱建江
- 对话充分 激情洋溢 / 李良永 李爱梅 李茂国
- 以说辩促写作 以写作促阅读 / 王湘英
- 确立课程视角 坚持语文本体 / 杨高旺
- 立体思维的三个维度 / 明学圣
- 关于语文“导学案”若干不足的反思 / 陈松泉
- 我这样教《欧也妮.葛朗台》 / 庄学培
- 作文评价要关注学生的写作心理 / 李彬
- 借得批注三分味 添与阅读一缕香 / 宋登水
- 一部有效教学研究的力作 / 王光龙
- “笨”字原本无贬义 / 陈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