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2年第5期
ID: 136894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2年第5期
ID: 136894
阅读教学中强化“差别感受性”的途径
◇ 钱建江
新课改中,对于语文阅读教学的认识,人们比较关注阅读方式的变化——由传统的“肢解式讲析”阅读行为,转向“整体性阅读”行为。应该说,语文阅读方式的转变,是新课程改革中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以“整体性阅读”思维组织的课堂教学,是遵循科学的阅读理论和符合人类认知规律的教学行为。然而,在推进“整体性阅读”的过程中,不少教师没有注意到关于“阅读”的另一组关系:“感知性阅读”(也可以称为“理解性阅读”)与“感受性阅读”。很多课堂阅读教学行为,看起来在进行“整体性阅读”,但是这种“整体性阅读”只是停留在“理解性阅读”这一层面上,而没有达到“感受性阅读”的层面。这既有教师思想认识方面的不足,也有应试导向方面的影响。在中考高考的阅读试题中,命题者很大程度上偏重于命制“理解性阅读”试题,这等于确定了以理性分析为主的阅读取向,这种阅读最多可以称之为“理性的整体阅读”,而不是真正的新课程阅读理念下的“整体性阅读”。
一、“感受性阅读”与“感知性阅读”的区别
从心理学上来讲,“感受性”是指感觉系统对刺激物的感觉能力。在阅读教学活动中,“感受性”特指教师或学生对语言以及语言所表现的形象、情感的接受能力。“感受性”与“感知性”一样,是一个过程性的动词。
如果说“感知性阅读”是指向语言和文本意义的一种阅读取向,它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的阅读获得相关信息,那么,“感受性阅读”则是通过语言的感知进而指向情感的激发和共鸣,它是对语言及其表达内容的感同身受,所谓“目击事物,便以心击之”,便是这个道理。
这里,我们必须搞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感受性阅读”中往往包含着“理解性阅读”,一般而言,“理解性阅读”是“感受性阅读”的基础。例如阅读《铃兰花》(见苏教版高中选修教材《现代散文选读》)一文,读者理解了“铃兰花”的象征意义,然后就能进一步感受到“铃兰花”里蕴涵的母子深情等更丰富的意味。另一个是“感受性阅读”中的差别感受性问题。一个人的差别感受性越强,他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感受就越丰富。例如《望月怀远》(见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唐诗宋词选读》)一诗,“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中的“怨”字,差别感受性弱的人,或许只能感知其中蕴涵的“怨恨”这一种含义,而差别感受性强的人,就能感受到“怨”字的多重意味:怨恨长夜漫漫,孤单凄凉,令人夜不能寐;怨恨情人远隔天涯,难以相见,只能望月长叹;怨恨相思之情挥之不去,拂之再来,乃至通宵。
课堂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系统”或“能力系统”,更是一个“情感系统”和“生命系统”。“情感”与“生命”重在感受。在语文阅读教学研究中,不少专家学者在强调“语感”——人的言语感觉、言语感受力、言语感悟力的特性,即在“直觉性”和“感性”的基础上,更明确提出语文学科要“以优秀的言语作品吸引他们,点燃他们的感知、想象、情感、思维,广化、深化、美化、敏化他们的语感……不断趋近课文作者——真正的人、优秀的人的精神境界,使他们也成为真正的人,优秀的人”。倡导感受性阅读,正是“为了突出学生阅读行为的自主性,重在感受体验,整体把握。在阅读目标上强化感受性、体验性,就是为了与长期流行的理性化阅读分析相抗衡。”
二、感受性阅读中“绝对感受性”与“差别感受性”的区别
“感受性”是感觉系统功能的基本指标,可用感觉阈限来衡量。“感受性”又有“绝对感受性”和“差别感受性”之分。刚能引起感觉的最小刺激量称为“绝对感觉阈限”,与之相应的感觉能力称为“绝对感受性”;刚能引起差别感觉的刺激之间的最小强度差,称为“差别感觉阈限”,与之相应的感觉能力称为“差别感受性”。简单一点说,一个感觉敏锐的人,他的“差别感觉阈限”就小,就能感受到事物的细微变化;一个感觉迟钝的人,他的“差别感觉阈限”就大,能感受到的往往是比较粗放的东西。因此我们应该努力缩小自己的“差别感受阈限”,这样在阅读中获得的感受必将更加丰富。
人的各种感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受内外条件的影响,例如适应、对比、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生活需要和训练等,这些内外因素都能导致相应的感受性的变化。在语文阅读中,一个人的“差别感受性”也是可以发生变化的。经过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对文本细节的敏感性也会得到强化,他们对蕴藏在语言细微处的意义也能加以涵泳,从而得到更多更微妙的体会。事实上,在阅读教学日益精细化的状态下,谁的差别感受性强,他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情感积淀就多,他的精神世界就越丰富。
三、阅读教学中如何强化学生的“差别感受性”
在感受性阅读教学中,可以感受的领域是广泛的,笔者将另文撰述。下面从思维训练的角度谈谈阅读教学中如何强化“差别感受性”。
尽管语言不同于声音、光线和重量,人对语言的感受性也不同于听觉、视觉和触觉,难以科学测量语言感受的“差别性”,但是,在阅读教学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很多途径,来培养和强化学生阅读中的“差别感受性”。
1.巧设“比较点”。
“比较”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最朴素的方法,“比较”也是一种思维过程。在语文学习中,主要是通过比较语言形式的差别,来感受语言所表现的情感的差异。可以说,运用“比较”的方法,最能体会到“差别感觉阈限”的程度变化。一般而言,大部分文章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比较点”,汉语的近义词相当丰富,作家写作时往往会从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或句子中,选择最准确,最生动,最有表现力的词语和句子,来表达独特的思想情感。教学中,就可以巧妙地设置词语或句子的“比较点”,让学生在比较中感受语言细微的差别对情感表达的影响。例如笔者在执教《风筝》(鲁迅)一文时,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多种版本的鲁迅文集里,大多数写作“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而现在苏教版教材中用的是“抓断”,请问究竟用哪个词语好呢?学生探索问题的兴趣被激发起来,通过比较,学生指出与“折”字相比,“抓”字更能显示气急败坏的样子,表明“我”的冷酷无情,扮演着“精神虐杀者”的角色。在比较中,凝聚在“抓”字上的一份特殊情感,很快被学生感受到了。再如笔者执教《再别康桥》(徐志摩)时,提出问题:第一节中的“轻轻”和最后一节中的“悄悄”能不能互换?学生在细斟慢酌中,感受到“轻轻” 是客观状态,“悄悄”是主观意向,结尾处用“悄悄”一词,表露出诗人不愿掠动心爱的康桥的一片温柔情意;这一节不是对第一节的简单重复,而是体现出了更深的眷恋。
可以设置的“比较点”,除了词语外,还有标点,句式,段落等,如《风筝》中“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句中逗号能否去掉?《再别康桥》中第三节最后一句,人教版教材上写作“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苏教版上为什么要改作“我甘做一条水草”?《铃兰花》中结尾四段在有的版本里是没有的,究竟要不要等等。在比较中,学生的思维变得更敏感,通过长期的训练,他们就能识别细微的语言差别中的不同意味,就能在阅读中更深切地感受到作家欣喜时的欢歌,悲戚时的沉吟,失落时的呼告,愤怒时的呐喊,真正拥有“我打开一本书,一个灵魂苏醒了”的那份独特感受。
2. 觅寻“疑问点”。
《易经》有云:“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恰当的“疑问点”,是开启思维的金钥匙。文本解读中仅针对理解性阅读而作的普通的设问,或许能很好地疏通和阐释文本,却不足以提升学生的阅读感受力,进而提升其批判、思辨能力。因此,教师要努力改变“鉴赏者”的立场,在阅读教学中首先成为一个“感受者”,去发现那些潜在的“疑问点”,抓住不放,启发学生深入探究,获得更具纵深感的文本阅读感受。例如,笔者执教《散步》(莫怀戚)一文时,未从常规处设问,而提出如下疑问:你觉得课文中谁最听话?“我”?“妻子”?“母亲”?“儿子”?在好奇而又饶有情趣的探究中,学生发现一家四口个个都是最听话的,进而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家人尊老爱幼的美德。教师随即提出下一个疑问:文中“我”是个合格的儿子,那么“我”是不是个合格的父亲呢?学生的思维始终保持着被触发的状态,他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指出:“我”伴同儿子的时日还长,与母亲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所以先要考虑母亲;“我”为孩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也是个合格的父亲。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这就是古人所说“人孰能不老,百事当以孝为先”。阅读教学中,通过类似这样的训练,亦能增强学生的思维敏感度,缩小其“差别感受阈限”,进而提高阅读感受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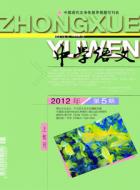
- 语文学科的理性回归之路 / 郑文华
- 语文课堂“诗化教学”论 / 毕泗建
- 语文教师专业知识发展的有效路径探索 / 陈元辉
- 欣赏小说的表达技法 / 余映潮
- 以表现性评价引领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实施 / 胡根林
- 亲情的呼唤,渐悟的愧怍 / 何庆华
- 关注文本言语特征探寻文本细读点 / 陈金兵
- 长江大桥之“大” / 张文敏
- 简约背后的精彩 / 陈华琴
- “四单导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毛高阳
- 说“小X” / 赵曼卡
- 从《鉴赏家》看汪曾祺笔下的人情美 / 顾乐远
- 散文教学内容确定的理据分析 / 成龙
- 说“各行其道” / 许金玲
- 例说《外国小说欣赏》教学内容的确定 / 林文源
- 阅读教学中强化“差别感受性”的途径 / 钱建江
- 对话充分 激情洋溢 / 李良永 李爱梅 李茂国
- 以说辩促写作 以写作促阅读 / 王湘英
- 确立课程视角 坚持语文本体 / 杨高旺
- 立体思维的三个维度 / 明学圣
- 关于语文“导学案”若干不足的反思 / 陈松泉
- 我这样教《欧也妮.葛朗台》 / 庄学培
- 作文评价要关注学生的写作心理 / 李彬
- 借得批注三分味 添与阅读一缕香 / 宋登水
- 一部有效教学研究的力作 / 王光龙
- “笨”字原本无贬义 / 陈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