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2期
ID: 92733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2期
ID: 92733
太白诗风概述
◇ 王波平
“唐代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强盛富庶又是最文采斑斓的时代。唐代不仅经济发达,国力居世界首位,而且文化之繁荣也是世界公认的。唐代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中,产生了两千多位各具风格的诗人,留传下来的诗歌多达五万余首。李白、杜甫更是整个古代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温家宝2006年11月13日《同文学艺术家谈心》载《光明日报》11月29日第二版)有唐一代,诗歌为盛。盛唐诗风,太白属最。最中有醉,醉意浓郁者,乃太白诗风。太白诗风可谓是独树一帜,空前绝后,绝对无法重复和临摹。这也是“诗仙”让人企羡和令人遥望之处。太白诗风的内容宽广,容量闳大。他的饮酒诗,塑造一种“酒徒”和“狂客”的自我形象,展示了他饮酒客的表象和孤独者的内心;他的怀古诗,酿造一种深沉而微妙历史蕴味,显示了他于生活的感喟和人世的感伤;他的游仙诗,创造一种瑰丽又神秘神话世界,揭示了他对现实的认识和时事的见识;他的山水诗,营造一种晶莹澄澈的清新自然,表示了他对自然的热衷和山水的热爱。
一、塑造自我形象的饮酒诗
李白与酒,情致醇厚,酱香浓郁,他对一位老者的怀念可鉴,“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哭宣城善酿纪叟》)李白于酒,贡献深远,回味绵长,他对湖北“白云边”酒的推介可见,“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一)说实话,没有你,中国的酒也许没有如此的畅销,连现代的高阳酒徒也少了一个喝酒的理由。其同时代的杜甫就为我们细致地绘画了一副太白醉酒图:“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塑造了一种“酒徒”和“狂客”的自我形象:纵饮不羁、挥翰如洒、放任自在、笑傲礼法,天赋仙姿,行为特异,不同凡俗,超越常规。
李白是一位高超的饮酒客。醉酒,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之中,流行着一种现实的普遍性,从屈子,到阮嵇,从刘伶,到陶谢,从李白,到欧苏……然而,他们的醉酒,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酒神精神,不是那种情欲的狂欢和本能的冲动,他们仍然是“在逃避中寻理解,于颓废间求醒悟,仍然有着太多的理性”。(李泽厚《华夏美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李白有太多的醉酒,亦有太多的忧愁,在“举杯浇愁愁更愁”的同时,亦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言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语。消极中有积极,悲观里有乐观,自怜间有自奋斗。中国文坛并不乏及时行乐诗和饮酒诗,但此前从未有过一首诗歌以如此蓬勃的活力和放旷的度量向读者述说饮酒的妙处。李白能直抒胸臆,高屋建瓴地指引我们去饮酒,在《将进酒》中诗人直呈饮酒两大主张:一是人应该饮酒以忘记世上和死亡的忧愁,二是与我同醉,不要吝惜金钱。“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狂放的激情充溢于金樽与钟鼓之间,高超的沉醉弥漫在饮酒和行乐之中。
李白同时也是一位失意的孤独者。“古来圣贤多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是这一理论的积极推行者,也是这一理论的忠实实践者。他的寂寞孤独是“高处不胜寒”的,是一种“传‘独坐’之神”(沈德潜《唐诗别裁》)的精妙,“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寥廓长空,凝滞孤山,怎一个“静”字受得,孤寂油然而生,却又只得去和幽人约会饮酒: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山中与幽人对酌》
诗歌乃兴会淋漓之作,酌者是隐居高雅之士,喝酒是恣情纵饮之醉,风度是超凡脱俗之兴。他只能与以酒为饮,以酒为友,塑造他“酒徒”和“狂客”的标准形象。如著名的《月下独酌四首》其一: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李白为我们导演了一幕生动的唐代荒诞剧。背景:花间;道具:一壶酒;角色:我;动作:独酌;剧名定名为月饮图。表面看来,诗人真能自得其乐,可是背面却有无限的凄凉。“对饮成三人”和独坐敬亭山感触一样,在多情狂放之间,仍是踽踽凉凉之行,仿若寂寞的鸵鸟,只一个人在奔跑。
二、酿造历史蕴味的怀古诗
怀古,很大层面上在咏史,实际上也是咏怀,是诗人借历史抒发自己现实感受的一种方式。李白在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时代,能感触到历史的跳动脉搏,生成一种深切的怅恨,或凭古讽今、或吊古伤今、或借古鉴今,不可说不是一位天才的诗人,能“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李白的怀古诗,称道历史人物,获取行为准则,触摸历史事件,体味生活辛酸,审视历史生活,感悟人世沧桑。
(一)称道历史人物,获取行为准则。在歌咏古代政治人物和游侠人物的诗歌中,有“功成身退”的鲁仲连,“高揖汉天子”的严子陵,“颇怀拯物情”的诸葛亮,“起来济苍生”的谢安,以及“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侯嬴和朱亥,等等,所有这些人物,在诗人的笔下都成为他自己的理想和性格的化身。这些历史人物风神与诗人酷似,如《古风》其十:
齐有傥倜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
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这个磊落高傲的鲁仲连形象,生动地传写了李白潇洒倜傥的神气。在怀古诗作中也写到了前期雄才大略、后期却迷信求仙的秦始皇,意在讽刺早年励精图治、晚年昏庸荒淫的唐玄宗。这些诗往往倾注了诗人鲜明的情感倾向,明示了诗人明确的价值判断。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却时时不如意,只处处勾起无限依念与想象,如《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
如果所谓“怀古”,只是对几百年前发生在此地的“谢尚闻袁宏咏史”情事的泛泛追忆,诗意便不免平庸而落套。诗人别有会心,从这桩历史陈迹中发现了一种令人向往追慕的美好关系-贵贱的悬隔,丝毫没有妨碍心灵的相通;对文学的爱好和对才能的尊重,可以打破身份地位的壁障。而这,正是诗人在当时现实中求之而不可的得。诗人的思绪,由眼前的牛渚秋夜景色联想到往古,又由往古回到现实,情不自禁地发出“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的感慨。尽管自己也象当年的袁宏那样,富于文学才华,而象谢尚那样的人物却不可复遇了。“不可闻”回应“空忆”,寓含着世无知音的深沉感喟。
(二)触摸历史事件,体味生活辛酸。这主要体现在李白的乐府诗创作中,李白的乐府诗大量地沿用乐府题,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皆能曲尽拟古之妙。一是借古题写现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如《丁督护歌》、《出自蓟被北门行》、《侠客行》等,均属于缘事而发之作,表达的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具有深刻的寓意和寄托。一是用古题写己怀,因旧题乐府蕴涵的主题和曲名本事,触发作者的感触和联想,借之来书抒写自己的情怀。这类诗更能体现李白狂放的人格风采和诗歌特色,“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叶燮《原诗·内篇》),言此意彼,“冥漠恍惚”,意余象外而曲尽隐微。《蜀道难》古辞寓有功业难成之意,正是此点触动了李白初如入长安追求功业未成时的悲愤,诗人再三吁嗟“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极力渲染蜀道高峰绝壁、万壑转石之艰难险阻,也是诗人于世道艰险的体认的写照。《将进酒》旧题含有以饮酒放歌为言之意,诗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壮气概,将及时行乐的狂欢抒写得激情澎湃。《行路难》古题寓意明确,“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感喟正道出了诗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理想展望。
[##]
(三)审视历史生活,感悟人世沧桑。从怀古玄远的时空回到咏史,是从形而上的哲思中回到人间现实,咏史诗联及人生、联及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位置的体认;因其与怀古诗的互渗、融合,也会有思古之幽情,有兴亡荣枯的感叹,显示出形而上的意味。但咏史诗起始于历史之具体人、事,其指向不在于对一生死存亡的玄思,而是对历史、现实经验的体认,有着浓厚的功利色彩。试看这样一种模式:怀古—伤今,咏史—讽时;其价值在于审视历史生活,感悟人世沧桑。如:
越王句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越中览古》
感慨昔时的繁盛与今日的凄凉,对比鲜明。
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
至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苏台览古》
柳色青青,年年如旧,又岁岁常新,以“新”与“旧”,以今古常新的自然景物来衬托变幻无常的人事。描绘人事欢乐难继、好梦不长的佳作应是《乌栖曲》: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
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
《唐宋诗醇》评论此诗“乐极生悲之意写得微婉”,可谓深谙其中三昧。在西施传说的简单艳情表面和复杂悲剧意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这也是此诗被贺知章誉为“可以泣鬼神”的魅力与流行所在。吴王对即将降临的灾难的漠不在意,表现在诗篇表面类似的漠不在意。正是我们这些读者将悲剧赋予诗篇。李白没有解决诗中的张力,他没有走向说教,甚至顶住诱惑,没有描绘他们的堕落后果。相反,他只通过暗示,消除了吴王作乐的简单表面,这些暗示只有读者能够理解。时间消逝,各种事物正在走向结束:水漏即将滴尽,太阳即将被山峰吞没,季节已是秋天,月亮即将沉入江中,而冉冉上升的朝阳将照耀他们的未来。观众知道所叙述情节的重要成分,其中的主人公却一无所知,这种手段基本上是戏剧的,他有力地唤起对于幻想和真实之间差异的注意,强烈地刺激有关历史与现实之间关联的思忖。
三、创造神话世界的游仙诗
李白自己说“五游神仙,游仙未曾歇”《感遇》其五),又说“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确,李白一生热衷游山玩水,寻仙访道,祖国大江南北名山大川几乎都曾有过他的足迹,也留下了他为数不少的游仙诗。品读这类迷离恍惚、神奇怪异的游仙诗,我们会对浪漫李白有一个更真切的了解,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神话的世界,在这个天地里,可以追求空灵飘渺、超凡脱俗的仙境,可以抒发怀才不遇、忧愤难堪的愤懑,可以释放解放自我、张扬个性的心声。
李白游仙诗的特点之一是仙化山水,营造缥缈,表达求仙访道的景仰。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推《游泰山六首》,这六首诗,几乎每一首都有神仙境界的描写。第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银台。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
玉女四五人,飘摇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
蓬瀛,是传说中的两座仙山,即蓬莱和瀛洲。金银台,是传说中神仙所居住的地方,用黄金白银铸成,金光闪闪,熠熠生辉。玉女,是仙女,长得如花似玉,妩媚迷人。九垓,即九重云霄至高处。流霞杯,仙人用的酒杯,流光溢彩,灿如云霞。艳姿丽容和芳香美酒一样令人心醉。看,这是多么美妙的境界!通过想象和联想,把神仙世界描绘得神奇美妙,光彩夺目,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实际上非常吻合诗人崇道信神,寻仙访道的心理。“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清平调词三首》其一)玉山、瑶台、霓裳、羽衣、月色、春风,此景惟有仙界有,人间那得几处见。蟾宫阆苑,闭月羞花;语语浓艳,字字流葩。
李白游仙诗的特点之二是美化仙境,暗斥现实,抒发怀才不遇的忧愤。《西上莲花山》(古风第十九)很能说明问题,诗歌是这样写的: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至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此诗写于安史叛军攻陷长安之后,首先描绘了一个神奇美妙的神仙世界。这是多么快意的神仙世界!高蹈尘外,洁净美好,令人神往。正当“我”跟着卫叔卿恍恍惚惚地飞向太空的时候,诗情陡然一转,“我”俯视人间,看到洛阳一带正被叛军肆虐蹂躏,生灵涂炭,血流遍野,而那些豺狼虎豹一般的安史叛军正趾高气扬,把持朝政。诗歌写到这里,就煞尾了,给读者留下了思索想象的空间。综合全诗来看,诗人意在将美好洁净的仙境和血腥污秽的人间进行对比,表现出诗人对叛乱者的无比憎恶,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对整个豺狼当道,人民遭殃的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显然,诗歌具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此外,还须注意的是,拜见仙人卫叔卿,这也是深有用意的。据《神仙传》载,卫叔卿曾乘云车,驾白鹿去见汉武帝,以为皇帝好道,见之必加优礼。但汉武帝只以臣下相待,于是大失所望,飘然离去。这里暗暗关合着李白自己的遭遇。天宝初年,诗人不也是怀着匡世济民的宏图进入帝阙的吗?而终未为玄宗所重用,三年后遭谗离京。可以想象李白的飘逸高举之中颇有几分志士不遇的悲愤。
李白游仙诗的特点之三是想象夸饰,神化仙境,表达自由洒脱的心声。《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一个辉煌灿烂的洞天福地出现在诗人面前,这个世界烟雾缭绕,幽深无底,日月辉映,金碧耀眼,群仙列队纷至沓来,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龙虎为之奏乐,鸾凤为之驾车,欢歌曼舞,兴高采烈。诗人置身其中,与群仙联欢,与神灵默会,忘却了世俗的名僵利锁、诡诈心机,褪尽了人间的污秽浊臭、私心杂念,尽情享受人间没有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才是诗人身心愉悦的最高境界啊。在人间活得很累很苦而且倍受压抑的李白终于在虚无缥缈的仙界找到了解放自我,张扬个性的空间。神游天上仙境,而心觉“世间行乐亦如此”,才敢于高呼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颜”的心声,敢于这样想、这样说的人并不多,李白说了,也做了。我佩服。我景仰。我快意。
四、营造清新自然的山水诗
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政治上的挫折碰壁,使他把赤子般天真情谊奉献给自由自在的山水,倾诉于无私无猜的自然。所以他寄情清风明月,漫游名山大川,留下许多山水名篇。“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诗歌中也有不少山水篇章,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李白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为我们营造了一种清新自然的山水世界。李白有不少短小精美的山水律绝,山水具体形象不一,手法技巧各异。例如《清溪行》写清溪感受:“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前二句看来只是以镜比水、以屏比山的修辞精巧,而诗人用意实为将水作明镜,山作屏风,以清水秀山为家。所以末二句说猿啼徒使游子伤感,而言外显示他这位谪仙则清心自在,怡然自适,因为山水就是他的家,合乎理想,恰同仙境。再如《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鸟儿飞尽,一朵白云悠然离去,始终相伴在一起的只有诗人和敬亭山,所以“相看两不厌”。这明白如话的大实话,作用与极端夸张同。而山拟人,人同山,有心与无生相知音,便是一种狂想,却也合乎他“浩然与溟?胪?啤保ā度粘鋈胄小罚┑墓勰睢V劣谒?拿??锻?烀派健贰傲桨肚嗌较喽猿觯?路?黄?毡呃础保弧对绶?椎鄢恰贰傲桨对成?洳蛔。?嶂垡压?蛑厣健钡龋?宦郾硐质址ㄊ悄馊嘶?蚍闯姆ǎ?际枪勰钌习汛笞匀挥胱晕一焱?惶澹?油蛭镂??啵?蛞黄鹦朔芄奈瑁?蛞晕?裟炎璧玻?剿?蜗蠖祭硐牖?⒖裣牖?⒏鲂曰?耍?晌??说闹?挠胗讶恕
参考书目:
①《唐诗咀华》 张明非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
②《盛唐诗》[美]宇文所安著 贾晋华译 三联书店 2004年
③《中国文学史》中册 章培恒 骆玉明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
④《唐诗宋词十五讲》葛晓音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⑤《中国文学史》第二编 袁行霈 罗宗强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
⑥《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年版
王波平,男,湖北荆州教育学院教务处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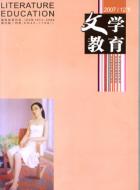
- 不知花落有多少 / 张梦琦
- 心事 / 董 炼
- 阿Q的假想敌们 / 崔守峰
- 随笔二则 / 孙婉怡
- 散文两篇 / 王?F?
- 音乐教育与德育渗透 / 林冬玲
- “有”和“具有”用法区别 / 陈世礼 占梅花
- 校园文化建设刍议 / 高利霞
- 文学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 李家金
- 《阿房宫赋》注释献疑 / 蒋福秀 杨向东
- 烛之武与触龙人物形象比较 / 魏君海
- 让语文与生活双赢 / 张娅娟
- 也谈语文学习兴趣的培养 / 郭国庆
- 如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 谢娟萍
- 运用情境教学让语文课活起来 / 马艳静
- 语文课导语之美 / 梁爱丽
- 课改新尝试 / 林 亮
- 语文教学中的审美 / 曹红波
- 中学文学鉴赏的三个目标 / 张 萍
- 语文教师要真正吃透新课标 / 郭克勤
- 重新审视语文教学中的五大关系 / 王进红
- 语文教学要重视课文中的文化 / 赵建新
- 语文教学应渗透生命意识 / 张红梅
- 关注人的生命是语文教学之本真 / 徐林根
- 《孔乙己》中关于脸色的细节描写 / 史鸿敏
- 《次北固山下》的景淡浓情 / 石聿寿
- 《漓江情韵》中的四美 / 黄文义 张 娟
- 《国殇》的悲壮崇高之美 / 王艳娟
- 李瓶儿为什么要嫁给西门庆 / 黄 文
- 解读《陈情表》中的四情 / 梅晓华
- 《兰亭集序》赏析 / 周 华
- 苏轼词作《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梦境与悲情 / 高 峰
- 《西湖组诗》中的季节意象 / 王芳实
- 《北方》的抒情艺术 / 黄良才
- 高考作文布局五法 / 祝海燕
- 个性化作文教学方法谈 / 赵连虎
- 让作文闪耀个性色彩 / 何满海
- 作文教学中的情感因素 / 介红波
- 英汉写作对比分析 / 常 虹
- 依托文本做好随文练笔 / 徐晓红 陈碧英
- 在多角度立意中提升作文质量 / 刘 敏
- 从高考作文评卷反观高中作文教学 / 杜丽萍
- 细节描写重在彰显真情 / 覃玉琴
- 语言风格与文体类型的互依关系 / 叶元齐
- 诗文诵读教学例谈 / 王海英 杨庆亮
- 阅读教学中如何做到长文短教 / 柯四银 胡秋英
- 从问题入手加强赏读教学 / 刘加洪
- 阅读教学过程中的自我感受 / 岳二平
- 如何有效提高学生自主阅读能力 / 谢鸣芳
- 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阅读教学 / 刘 洋 林春霞
- 文本阅读整体感知的误区与对策 / 陈晓燕
- 联系生活深化阅读感悟 / 胡梅贞
- 从《项链》看文学经典重读 / 何 峰 王 慧
- 文学解读的方法透视 / 白彩霞
-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教学简案 / 丁 翔
- 《长城万里行》教学设计 / 张爱娥
- 语文课堂优化四原则 / 姜跃明
- 古典诗歌教学如何体现情感教育 / 李文军
- 如何深化中学的文学教育 / 杨卫胜 李慧珍
- 高中语文探究式教学的实施途径 / 王承栋
- 语文教学应做到生活化 / 万俊林
- 以美的语言和手段进行语文教学 / 冯卫平
- 青春、爱情、革命的众声喧哗 / 高旭国
- 关于加强校本教研的实践与调查 / 熊仁山
- 评温儒敏先生的《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 / 艾士薇
- 古代诗词教学方法新探 / 范 华
- 中学新诗教学隐而不显原因新探 / 范 磊
- 古诗词中虚词的意义分析 / 刘小华
- 文学大师笔下的衣饰描写 / 钱光华
- 古诗词中的色彩美 / 郝光霞
- 童话世界中的信任与猜疑 / 张金凤
- 我国现代服饰流行美的文化根源 / 龚菲丽 张 坚
- 论《俄狄浦斯王》的悲剧精神 / 周 青
- 评孟樊的《旅游写真》 / 古远清
-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文与酒 / 李晔晖
- 刘禹锡诗歌艺术特色研析 / 李瑞星 海 刚
- 略论苏轼的人格观 / 龙 路
- 董立勃《骚动的下野地》的美学表现 / 谢祖德
- 试论鲁迅的读者观念 / 王玉琦
- 《好逑传》与《赫曼与窦绿苔》比较研究 / 王 博
- 浅谈现代作家的志向抉择 / 李 琰
- 论韩非言语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 邱 渊
- 太白诗风概述 / 王波平
- 路遥写两部大作的一些情况 / 高建群
- 我们怎样做祖宗 / 黄一龙
- 女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城墙 / 屈雅红
- 鲁迅是个矛盾的人 / 吴 俊
- 以古典文献学为视角看中学语文教学 / 戴丽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