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2期
ID: 92731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2期
ID: 92731
浅谈现代作家的志向抉择
◇ 李 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积聚着中国文人的血和泪,伤和痛,在那一场文化和思想的革命中,中国文人的思想乃至心理也同样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呈现出现代作家的志业抉择和最终转向的图景,并且这一事实还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现代文学发展的方向,笔者试图抓住那个时代作家对于志业的抉择,以此说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折不是空穴来风,是有其历史、作家和文学本身的因素的。
在现代文学的分期中,学界多把五四运动到之后的三十年定义为现代文学。纵观现代文学三十年,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时期的文学家或者批评家在来源与身份上大体可以分成三类:
1.由理科转向文学创作(其中理科在这里只是代指由与文学无关的学科转向文学创作,并不一定是现实意义上的理工科)。如,胡适、鲁迅、郁达夫、欧阳予倩、张资平、郭沫若、田汉、冰心、阿英、郑振铎,闻一多,等等。
2.由于战争的波及和家境的贫苦,很多人被迫辍学,但是他们往往也不忘自学的力量,并最终成长为优秀的文学家。如,冯雪峰、许钦文、王鲁彦、叶圣陶、萧军,等等。
3.自始至终都读文科,也同样在进行着文学创作。如茅盾、俞平伯,等等。
我们重点将眼光放到第一类,此类文人至少在志向与事业上都进行过一次抉择并最终投入文学的怀抱,这就给了我一个可供分析的话题,即他们为何要转向文学,有哪些原因导致他们最终选择文学创作?
一、五四运动中反思的中国文人——“文学救人”。
五四运动对文人思想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五四时期所提倡的科学民主,不仅代表了当时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而且也成就了文人志业抉择的第一功,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文人们开始作出了他们的第一次抉择,那就是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为国出力。比如他们大多选择的是医学、法律、船舶、军事,等等,这些专业都属于实用型的专业,学成之后,他们肯定能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所帮助,医学能悬壶济世,船舶和军事能增强我国的军事能力。如下图:
“当时的号召是富国强兵,总想学些实际的东西来达到这层目的,因此选了医学。”[2-p150]这是郭沫若对于自己选择医学的解释。如果他们的第一次选择为的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当五四运动把这种号召推向高潮的时候,他们中有的人却用清醒的头脑思考着中国的现状,他们清楚的意识到,中国需要的不是医治外在肉体的医生,而是可以唤醒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的领航者。“——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3-p135]“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p4]基于这样的意识,他们才作出了第二次选择,由理转文。
而五四运动的发生却是促使文人开始反思的导火索,“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首次觉察到有彻底改革中国文明的必要”[4-p35],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就是让他们知道所谓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这些归根到底都不能真正的让中国摆脱侵略的境地,只有文学才能唤醒中国国民,才能达到救人的目的。他们认识到虽然“中国急于需要一些物质文明来补救精神文明的不足”[2-p152],但是,“决定一个人的动向和成就的,主要还是教育和思想”[2-p153]。中国的教育需要的是文人,中国的思想更加需要的是文人,只有文人,才能将禁锢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众唤醒,而不是那些实用的机器。所以,文人们纷纷踏上了改变中国民智的道路,他们同时也肩负起教育和改革的重担,通过“文学救人”这样的途径来实现自我价值。
二、旧式教育下熏陶出的文学之情。
现代作家的成长历程中,不论学理,还是学文,很少有人从未受过文学的浸染,这是被他们所处的这个特殊时代牢牢抓住的事实,可以说,年少时期对于古典文学的痴情是当时每一个文人的梦想,尽管战争的硝烟落在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但它们也很难攻破文人们心中的那座城堡,所以文学便成为那时文人的一方净土。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文人,大多生在旧时代,在他们成长的青少年时期,他们所受的教育多是私塾和学堂,这样的中式教育也必然让他们有一种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和熟悉。换句话说,少时中式的教育奠定了他们的文学功底,这便成为文人志业抉择的第二个原因。
在冰心的传记中,作者这样写到:“书,是冰心童年的亲密朋友。”[6-p22]冰心的幼年时期,她就能连蒙带猜的将她喜欢的《水浒》等文学名著看几遍,这就无形中给她对于古典文学的热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连郭沫若自己也在他的《郭沫若论创作》一书中说到:“在我未发蒙前便教过我好些唐宋人的绝句,我也能琅琅上口,有的至今都还记得。”[2-p150]当然,有部分的文人在学习理科的时候才逐渐发现,他们的兴趣不在理科而在文科。于是对于古典文学的热爱渐渐占据上风,让他们放弃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初衷,并开始思考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学习理科。胡适先生改行的原因就是如此,“在这些试验之后,我开始反躬自省:我勉力学农,是否已铸成大错呢?我对这些课程基本上是没有兴趣——它与我自信有天份有兴趣的各方面,也背道而驰”。[8-p133]
然而,就在他们将转向提上日程之后,这种对于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却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对不能忽略的优势。可以说,他们在文学方面所具有的伟大成就恰恰与他们的转向有着密切的关系,用文学创作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与他们的逻辑思维和有别于文学以外的意识特征有关,这种不同于文学所重视的形象思维的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注定了他们那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从学习理科到转学文科,从逻辑思维到感性的形象,从实用到心灵的净化,他们经历了比任何人都丰富的心灵的洗礼。“我学过医,使我知道了近代科学方法的门径。这些,对于我从事文艺写作,学术研究,乃至政治活动,也不能说是毫无裨补。”[2-p152]就是这样的一种学习理科的经历,使很多文人都拥有了看待事物以不同于常人的心灵,使很多文人都拥有了用不同于普通文人的手法来抒写自己的故事。鲁迅解剖人性的犀利,就像一把握在他手上的手术刀,又快,又准,毫不留情,艾青诗歌中时时充溢着的色彩感也当然可以归功于他早年的绘画学习。然而跨专业的优势并不是他们成功唯一的条件,如果没有对于文学的热爱和熟悉,他们所谓的优势并不能成为他们进军文坛的利刃。
三、变革时期的文人心理——政治和社会意识。
1905年,中国废止传统的科举制度,这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前途模糊不清,它改变了我们中国传统的入仕观,造成了一种个人的挫折感,这样的挫折感就只好用有机会能领导群众来弥补。然而群众的领导者又是怎样的人,他一定是舞动人心的鼓动者,宣传思想的倡导者,揭示社会弊病的改革家,所以他们纷纷成立社团,变成了中国的改革家,变革民众的心理,成为了中国文化转折的功臣。更有甚者,他们中有的人摇身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挺身而出,带领着中国人民摆脱愚昧,建立新的国家。毛泽东就是在那个时代诞生的伟大实践家,但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他行文中的蓬勃大气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当时很多文学家都与政治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他们或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了社会变革,如,李大钊,他本人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事实上在那样一个只要有些微民族自尊心的人都会想要对当时的时势推波助澜,鲁迅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人,他的杂文的犀利,讽刺时政,揭露社会缺憾,这不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参与政治评判的表现!因为在某一个程度上,当时的政治就代表爱国心,代表文人改变社会的努力,代表“文学救人”的途径。正是在文人参与下,中国的国民也逐渐觉醒,并产生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组织,让她引领中国迈向成功之路。
[##]
文化是不能用某一种具体形态来代表的,然而白话文的出现却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文人创作的通俗化,这种通俗化的文本在冲破种种阻碍后终于在全中国畅行,这带给文人的好处远远不如带给普通老百姓的好处,因为就连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在家里放上几本小说,看上几份报纸。同时,文人创作的通俗化也使中国的文人一改以往的精英身份而变得普通,而今,社会这所大学也可以造就伟大的作家。在现代文学中,特别是中国社会动荡的那几年中出现了很多并未接受正式的学院教育而在文学中颇有成就的人,如:老舍、刘半农、萧红、萧军,等等。老舍的自叙文集中,他写到:“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9-p87]这里他所说的新的文学语言指的就是白话文的诞生,由于白话文的诞生,精英文学的下场与通俗文学的登台,才使像老舍这样的“以我这么一个中学毕业,既没有什么学识,又须挣钱养家”[9-p86]的人能够在文学殿堂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可以说,这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无关系,与他们的刻苦学习也不无关系,但是这与文化观念的下移更有关联。可以说没有当时的白话文,就没有现代文学,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所以白话文对当时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经过对以上文人转向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门第观念在文学界只能成为众矢之的,并最终导致文学的僵化甚至死亡,因为一个人的创作才能不是天生就注定的,他可以经过后天的练习和培养来达成自己的梦想。文学的门槛说高也高,说不高也不高,它的高在于它选择的往往是情感丰富,对文字极富有领悟力的人,它的不高在于它从不以学历来论资排辈。纵观当今文坛,青年的一辈人才济济,又有哪些是真正文科本家的出身呢?这不就再一次说明了“英雄不问出处”。然而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文人的转向对文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些文人的转向中,我们发现,他们给文学带来的不仅仅是他们卓绝的文学功底,还有就是文学视界的扩大,在他们的转向中,一些从未有过的文体诞生了,鲁迅的杂文,冰心的问题小说,等等,这些都是掺入了异质因素的文学文体。总而言之,文人的转向对文学的意义是巨大的,他们不仅壮大了文学家的队伍,而且还将异质因素带入了文学中,使文学在发展中不断更新,完善。
在新的世纪中,文学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文学家的界限也越来越暧昧不明,但不论怎样,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新生的异质因素带给文学的不仅仅是新奇,还有就是让文学从死寂中复活的新鲜血液,那么,就让我们静静的等待一个划时代的新的文学的诞生吧!
[参考文献]
[1]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2]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3]钱理群,王得后.鲁迅散文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4]周策纵等.五四与中国[M].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中华民国68年
[5]冰心.从‘五四’到‘四五’[J].文艺研究.1979年第一期
[6]肖凤.冰心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
[7]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8]李燕珍.胡适自叙[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9]胡?青.老舍写作生涯[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81
李琰,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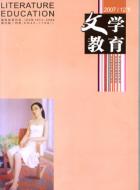
- 不知花落有多少 / 张梦琦
- 心事 / 董 炼
- 阿Q的假想敌们 / 崔守峰
- 随笔二则 / 孙婉怡
- 散文两篇 / 王?F?
- 音乐教育与德育渗透 / 林冬玲
- “有”和“具有”用法区别 / 陈世礼 占梅花
- 校园文化建设刍议 / 高利霞
- 文学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 李家金
- 《阿房宫赋》注释献疑 / 蒋福秀 杨向东
- 烛之武与触龙人物形象比较 / 魏君海
- 让语文与生活双赢 / 张娅娟
- 也谈语文学习兴趣的培养 / 郭国庆
- 如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 谢娟萍
- 运用情境教学让语文课活起来 / 马艳静
- 语文课导语之美 / 梁爱丽
- 课改新尝试 / 林 亮
- 语文教学中的审美 / 曹红波
- 中学文学鉴赏的三个目标 / 张 萍
- 语文教师要真正吃透新课标 / 郭克勤
- 重新审视语文教学中的五大关系 / 王进红
- 语文教学要重视课文中的文化 / 赵建新
- 语文教学应渗透生命意识 / 张红梅
- 关注人的生命是语文教学之本真 / 徐林根
- 《孔乙己》中关于脸色的细节描写 / 史鸿敏
- 《次北固山下》的景淡浓情 / 石聿寿
- 《漓江情韵》中的四美 / 黄文义 张 娟
- 《国殇》的悲壮崇高之美 / 王艳娟
- 李瓶儿为什么要嫁给西门庆 / 黄 文
- 解读《陈情表》中的四情 / 梅晓华
- 《兰亭集序》赏析 / 周 华
- 苏轼词作《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梦境与悲情 / 高 峰
- 《西湖组诗》中的季节意象 / 王芳实
- 《北方》的抒情艺术 / 黄良才
- 高考作文布局五法 / 祝海燕
- 个性化作文教学方法谈 / 赵连虎
- 让作文闪耀个性色彩 / 何满海
- 作文教学中的情感因素 / 介红波
- 英汉写作对比分析 / 常 虹
- 依托文本做好随文练笔 / 徐晓红 陈碧英
- 在多角度立意中提升作文质量 / 刘 敏
- 从高考作文评卷反观高中作文教学 / 杜丽萍
- 细节描写重在彰显真情 / 覃玉琴
- 语言风格与文体类型的互依关系 / 叶元齐
- 诗文诵读教学例谈 / 王海英 杨庆亮
- 阅读教学中如何做到长文短教 / 柯四银 胡秋英
- 从问题入手加强赏读教学 / 刘加洪
- 阅读教学过程中的自我感受 / 岳二平
- 如何有效提高学生自主阅读能力 / 谢鸣芳
- 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阅读教学 / 刘 洋 林春霞
- 文本阅读整体感知的误区与对策 / 陈晓燕
- 联系生活深化阅读感悟 / 胡梅贞
- 从《项链》看文学经典重读 / 何 峰 王 慧
- 文学解读的方法透视 / 白彩霞
-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教学简案 / 丁 翔
- 《长城万里行》教学设计 / 张爱娥
- 语文课堂优化四原则 / 姜跃明
- 古典诗歌教学如何体现情感教育 / 李文军
- 如何深化中学的文学教育 / 杨卫胜 李慧珍
- 高中语文探究式教学的实施途径 / 王承栋
- 语文教学应做到生活化 / 万俊林
- 以美的语言和手段进行语文教学 / 冯卫平
- 青春、爱情、革命的众声喧哗 / 高旭国
- 关于加强校本教研的实践与调查 / 熊仁山
- 评温儒敏先生的《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 / 艾士薇
- 古代诗词教学方法新探 / 范 华
- 中学新诗教学隐而不显原因新探 / 范 磊
- 古诗词中虚词的意义分析 / 刘小华
- 文学大师笔下的衣饰描写 / 钱光华
- 古诗词中的色彩美 / 郝光霞
- 童话世界中的信任与猜疑 / 张金凤
- 我国现代服饰流行美的文化根源 / 龚菲丽 张 坚
- 论《俄狄浦斯王》的悲剧精神 / 周 青
- 评孟樊的《旅游写真》 / 古远清
-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文与酒 / 李晔晖
- 刘禹锡诗歌艺术特色研析 / 李瑞星 海 刚
- 略论苏轼的人格观 / 龙 路
- 董立勃《骚动的下野地》的美学表现 / 谢祖德
- 试论鲁迅的读者观念 / 王玉琦
- 《好逑传》与《赫曼与窦绿苔》比较研究 / 王 博
- 浅谈现代作家的志向抉择 / 李 琰
- 论韩非言语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 邱 渊
- 太白诗风概述 / 王波平
- 路遥写两部大作的一些情况 / 高建群
- 我们怎样做祖宗 / 黄一龙
- 女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城墙 / 屈雅红
- 鲁迅是个矛盾的人 / 吴 俊
- 以古典文献学为视角看中学语文教学 / 戴丽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