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2期
ID: 92730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2期
ID: 92730
《好逑传》与《赫曼与窦绿苔》比较研究
◇ 王 博
中国与德国——东方与西方,历来是探讨中西文化碰撞时绕不开的热点。歌德作为德国文学的灵魂人物,他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受到中外学者的共同关注。从1831年10月始,歌德把兴趣集中到了遥远的中国。他先后在图书馆借阅了10多种有关中国的书籍,通过英法文译本读了一些中国小说和戏剧。他一直想把《好逑传》改编成一首长诗;读过《赵氏孤儿》后,受到启发,他又计划写一部戏剧。他写了14首名为《中德四季晨昏吟咏》的抒情诗,抒发了对东方古国的憧憬。通过接触中国的文学作品,歌德从中看到人类共同的东西。国内关于这一比较专题的论文及著作,都不约而同的援引了1827年1月31日那场著名的谈话。晚年的歌德对中国文学有了进一步了解后,认为“一部中国传奇”[1]与他所写的长篇叙事诗《赫曼与窦绿苔》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据考证这部传奇就是第一部知名于欧洲的中国长篇小说《好逑传》。大致成书于明末清初,位列“十才子书”第二的《好逑传》,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享有特殊的地位。然而这个十分有趣的研究课题却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本文试图以歌德的见解为切入点,将《好逑传》与《赫曼与窦绿苔》相比照,从思想内涵、人物形象、情节设置、叙事视角几方面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分析,由一个崭新的角度,探究儒家文化对歌德的影响。
一、共通的思想内涵
席勒在给马耶尔的信里,盛赞《赫曼与窦绿苔》“是一本充满智慧和德性底珍美的教训的书”[2]。而“在歌德的时代,在德国人已经认识的中国小说中,堪称‘道德小说’的也仅有《好逑传》一本而已!”[3]署名“名教中人”的作者意在敦伦明理,提高名教声誉,借故事给世人以劝诫。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儒释道互补,而以儒教思想为主。在十七、十八世纪被介绍到西方的,也只限于儒家的经籍。18世纪是欧洲的启蒙主义时代,启蒙主义思想家们对儒家伦理等道德理性十分推崇。伏尔泰、狄德罗等人更将中国视为理想国,他们对中国儒家的专制统治理论十分赞赏。哲学家莱布尼兹甚至希望让中国的皇帝去帮助治理西方国家。被尊为“魏玛的孔夫子”[4]的歌德所接触到的是富于浓厚的道德色彩,信奉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文化。他认为正是靠着道德和礼仪,“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5]这位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大思想家,对“把‘男女授受不亲’的孔孟礼教渲染发挥到了极致”[6]的《好逑传》产生共鸣,与他晚年政治思想趋于保守有关。
儒家以道德立教,意欲使人成为有德性的人,使社会成为和谐社会。有德性即自觉遵守仁义理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准则。《好逑传》中铁中玉除恶扶善、不畏强权,打入钦赐禁地养闲堂救出被囚良家女;在刑场慧眼识英雄,以命保命救侯孝;路见不平出手搭救被挟水冰心,都体现了一个义字。水冰心不顾闲言,将被恶人算计生命垂危的恩人铁中玉,接入家中医治。虽然患难之中生爱慕,但始终以理自守,孤男寡女同处一室,隔帘畅谈“五夜无欺”[7]。后来双方父母作主让他们结合,但两人以为如此一来便难证清白,有先奸后娶的嫌疑,也辜负了当初甘冒“男女授受不亲”之大忌,互相救援的仁义之举,故再三推辞。最后碍于父母之命,“名结丝罗以行权,而实虚以合卺以守正”[8]。突显了一个礼字。此外水冰心劝解铁中玉宽恕害他性命的地方县令。韦佩苦读成知县,宁丢乌纱帽,也要报答救了妻子的铁中玉,上书直言证其清白等,都是符合道德与礼仪的名教风范。最终所有有德性的人,都受到了皇帝的嘉奖。作品大团圆式的结局,号召百姓向剧中讲求伦理的人物看齐的说教,都体现了道德劝诫的主旨。
作为世界四大诗人之一,歌德也被英国诗人拜伦尊称为“欧洲诗坛的君王”。他汲取了叙事诗与牧歌的长处,创作了古典牧歌式的叙事诗《赫曼与窦绿苔》。古典文学强调艺术的伦理教化作用,认为艺术的最高价值就是培养教育人,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基于此长诗“不但把材料艺术地扩大为表现德国人底生活的生动的画面,而且使诗中底人物也变成了人类一般的典型的,有伦理价值的东西”[9]。“歌德在这里歌颂了德国小市民安分守己的保守思想。”[10]他借人物之口说出了自己的主张:健全的国民应该尊重家庭和社会的秩序,莫因乱世而动摇了勤勉地振兴家业的意志。也就是说要守着规矩,“合乎自然,和平的发展、进化”[11],达到一种和谐。这与孔子所言万物各得其所的和谐的社会观,有异曲同工之妙。歌德在诗中写道,赫曼的母亲责怪父亲试图按自己的意愿捏造孩子的做法,她说养育子女的最善之路是“自由地让他们去发展”[12]。牧师也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凡是合乎自然、合乎理性的东西便是善”[13],人们的禀赋使他们从事各种行业,闲静与勤勉的人都不可非难,因为这是本性使然。无疑这也是歌德本人的思想。
作为一本在席勒眼里有着智慧与德性的训诫书,该诗也宣扬了孔孟的关于“礼”、“义”、“仁”、“孝”的思想。窦绿苔在逃难途中搭救刚刚分娩的母亲和新生的婴儿,出于对众人的爱而义务去泉边打水;赫曼把母亲收拾的衣服和酒食送给需要帮助的灾民;药店老板和牧师倾囊相助等,都体现了仁义之心。赫曼对父母恪守孝道,默默忍受父亲对他的责骂,毫不留情的对待用言语中伤父亲的人。为了怕母亲担心,离家前都会事先告知一声。他对父母充满了敬仰之情,双亲在他眼中是最有智慧的人,他也是父母最孝顺的儿子。尽管赫曼与窦绿苔一见钟情,但是他们仍然克己守礼。窦绿苔答应了赫曼,去他家中当帮手,夜色中,两人匆匆的往回赶。因为天太黑,少女摔倒了,赫曼赶紧扶起她,两人“胸儿压着了胸,脸儿压着了脸”[14],此时的赫曼毫无邪念,反而为某种严肃的意趣所缚,屹立着像尊石像。“他并没有把她抱得更紧只是支持着那重量。”[15]姑娘也忍着痛,善意的谢绝了赫曼的帮助。如同铁中玉与水冰心,这对重礼的男女也获得了好姻缘。和《好逑传》结尾所揭示的一样,有德性的人最终会得到好报,赫曼与窦绿苔受到了父母的祝福,四人将手儿紧紧的握到了一起。难怪歌德会对爱克曼说,中国传奇“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16]。
二、理想的人物形象
歌德在即将步入知天命的年纪里,迎来了“文学创作的第三阶段”[17]。此时的他消磨掉了“狂飙突进”时的澎湃激情,与好友席勒一起,“开创了德国文学史上‘魏玛古典主义’的繁荣时期”[18]。古典主义文学将启蒙运动的理性和狂飙突进的情感相融合,“要求感情与理智、理想与现实、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自由与必然的和谐统一”。[19]这种和谐统一所孕育出的是新型的人,即理想的人。也就是古典人道主义理想所追求的完整、和谐、全面发展的人。《赫曼与窦绿苔》作为“歌德此时期政治思想、生活理想和艺术理想的总结”[20],其中的窦绿苔与《好逑传》中的水冰心一样,都是内在美与外在美、肉体与灵魂达到和谐平衡的理想女性。
同是美丽非常的女子,两人在外形上却差异很大,这反映了歌德与中国明清时代的古人所不同的美学观。明清传奇里的美女,都轻盈似燕、腰纤欲折。书中的水冰心也不例外,她“生得双眉春柳,一貌秋花,柔弱轻盈,闲处闺中,就像连罗绮也无力能胜”[21],过其祖和铁中玉都对她一见倾心。再看那容貌出众的窦绿苔,文中赫曼对姑娘的服饰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间提到了她高耸的胸脯,鹅蛋似的脸庞及浓密的长发。诗中多次夸赞窦绿苔的身材,与水冰心不同,她有着健壮的臂膀,匀称的体格,与魁梧的赫曼一般高。歌德借牧师之口,夸她是自然母亲的杰作,质朴可人。“歌德热爱自然,崇拜自然,他总是喜欢把美与自然联系起来。什么是美,他认为符合事物自由发展的天性就是美。”[22]这与庄周“牛马四足是谓天”的观点很相似。“他说:一个成熟的姑娘,发育有丰满的胸脯,宽大的骨盘,就显得美。因为这符合女人生育的目的性。”[23]如此说来,窦绿苔无疑是极美的女孩。
[##]
同为落难孤女,两人都敢于斗争,不畏强暴,以勇敢和智慧捍卫女性的人格与尊严,以高贵的品性战胜社会的偏见,而得到了幸福的结果。水冰心是兵部侍郎之女,因为有父亲的庇护,恶少过公子面对她的再三拒绝无可奈何,但人有旦夕祸福,水侍郎因误用一员大将被朝廷削职,遣戍边庭,过其祖重又联合地方长官和冰心的叔叔对她施加压迫。但有才有胆,赛过须眉男子的水小姐没有被恶浪打倒,而是不露声色的三戏恶少过其祖:施压力逼婚,偷梁换柱、暗改庚帖;排筵席诱婚,巧施诈术、虎口求生;城南庄抢亲,金蝉脱壳、转危为安。水冰心的一系列反抗集中体现了一个智字。最后过公子假传圣旨劫小姐,无路可退的水冰心只好暗藏尖刀,横下一条心,准备拼将一死。她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宁折不弯的斗争精神令人叹服。
窦绿苔也是一位有着独立人格的坚强女性。法军借驱逐普奥联军之机侵入了莱茵河以西的德境,自由的战士变得凶狠而暴虐。面对兽性的敌人,美丽的姑娘临事不畏,挥舞利刃,与对方拼杀,保护了自己和另一个女孩的清白。面对战乱中死去的父亲,她强忍悲痛、镇定自若,如男儿一般料理好后事,随后孤身一人随大部队踏上了避难河东的征程。同为反抗恶势力,在窦绿苔身上则体现了一个勇字。
同是互相爱慕,水冰心与铁中玉在长期的患难交往中始终不违名教而贞洁自持。窦绿苔虽然贫穷,但面对富裕的金狮馆主及其子,不改不卑不亢、自尊自爱的好品质。为了报答恩人,水冰心违背“男女授受不亲”之礼,将铁中玉接到自己家里养病,独居暗室五夜无欺,以身正不怕影子斜的磊落,抗击小人散布的流言蜚语。当他们不得已顺从父母之命成婚后,为了保持君子的名节,证明当时“毫无苟且”,仍然异室而居,甘愿夫妇为名,友朋为实。直到恶人再次搬弄是非,皇后派人亲自验明水冰心果系贞身后,两人才奉旨真正结为伉俪。最终水冰心凭借高贵的品性,既保全了名节,也获得了美满的姻缘。
花因春尽多零落,岁月何曾得久长。眼见着父母日衰,自己年龄渐长,年轻的赫曼不禁夜不能寐,天天心焦,“这庭园,这堂皇的土田——躺在这儿的山岗,一切都百无聊赖:因为我缺乏一位姑娘”。[24]恰在此时,他在赶去给迁徙中的难民发送衣食的路上遇到了心仪的窦绿苔。突如其来的爱情使他一夜成长,产生了结婚的念头。但父亲态度坚决的表明不希望儿子娶一个老百姓的村姑回来耽误前程,他已经相中了邻居一位富翁的女儿做未来的儿媳,因为那姑娘能带来丰厚的嫁妆。孝顺父母的赫曼难以抑制心中的痛苦,只得跑到梨树下号啕一番。较之赫曼,窦绿苔对待爱情的态度更加积极。尽管她对赫曼一见钟情,但面对其父轻慢的言语,受到伤害的少女当即克制而又坚决的维护自己的尊严,认为金狮馆主对贫困女太没同情。虽然她和赫曼贫富有别,但爱情没有贵贱,她大胆的表白了心中的爱,不愿把心思藏在心里只是等待。最后她决定保有自尊的离开,重新过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要忍受住在爱人身旁的相思之苦。窦绿苔依靠自己的自尊自强,和之前牧师和药店老板打探到的她的善良和贤惠的美德,摆脱了传统的门第观念,打消了赫曼父亲的疑虑,争取到了婚姻的自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三、相似的情节设置
被恩格斯评价为“市民的牧歌”的《赫曼与窦绿苔》是用荷马的诗体六步韵(Hexameter)写的,作为德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这首叙事诗严格遵守了古希腊戏剧的“三一律”原则,讲述了某一天午后到日暮为止的仅仅半天之内的一个地主家里的一件事情。然而四卷十八回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好逑传》中的场景却横跨北直隶大名府与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故事历时一年多,主线穿插副线,涉及人物众多,关系复杂。但是貌似悬殊的两个文本,其主体情节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即身处异地的两名青年男女因为某种机缘偶然相遇,并坠入爱河,最终突破了重重障碍,结合到了一起。
《好逑传》中铁中玉是北直隶大名府的御史公子,水冰心是济南历城县的侍郎小姐,两人相距千里。在京城时,铁中玉因为打入养生堂解救被大??钌忱?慷崛ビ慕?鹄吹那钚悴盼づ逦椿槠抟患业恼桃逯?俣???笳稹W怨呕龈O嘁溃??朔辣溉ü蟊ǜ矗???恿烁盖椎难档汲雒庞窝П苁欠恰N薅烙信迹?还??邮窒滦?肿〉乃?〗闱∏膳龅搅送揪?舜Φ奶?杏瘢?谑翘?逑烙肫媾?拥靡韵嗷帷L??恿私獾剿?〗闳?饭?渥娴闹腔郏?挚吹剿?缦勺影愕拿烂玻??智隳健K??奶?帕颂?杏裨诰┏堑南酪逯?拢?值玫剿?陌镏?牙牖⒖冢?虼硕运?峭蚍志囱觥V?笏??母?嵌蕴?杏裼芯让??鳎?饺嗽诨グ锘ブ?谐闪酥?骸5?钦舛杂星槿巳匆蛭??细缸拥淖枘雍陀形ダ窠讨?佣?荒艿W欧蚱薜男槊?W詈笤诨噬稀⑺?郊页ぜ拔づ宓陌镏?拢??侵沼诿缆?慕岷显诹艘黄稹
再看《赫曼与窦绿苔》,赫曼与窦绿苔,一个居住在莱茵河以东,一个生活在莱茵河以西,本来是命运不会有任何交集的两个毫不相干的青年,但是1792年的那场战争却改变了窦绿苔原先的生活轨道。为了避难,她不得不随众人一起流亡到了河东地区。同时姑娘善良的品性又成了两人相遇的契机,他们的结识都是为了帮助他人。赫曼是受母亲之命驾着马车,将准备的衣食送给需要帮助的人,而窦绿苔是为了搭救年轻的母亲和她刚出生的孩子,放下了不向人乞怜的尊严,主动寻求赫曼的帮助。窦绿苔的言行与开篇牧师与药店老板打探回来的“各人只顾得自己,顾不得别人的身上”[25]的混乱的逃难场景犹如云泥。两个心灵如外貌一样美的青年一见钟情,可是却受到了来自赫曼的父亲,一个有着很强的门第观念,嫌贫爱富的地主老爷的阻碍。最后在母亲、牧师及药店老板的游说下,两个年青人终于受到了父母的祝福,把手儿紧紧的握在了一起。
虽然情节内容大致相当,可是两位作家在编排素材的技巧运用上却是各有千秋。《赫曼与窦绿苔》运用了巧妙的对照法,如平静的小镇生活与难民的纷乱逃逸,梨树下赫曼对母亲的痛苦倾诉与生机勃勃的美丽田野,家庭生活的安宁与战争的残酷等。而《好逑传》则是环环相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常常是刚刚解决了一个矛盾,继而又引发了新的冲突。如铁中玉半路杀出救了水冰心,过公子与水运又转而合谋加害于他。水冰心几番施巧计虎口脱险,又碰到更厉害的成奇为过公子献狠招。铁中玉刀下救侯孝,侯将军沙场立功又使水侍郎官复原职,惹怒过学士再行加害等。
诚然《好逑传》与《赫曼与窦绿苔》在思想内涵、人物形象与情节设置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两部作品也存在许多明显的差异。比如叙事视角的不同,《好逑传》的视角与声音基本一致,叙述者作为视角承担者,讲述了整个故事。它的视角类型属非聚焦型,观察者也即说话人,犹如一位有着“上帝的眼睛”的先知,居高临下,“对故事的结局、人物的命运了如指掌”。[26]而《赫曼与窦绿苔》中,视角与声音并非完全一致,故事中的人物是视角的承担者,视角在金狮馆主、赫曼、牧师、母亲、药店老板等人间相互转换,声音则是叙述者的,他转述人物看到的东西,双方呈分离状态。与非聚焦型视角不同,它属于不定内聚焦型视角,叙述者以第三人称的口吻讲故事,采用几个人物的视角来呈现不同的事件,视角在某一特定范围内必须限定在单一人物的身上。按照福斯特的理论,《好逑传》与《赫曼与窦绿苔》中刻画的一系列角色都属于扁平人物,众所周知晚年的歌德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有意思的是铁中玉、水冰心、赫曼和窦绿苔恰好是儒家文化所宣扬的“义”、智”、“仁”、“勇”的象征,以孔孟之说为媒介,无怪乎歌德说中国人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参考文献]
[1][5][16][德]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第115、116、115页。
[2][9]周学普:《赫尔曼与陀罗特亚 译者序》,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7年版,第16、6页。
[3]谭渊:《〈好逑传〉早期西方译本初探》,《中国翻译》2006年5月 第26卷第3期。
[4]Ha Ewers:“Goethe——der konfuzius Von Weimar”,Das Neue China.Nr.4/79,s.28
[6]杨武能:《歌德与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91年版,第43页。
[7][8][21][清]名教中人:《好逑传》,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年版,第175、146、21页。
[10][18]王忠详 聂珍钊主编:《外国文学史》,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154、152页。
[11][17][20]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134页。
[12][13][14][15][24][25][德]歌德著,郭沫若译:《赫曼与窦绿苔》,重庆:文林出版社 中华民国31年版,第51、80、115、115、74、16页。
[19]张玉能主编:《西方文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13页。
[22][23]龙春力:《浅谈歌德的文艺美学思想》,《鞍山师专学报》 1990年第2期。
[26]胡亚敏:《叙事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25页。
王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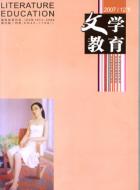
- 不知花落有多少 / 张梦琦
- 心事 / 董 炼
- 阿Q的假想敌们 / 崔守峰
- 随笔二则 / 孙婉怡
- 散文两篇 / 王?F?
- 音乐教育与德育渗透 / 林冬玲
- “有”和“具有”用法区别 / 陈世礼 占梅花
- 校园文化建设刍议 / 高利霞
- 文学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 李家金
- 《阿房宫赋》注释献疑 / 蒋福秀 杨向东
- 烛之武与触龙人物形象比较 / 魏君海
- 让语文与生活双赢 / 张娅娟
- 也谈语文学习兴趣的培养 / 郭国庆
- 如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 谢娟萍
- 运用情境教学让语文课活起来 / 马艳静
- 语文课导语之美 / 梁爱丽
- 课改新尝试 / 林 亮
- 语文教学中的审美 / 曹红波
- 中学文学鉴赏的三个目标 / 张 萍
- 语文教师要真正吃透新课标 / 郭克勤
- 重新审视语文教学中的五大关系 / 王进红
- 语文教学要重视课文中的文化 / 赵建新
- 语文教学应渗透生命意识 / 张红梅
- 关注人的生命是语文教学之本真 / 徐林根
- 《孔乙己》中关于脸色的细节描写 / 史鸿敏
- 《次北固山下》的景淡浓情 / 石聿寿
- 《漓江情韵》中的四美 / 黄文义 张 娟
- 《国殇》的悲壮崇高之美 / 王艳娟
- 李瓶儿为什么要嫁给西门庆 / 黄 文
- 解读《陈情表》中的四情 / 梅晓华
- 《兰亭集序》赏析 / 周 华
- 苏轼词作《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梦境与悲情 / 高 峰
- 《西湖组诗》中的季节意象 / 王芳实
- 《北方》的抒情艺术 / 黄良才
- 高考作文布局五法 / 祝海燕
- 个性化作文教学方法谈 / 赵连虎
- 让作文闪耀个性色彩 / 何满海
- 作文教学中的情感因素 / 介红波
- 英汉写作对比分析 / 常 虹
- 依托文本做好随文练笔 / 徐晓红 陈碧英
- 在多角度立意中提升作文质量 / 刘 敏
- 从高考作文评卷反观高中作文教学 / 杜丽萍
- 细节描写重在彰显真情 / 覃玉琴
- 语言风格与文体类型的互依关系 / 叶元齐
- 诗文诵读教学例谈 / 王海英 杨庆亮
- 阅读教学中如何做到长文短教 / 柯四银 胡秋英
- 从问题入手加强赏读教学 / 刘加洪
- 阅读教学过程中的自我感受 / 岳二平
- 如何有效提高学生自主阅读能力 / 谢鸣芳
- 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阅读教学 / 刘 洋 林春霞
- 文本阅读整体感知的误区与对策 / 陈晓燕
- 联系生活深化阅读感悟 / 胡梅贞
- 从《项链》看文学经典重读 / 何 峰 王 慧
- 文学解读的方法透视 / 白彩霞
-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教学简案 / 丁 翔
- 《长城万里行》教学设计 / 张爱娥
- 语文课堂优化四原则 / 姜跃明
- 古典诗歌教学如何体现情感教育 / 李文军
- 如何深化中学的文学教育 / 杨卫胜 李慧珍
- 高中语文探究式教学的实施途径 / 王承栋
- 语文教学应做到生活化 / 万俊林
- 以美的语言和手段进行语文教学 / 冯卫平
- 青春、爱情、革命的众声喧哗 / 高旭国
- 关于加强校本教研的实践与调查 / 熊仁山
- 评温儒敏先生的《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 / 艾士薇
- 古代诗词教学方法新探 / 范 华
- 中学新诗教学隐而不显原因新探 / 范 磊
- 古诗词中虚词的意义分析 / 刘小华
- 文学大师笔下的衣饰描写 / 钱光华
- 古诗词中的色彩美 / 郝光霞
- 童话世界中的信任与猜疑 / 张金凤
- 我国现代服饰流行美的文化根源 / 龚菲丽 张 坚
- 论《俄狄浦斯王》的悲剧精神 / 周 青
- 评孟樊的《旅游写真》 / 古远清
-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文与酒 / 李晔晖
- 刘禹锡诗歌艺术特色研析 / 李瑞星 海 刚
- 略论苏轼的人格观 / 龙 路
- 董立勃《骚动的下野地》的美学表现 / 谢祖德
- 试论鲁迅的读者观念 / 王玉琦
- 《好逑传》与《赫曼与窦绿苔》比较研究 / 王 博
- 浅谈现代作家的志向抉择 / 李 琰
- 论韩非言语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 邱 渊
- 太白诗风概述 / 王波平
- 路遥写两部大作的一些情况 / 高建群
- 我们怎样做祖宗 / 黄一龙
- 女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城墙 / 屈雅红
- 鲁迅是个矛盾的人 / 吴 俊
- 以古典文献学为视角看中学语文教学 / 戴丽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