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2期
ID: 92732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2期
ID: 92732
论韩非言语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 邱 渊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不能统一。随着秦王朝的逐渐强大,秦国历代帝王企图并吞八方,统一宇内。同时,秦帝国的统治者也认识到,要想达到地理版图和政治的统一,首先要统一思想。《韩非子》的出现正迎合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想法,因此,秦始皇一读韩非的书,就有恨不相见的感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纵观韩非的书,他完全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思考问题的。为了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刀锯斧钺都可以用上,而且刀锯斧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要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言论。《韩非子》中“言”字出现了457次,其中反映出来的言语思想主要就是对臣子和人民言语的钳制。其中与臣子的谏言有关的“言”就有80多次,(说明:《韩非子》中很多具体的“言”很难判定是不是“谏言”,因此,80多次也只能是个大概的数据,但已经能说明问题。)而其关于谏言的思想也完全是站在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的。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拙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ㄎ⑺翟迹?妒《?皇危?蚣?晕?鄱?槐纭<ぜ鼻捉??街?饲椋?蚣?晕?诙?蝗谩c却蠊悴??钤恫徊猓?蚣?晕?涠?抻谩<壹菩√福?跃呤?裕?蚣?晕??Q远??溃?遣汇D妫?蚣?晕?吧??纳稀Q远?端祝?钤耆思洌?蚣?晕??=菝舯绺??膘段牟桑?蚣?晕?贰J馐臀难В?灾市叛裕?蚣?晕?伞J背剖?椋?婪ㄍ?牛?蚣?晕?小4顺挤侵??阅蜒远?鼗家病#ā逗?亲印つ蜒浴罚
在这里,韩非完全站在君主的角度来谈“言”的,这里“难言”之“言”指的是臣子对君主的“言”,是“谏言”。对于“谏言”,“华而不实”不行;“伦”的含义是“体统”,“拙而不伦”是指朴拙没有体统,这样不行;“虚而无用”不行;“刿”是“刺伤”,“刿而不辩”指语言锋芒太露,伤人却不雄辩,这样不行;“谮而不让”指超越等级,不谦让,不行;“夸而无用”不行;“家计小谈”指“家常小事”,“陋”是和前面“闳大广博,妙远不测”相对立的,说的是狭隘浅薄,这样不行;“贪生而谀上”不行;“诞”不行;“史”指“繁于文采而不质朴”,即像庙里的祝官或衙门里的文书太讲文采,孔子说“文胜质则史”中的“史”也是此意,“史”不行;“鄙”是和“史”相对而言的,指粗俗,没有文采,不行;“诵”指称引典籍,食古不化,即“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这里的“诵”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诵”也不行。
虽然韩非生活的时代,秦国日益强盛,秦始皇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大一统的局面正日益形成,但韩非写《难言》的时候,他尚在韩国,并不是秦始皇的臣子或门客。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钱穆说:“其(韩非)使秦在韩王安五年。翌年见杀。”[1](P.551)
王先谦说:“(韩非)目击游说纵横之徒,颠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贼民,恣为暴乱,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国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权力,斩割禁断,搜朝野而谋治安。其身与国为体,又烛弊深切,无繇见之行事,为书以著明之。”[2](序)
这样看来,韩非的这种关于“言”的思想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话语权力下移,百家争鸣,对于文化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这导致当时各种思想流派争奇斗艳,韩非的思想也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统治者对话语权力的失控也导致了文学的繁荣。但是,话语权力下移,处士横议对统治者统一思想,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是不利的,至少在韩非看来是这样。
韩非希望君王能行使至高无上的君权来约束臣民的言论。他将自己定位为至高无上的君王脚下的一个臣子,因此,他的言论完全丧失了个人的人格独立,这就导致他所理解的“言”是如此之难。在韩非这里,春秋以来知识分子因天下共主,言论失控所得到的个人的独立人格丧失殆尽,个人只能是君王的奴隶,稍有不慎就有杀头的危险。韩非就是在他自己建构的社会模式下丢了性命。
在韩非看来,臣民当言,但必须是在维护君王的绝对权威和绝对利益的前提下来言。《韩非子·主道》说:“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在这里,臣民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言论。他认为人主必须仔细审察人臣的言论,《韩非子·南面》云:
人主有诱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於事者困於患。其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钢鳌V鞯勒撸?谷顺记把圆桓挫夺幔?嵫圆桓挫肚埃?滤溆泄Γ?胤?渥铮?街?蜗隆H顺嘉?魃枋露?制浞且玻?蛳瘸鏊瞪柩栽唬骸耙槭鞘抡撸?适抡咭病!比酥鞑厥茄圆桓??撼迹?撼嘉肥茄圆桓乙槭拢??普哂茫?蛑页疾惶???级廊危?缡钦呶街?侦堆裕?侦堆哉咧旗冻家印V鞯勒撸?谷顺急赜醒灾?穑?钟胁谎灾?稹Q晕薅四?⒈缥匏?檎撸?搜灾?鹨病R圆谎员茉稹⒊种匚徽撸?瞬谎灾?鹨病H酥魇谷顺佳哉弑刂?涠艘栽鹌涫担?谎哉弑匚势淙∩嵋晕??穑?蛉顺寄?彝?砸樱?植桓夷?灰樱?阅?蚪杂性鹨病
韩非提出“人主”不能壅于言,“其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指的是“人臣”进言时说的条件很少,退下去办事的花费却很多,即使有功他的进言也不真实。为了避免“人主”“壅于言”,对于“人臣”,“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钢鳌!倍?遥?顺家?盐铡把浴钡亩仁翟诓蝗菀祝?叭顺急赜醒灾?穑?钟胁谎灾?稹保?顺肌巴?浴币?巫铮?澳?弧币惨?巫铩W苤??诤?堑墓瓜肜铮?挥小叭酥鳌钡睦?娌攀俏ㄒ坏模?叭顺肌钡囊磺醒月郾匦胍浴叭酥鳌钡睦?嫖?诵摹W魑?叭顺肌保?挥腥魏蔚难月圩杂桑?坝锶?ν耆?ナЯ耍??挥盟灯胀ǖ睦习傩铡
更有甚者,控制话语仅仅是表层的手段,他要求“人主”应该从根本上控制人心。《韩非子·说疑》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奸”是什么呢?在韩非的思想体系里,“奸”就是指对“人主”不利的言行。
为了控制臣民的言论和思想,韩非为“人主”设计了一系列的策略,而且,这些策略构成了系统的“法、术、势”的思想体系,例如:他提出“七术”,在“七术”中提到“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等,对这三“术”,韩非的解释分别是:“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韩非子·内储说上》)
毫无疑问,韩非的思想必然导致极端的独裁。用现在的思想来看待这个问题,让人民放弃一切自身的利益,只为抽象的国家献身,必然导致极端的法西斯专制,但在当时,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如果放在客观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韩非的思想,其思想又有其存在的意义。在春秋战国时代,君主的利益和国家的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如果真能够将言论和思想高度地统一起来,必然会极大地提高一个国家的力量,在战争时期也必然会极大地提高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当然韩非思想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估量。
[##]
在韩非的时代,知识分子自身觉悟有所觉醒,下层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话语权,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更是将这种话语权发挥到极致。这时所谓的“言”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当时的百家著述,韩非要禁止的“言”也应该主要指这种百家著述。韩非的思想在秦始皇那里得到极端的实现,最终导致了焚书坑儒。《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焚书坑儒”标志着百家争鸣时代的结束,它以其极端的形式拉开了文化专制的序幕。从此之后,对言论的极端控制以及与此相伴的独裁就如病毒一样,种子绵绵不绝,而且变本加厉。
在此之前,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总是积极地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干预政治,企图以王者之师的身份出入王庭,成为贤明“人主”的座上宾。“焚书坑儒”以其极端的方式无情地毁灭了知识分子的一厢痴情,也一度给文化以及文学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先秦时期,知识分子拥有的是智慧和思想,这就是所谓的“道”;统治者拥有的是地位和权力,拥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就是所谓的“势”。知识分子企图用其智慧和思想参与社会,干预政治,决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统治者则力图利用其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为所欲为。韩非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在韩非这里,“执要”的“圣人”并不是普通的贤哲,而执掌国柄的“人主”。但知识分子并不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使命和政治追求,这就导致了“道势之争”,“焚书坑儒”为“道势之争”划上一个句号。王齐洲先生对这个问题有极为深刻的论述,他说:“‘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也是他们的价值目标。”“‘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也是他们的道德追求。”“‘道’‘势’之争以‘势’的增长和‘道’的萎缩作为结果或趋势,恐怕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和真正的儒家学者所不愿看到又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采取避世立场的道家学者也许还能在虚静的精神世界里保留那一份‘乐道忘势’的超然态度,而积极入世的儒家学者则很难继续‘乐道忘势’,即使他们大力提倡‘道’,而这种‘道’已经不完全是可以与‘势’相抗衡的精神力量,而是服从和维护‘势’的道德说教了。”[3](p.136-152)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在秦始皇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儒家学者关心社会的胸怀以及他们做“帝王之师”的痴情幻想使他们过多地关注现实的社会,他们要在政治理想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知识分子这种努力使当时作为广义的“文学”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即使下层人民的代表墨子也是努力地在可能的程度上和可能的范围内影响政治。“势”尊“道”卑使知识分子靠自己的智慧和人格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泡影,但知识分子的智慧仍需要表现,思想仍需要表达,感情仍需要宣泄。在“势”尊“道”卑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在统治者的淫威下求生存,文学在政治的重压下求发展,于是,文学在内容和特征上出现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统治者教化民众的工具,成了歌功颂德的一种手段。另一种趋势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将自己的才华用来创造具有新的特点的文学,和先秦的文学相比,这种文学和政治的距离有所拉大,文学的艺术性增强,知识分子开始在这种艺术性相对增强的文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精神寄托。当然,也出现了一些将歌功颂德、教化民众和艺术性结合得很好的文学作品。
总体说来,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有两条主要脉络:一条是文体的发展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始终;一条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和特点始终起着决定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清]王先慎撰,钟哲校点.韩非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3]王齐洲.呼唤民族性:中国文学特质多维透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邱渊,男,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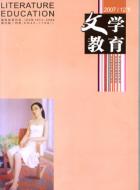
- 不知花落有多少 / 张梦琦
- 心事 / 董 炼
- 阿Q的假想敌们 / 崔守峰
- 随笔二则 / 孙婉怡
- 散文两篇 / 王?F?
- 音乐教育与德育渗透 / 林冬玲
- “有”和“具有”用法区别 / 陈世礼 占梅花
- 校园文化建设刍议 / 高利霞
- 文学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 李家金
- 《阿房宫赋》注释献疑 / 蒋福秀 杨向东
- 烛之武与触龙人物形象比较 / 魏君海
- 让语文与生活双赢 / 张娅娟
- 也谈语文学习兴趣的培养 / 郭国庆
- 如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 谢娟萍
- 运用情境教学让语文课活起来 / 马艳静
- 语文课导语之美 / 梁爱丽
- 课改新尝试 / 林 亮
- 语文教学中的审美 / 曹红波
- 中学文学鉴赏的三个目标 / 张 萍
- 语文教师要真正吃透新课标 / 郭克勤
- 重新审视语文教学中的五大关系 / 王进红
- 语文教学要重视课文中的文化 / 赵建新
- 语文教学应渗透生命意识 / 张红梅
- 关注人的生命是语文教学之本真 / 徐林根
- 《孔乙己》中关于脸色的细节描写 / 史鸿敏
- 《次北固山下》的景淡浓情 / 石聿寿
- 《漓江情韵》中的四美 / 黄文义 张 娟
- 《国殇》的悲壮崇高之美 / 王艳娟
- 李瓶儿为什么要嫁给西门庆 / 黄 文
- 解读《陈情表》中的四情 / 梅晓华
- 《兰亭集序》赏析 / 周 华
- 苏轼词作《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梦境与悲情 / 高 峰
- 《西湖组诗》中的季节意象 / 王芳实
- 《北方》的抒情艺术 / 黄良才
- 高考作文布局五法 / 祝海燕
- 个性化作文教学方法谈 / 赵连虎
- 让作文闪耀个性色彩 / 何满海
- 作文教学中的情感因素 / 介红波
- 英汉写作对比分析 / 常 虹
- 依托文本做好随文练笔 / 徐晓红 陈碧英
- 在多角度立意中提升作文质量 / 刘 敏
- 从高考作文评卷反观高中作文教学 / 杜丽萍
- 细节描写重在彰显真情 / 覃玉琴
- 语言风格与文体类型的互依关系 / 叶元齐
- 诗文诵读教学例谈 / 王海英 杨庆亮
- 阅读教学中如何做到长文短教 / 柯四银 胡秋英
- 从问题入手加强赏读教学 / 刘加洪
- 阅读教学过程中的自我感受 / 岳二平
- 如何有效提高学生自主阅读能力 / 谢鸣芳
- 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阅读教学 / 刘 洋 林春霞
- 文本阅读整体感知的误区与对策 / 陈晓燕
- 联系生活深化阅读感悟 / 胡梅贞
- 从《项链》看文学经典重读 / 何 峰 王 慧
- 文学解读的方法透视 / 白彩霞
-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教学简案 / 丁 翔
- 《长城万里行》教学设计 / 张爱娥
- 语文课堂优化四原则 / 姜跃明
- 古典诗歌教学如何体现情感教育 / 李文军
- 如何深化中学的文学教育 / 杨卫胜 李慧珍
- 高中语文探究式教学的实施途径 / 王承栋
- 语文教学应做到生活化 / 万俊林
- 以美的语言和手段进行语文教学 / 冯卫平
- 青春、爱情、革命的众声喧哗 / 高旭国
- 关于加强校本教研的实践与调查 / 熊仁山
- 评温儒敏先生的《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 / 艾士薇
- 古代诗词教学方法新探 / 范 华
- 中学新诗教学隐而不显原因新探 / 范 磊
- 古诗词中虚词的意义分析 / 刘小华
- 文学大师笔下的衣饰描写 / 钱光华
- 古诗词中的色彩美 / 郝光霞
- 童话世界中的信任与猜疑 / 张金凤
- 我国现代服饰流行美的文化根源 / 龚菲丽 张 坚
- 论《俄狄浦斯王》的悲剧精神 / 周 青
- 评孟樊的《旅游写真》 / 古远清
-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文与酒 / 李晔晖
- 刘禹锡诗歌艺术特色研析 / 李瑞星 海 刚
- 略论苏轼的人格观 / 龙 路
- 董立勃《骚动的下野地》的美学表现 / 谢祖德
- 试论鲁迅的读者观念 / 王玉琦
- 《好逑传》与《赫曼与窦绿苔》比较研究 / 王 博
- 浅谈现代作家的志向抉择 / 李 琰
- 论韩非言语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 邱 渊
- 太白诗风概述 / 王波平
- 路遥写两部大作的一些情况 / 高建群
- 我们怎样做祖宗 / 黄一龙
- 女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城墙 / 屈雅红
- 鲁迅是个矛盾的人 / 吴 俊
- 以古典文献学为视角看中学语文教学 / 戴丽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