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8期
ID: 356222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8期
ID: 356222
“理性”能拯救中学语文教学吗?
◇ 吴平安
说来惭愧,在我撰写《中学语文老师惹谁了?》(《中国教育报》2005.12.8),回应徐江先生对于中学语文的一系列批评时,竟尚未拜读徐先生发表在《人民教育》2005年9期的重要文章《中学语文“无效教学”批判》;而我在文章中现身说法,以自己的辛苦恣睢为同行请命时,也尚未读到网上援引的徐先生“我从不通过体察甘苦来探讨学术问题”的声明。前者是徐先生批评中学语文教学的理论基础,而后者,则必须承认,那的确是一种冷静而客观的学术态度。
揣摩徐江先生的意图,是要从哲学的高度审视语文教学,使我辈终日碌碌于形而下层面的中学老师,也能感受到些许形而上辉光的烛照,此举无疑是良好而富有建设性的。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在那个同样是众语喧哗的哲学王国里,哪一种智慧之光,足以给中国当代的语文教学洒下一片光明呢?恐怕其间选择的空间是十分广阔的。取舍不当,则不仅于事无补,南辕北辙也未可知呢?
一、与时俱进:质疑康德与阅读教学的理性拯救之路
徐江先生为中学语文“无效教学”之病开出的药方,一言以蔽之,是“理性”,这也是徐先生对中学语文教学一系列批判的基石和逻辑起点。徐文开宗明义:“语文教学质量搞不上去归根结底是语文界对自己的教学缺少理性认识,换句话说,人们还不能进行理性教学。”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提供理论支撑,徐先生抬出了一位尊神康德——一位主要学术活动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徐先生言之凿凿:“我这样的评价,是根据德国哲学家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所论‘理性’行为的标准而断的。”
为了说明问题,请允许我在这里援引王富仁、郑国民两位先生为《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丛书》撰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该丛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课题研究成果。这篇序言以《用文艺学视角观照中小学语文教学》,发表在《中国教育报》2006年6月15日的《读书周刊》上:“从1997年开始,中国语文教育遭遇了世纪末的尴尬。社会各界对语文教育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批评与讨论。在批评与讨论的过程中,论争的焦点问题是文学教育。”
这场针对中国语文教育的世纪末大讨论显然在语文界高层引起了震动。社会各界对语文教育“全面而深入的批评”,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得到了正面的积极的回应。在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就将文学教育与审美教育,确立为“课程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中,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均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我们当然不能无视和贬损在文学教育、审美教育中理性的参与及作用。问题是,像徐先生那样,言必称康德,言必称理性,试图在语文教学中构建其理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恐怕就大可商榷了。
需要指出的是,即令是在议论文的教学中,进行“理性教学”的所指,恐怕与徐先生的批判与垂范也有很大的距离。徐先生的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其中针对文言文教学的内容便占了两个部分,即《探讨论证的思维过程——〈六国论辩证思维解析〉》和《探究主体的深层心迹——为什么学〈游褒禅山记〉》。当徐先生愤怒声讨中学语文教学的两大弊病,“该教的教得不太好,不该教的又教得太多”时,由于完全脱离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其实他恰好是没有搞清什么是该教的什么是不该教的,犯了以主观臆测替代客观实际的毛病。《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就文言文教学制定的课程目标不仅是十分明确的,而且是十分具体的,我们认为这一课程目标是符合中学生与中学语文实际的:“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诵读古代诗词和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可参考附录以《关于诵读篇目和课外读物的建议》)
中学的文言文教学,很大程度上是当作“古代汉语”课上的。上述“课程目标”,也就最具权威性地决定了考试的内容,而考试的内容也便最具权威性地决定了教学的内容,这是任何一位一线教师都不敢掉以轻心的。文言文教学是很忌讳凌空蹈虚的,强调一篇课文在语言层面对“课程目标”的落在实处,课堂上多给学生留点诵读时间,最理想的是当堂成诵,这样的课就算上得不错了。因为背诵默写集中于文言文,为高考必考题,学生对文言文语感的培养全仰仗于课文的熟读和背诵(常有断句标点的试题)。如果一定要在文言文教学中贯穿“理性”的话,这就是须臾不可忘记的理性。这种处理当然会丢弃许多东西,为大学教师嗤笑,不过有所得必有所失,而目前中学语文教学的现状是,达到“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课程目标也绝非易事。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赘叙在“四面楚歌”的当代文化语境中中学语文特别是文言文教学所面对的挑战,不妨说,体现了国家意志的课程标准正是借助于高考这根指挥棒,强制性的使我们民族的血脉得以承传。
二、大道至简:质疑叙述学与写作教学的理性拯救之路
为了将中学语文教学的理性拯救之路拓宽延长,徐江先生发表了《我看语文教师应试能力的缺失》一文,将对语文教学与语文教师的激烈批评,由阅读领域转移到写作领域。徐先生教导我们要“学会在写作理论研究中把握认识方法”,再次居高临下的指责中学老师“在这方面中学语文教师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他们缺少基本的写作理论涵养。无论是研究记叙文抑或是学习叙述理论,他们还不能从哲学层面搞懂‘什么是叙述’以及‘为什么要有叙述行为’。”徐先生言之凿凿:“从本质上讲,写作本身就是认识事物。”“认清这些普遍的道理,人们才能自觉地写作。”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虽说对叙述理论的研究早已有之,但“叙述学”作为一个术语,是托多洛夫于1969年提出,而后成为一门显学的。托氏创立“叙述学”的初衷,正是为了对“叙述的本质和叙述分析的几条原则,提出几点一般性的结论。”(转引自《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朱立元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与徐先生对叙述理论的推重几无二致。可是不要忘了,在这“几条原则”和“几点一般性的结论”提出之前,人类的叙述行为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了,而且这“几条原则”和“几点一般性的结论”究竟能否涵盖无限丰富的叙事作品,都使人大可怀疑。如果说“认清这些普遍的道理,人们才能自觉地写作”,则无异于说“认清这些普遍的道理,人们才能开口说话”一样。这不是中国的美学传统,中国美学着眼的是最朴素也是最根本的原则。诚如《礼记·乐记》所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大道至简,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艺术发生学。黄瑞云先生盛赞“这是古代诗论的精华,他对诗的本质的说明,万古不磨,值得我们用黄金铸成大字镶嵌在艺术的殿堂上”(黄瑞云《毛诗序与儒家诗论》,引自中国语文网http://www.chinesec.net)生活之树常青,艺术之树常青,而理论往往是灰色的。而且一部世界的艺术史文学史中最闪光的篇页,往往就是由一批探索者革新者叛逆者对既定规范既定理论的不断冲撞不断突破而写就的。
或许要问:这里谈论的是艺术创作,与中学生作文是不是一回事?事不同而理同,我的经验和教训恰恰是,为人师者总喜欢在学生写作的起步阶段,有意无意中用一条条“规范”的绳索与一种种“理论”的框框,将学生的手脚捆绑得死死的,将学生的思想限制得死死的,于是在规则和理论在头脑中发芽生根之日,也就是灵动和鲜活之气在笔下泯灭之时。
我认为当下中学写作教学的要务,绝不是“学会在写作理论研究中把握认识方法”,也不是“从哲学层面搞懂‘什么是叙述’以及‘为什么要有叙述行为’”,没有必要将原本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倘若借用高考作文判分标准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基础等级”,就是能够正确熟练有效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也即是要文从字顺,行文得体。叙事状物,表情达意,都能清晰明了;“发展等级”,就要在表达上追求个性与创意,在驾驭语言上见出娴熟和功力了。与上述中国美学最朴素最根本的原则相对应,写记述抒情类的文章时,要强调“有感而作”,写真情实感,力避矫情滥情,无病呻吟;写议论说理类的文章时,要强调“有见而作”,写真知灼见,力避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可惜这些最浅近也是最基本的,针对中学生实际行之有效的“写作常规”却恰好是徐先生大力挞伐的。徐先生断言“这种形而上思维的摄入,对于教师和学生应试能力的产生影响是巨大的,绝非翻来覆去将什么‘常规’的‘叙事要有真情实感’、什么‘表达方式’、什么‘叙事六要素’等具体要求所能比及的。”大学老师的本事,就是将原本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作中学老师的,再复杂的问题也只能简单化处理了。
另外,当我们把写作话题转入“对既定规范既定理论的不断冲撞不断突破”时,不要以为这只是发生在某些先锋作家的前卫写作上。实际情况是,在当前文化语境中,在局部范围内,对既定语言规范的冲撞与突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今天中学生的作文周记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新词语、外来语、网络语已经屡见不鲜。而对成语的广告改写,对修辞格的新奇运用,对语言表达方式的另类改造,也时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丰富着我们的话语空间,乃至于大有将其逐渐演变成一种语言学上指称的“社会方言”,并成为其身份认证的趋势。在整体范围内,这种对语言规范的冲撞与突破也时有所见。最近班里学生有篇作文,我名之为“都市民谣”式写法,它采用一种不断重复的,单调机械的语言,配以“写啊写啊,练啊练啊,考啊考啊”的反复咏叹,将目前应试教育体制下中学生枯燥乏味的学习生活传达得淋漓尽致,讲评中批评者称之为“文字垃圾”,我则赞为大有某种“后现代”色彩。迄今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三、时移事易:也谈“回到康德那里去”
倘若把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放在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之下,承认在新课程标准中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得到极大提升,面对文学教育与审美教育已经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在教科书得以充分体现 的语文教育实际,再来讨论中学语文“无效教学”的问题并试图找出医治的良方,可能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如果一定要像徐先生那样言必称康德,像新康德主义者那样唤一声“回到康德那里去”的话,那么我倒认为更能给我们提供思想资源因而也更有现实针对性的著作,并不是《纯粹理性判》,而是《判断力批判》。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康德提出了其美学思想的一个核心命题——“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判断力批判(上)》,康德著,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48页)。在康德看来,审美对象与非审美对象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我们能否以一种无利害关系的观点去审视它,而“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对某一对象或其它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同上,第47页)。
朱光潜先生在《对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一文中(该文曾入选人教版统编教材),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甄别出主体对客体的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三种不同态度。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学教育、审美教育难于充分展开,正在于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往往是用木商看古松的实用态度,用植物学家看古松的科学态度来审视课文的,这两种态度,也就是康德所言的功利态度,而我们最缺少的就是画家看古松的美感态度。
提到实用态度,就不得不论及当前的考试制度,而这一点恰好是徐先生不予或不愿承认的。批评“大家把原因归咎于考试体制,心安理得地把自己应付的责任推卸掉了。”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倒不如说这是一线师生每日每时都要面对的实际问题。只要教育公平的敏感问题会继续牵扯亿万人的神经,只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仍然是社会普遍接受的理念,人才培养与选拔遭遇“格式化”的命运恐怕从根本上就难以避免。即以诗歌鉴赏为例,无论是中国古典文论的“诗无达诂”“见仁见智”,还是西方接受美学的“召唤结构”“空筐效应”,都隐含了在这一领域内,个性化阅读乃至于误读的合法性。可是当诗词鉴赏一旦作为考题出现在考卷上(此已为定型化的高考必考题),则对不起,体现公平公正性的“用一把尺子衡量”的判分标准,是不能容忍个性化阅读,更不能容忍误读的。师生从根本上讲就不可能摆脱实践性的功利诉求,从而进入康德所言的审美静观状态。
提到科学态度,就要涉及康德审美鉴赏理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美不用概念而又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了。为了划清艺术审美与科学认识的界限,强调前者不能为后者所替代,康德提出了“审美观念”以区别于“理性的观念”。然而,中学生尤其是理科班的学生,却常常是以看待自然科学的眼光观照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的,以概念判断推理的方式对待远较逻辑推演复杂得多的人类审美与情感问题。考试的命题和相应的教辅材料又常常在强化这一倾向。还是拿上述的诗词鉴赏题为例,“内容”早已固化为诸如怀古、思乡、惜别、归隐等等“类别”;意像也“提取”出诸如春花、秋月、杨柳、寒蝉等等模式,而命题范围毕竟有限,不可能考虑其间的细微差别,这就给理性的介入与概念的泛滥提供了空间,当语义的模糊与多义为具体与单一所替代,涵泳品味的鉴赏变为按图索骥的操作时,这已同中国诗的精神风马牛不相及了。像有人质疑杜牧《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反诘“莺啼何以千里得闻”那样的笑话,在今天理科班语文教学中时有发生,这不能不说都是“理性”与“科学态度”在作祟。
康德审美无利害关系的命题难以得到现实的回应,还在于当代文化语境的挑战。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氛围中,审美活动恰恰堕落为欲望的宣泄,而离精神的追求越来越远;它不再承诺以将人类从动物界中提升为己任,却恰恰强化人的动物性需求并为其合理性辩护。因此便完全阻断了席勒康德等人所设计的通过审美的中介,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审美的人并以此拯救人类道德的途径。
[作者通联:武汉洪山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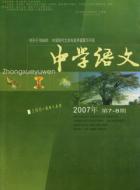
- 帮学生搭建沟通古今的桥梁 / 王登明
- 一堂好课的两重文化使命 / 张一山
- 寻芳撷翠躬亲 / 王建明
- 研究传 / 王明芬
- 语文“小组合作学习”教学误区与对策 / 黄汉宗
- 风刀霜剑难相逼,一怒沉江谁人叹 / 兰燕妮
- 《〈孔雀东南飞〉民歌特色》补 / 王白云
- 演绎“演绎” / 龙 玫
- “草根”新义简说 / 徐丽华
- “物称东西”的俗语源浅探 / 涂新林 柯 举
- 释《孔雀东南飞》中的“相” / 董秋成
- 古代之“游”类别谈 / 傅嘉明 莫娟娟
- “理性”能拯救中学语文教学吗? / 吴平安
- 从人性向度解读贝尔曼 / 郑可菜
- 面对社会、人生的思索 / 史绍典
- 2007年高考语文语言运用题五大亮点例说 / 李思衡
- 你提的是否是一篮子“春光” / 洪 峻
- 2007年高考现代文阅读湖北卷与广东卷之比较 / 冯 渊
- 蛋下得如何,还是让别人来评吧 / 洪方煜
- 满园春色关不住 / 王学华
- 审读图 / 薛海潮
- 奇文共欣 / 孟晓东
- 高考标点题解题方法例说 / 史淑杰
- 逆风飞飏,我手写我心 / 王 敏
- 新材料作文探究廖艺挺 / 廖艺挺
- 记叙技巧提升谈略 / 赖夏初
- 中美两国写作教学内容之比较 / 许 锃
- 美国学生如何写作文 / 史 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