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9期
ID: 143346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9期
ID: 143346
《背影》末段品读
◇ 徐德湖
《背影》末段中朱自清先生的晶莹泪水,蕴含着最丰富、最复杂、最深沉的情感,应该是教学的重点;由于该段文字叙述概括,将深情蕴含在朴素、甚至看似平淡的言语之中,因而也是教学的难点。不少教师平常教学过于简略,学生只能大致感受作者的思念之情,而缺乏应有的深刻感悟。本文试结合相关背景材料,通过对该段内容的分析,品味其中饱含的深沉情感。
文章写于1925年,这之前发生过许多事情。据《朱自清年谱》(姜建, 吴为公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10月版),“我”的祖父和父亲两代做官,家道富有,积蓄颇丰。1912年,军阀徐宝山以逮捕和杀头作要挟,勒索朱家钱财。祖父为保家人安全,被迫捐出大半家财,终因不堪勒索而辞世。父亲惊惧交加,累倒生病,被迫辞去宝应厘捐局长。经此变故,家道中落。当时“我”已15岁,也当有刻骨之恨。
至1917年,淮阴籍潘姓姨太太得知,父亲在徐州纳了几房妾,赶去闹事。父亲被撤职,花了很多钱,仍亏空500元,祖母又不堪承受而辞世。父亲又卖又典,才还了亏空;又借高利贷,才办了丧事。到此,家道彻底败落。这种阴影从此一直笼罩全家。除了“我”的幼稚,这也是上文“我”与父爱产生隔膜、形成错位的主要原因。
这两次家庭变故,是品味“我”的晶莹泪水的远背景。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这是品味“我”晶莹泪水的近背景,但比之于五年以前,更为复杂、更为凄惨暗淡。“东奔西走”,突出奔波之劳碌,这与家中光景“一日不如一日”形成反差,令人想象其中的艰辛。祖母丧事之后,父亲肩上一家老小的生活负担更重了。他虽为谋事东奔西走,但几乎一直没有成功,而是长期失业,家庭经济破产。后来,家里人连借钱也借不到了,而且是债主满门,讨本钱的、讨利钱的,吵成一片。“我”在杭州任职,每月七十块钱薪酬,寄一半家用,还是不够;又没定期,家里等着用,又是焦急。这从朱自清《笑的历史》(《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作者以妻子武钟谦为原型写作的小说)可见一斑。加之父亲娶有一妾,家庭开销增多,“我”和母亲很受压抑。“我”为了节约开支,乃往扬州任职。偏逢校长系父亲故旧,薪资全送给父亲,“我”又辞职往他处谋身。结果“触他之怒”, “我”与父亲失和,两年不相见。(转引孙绍振《〈背影〉的美学问题》,2010年第6期《语文建设》)归根结底,这些都由经济窘迫引起。
“我”还在北大读书时,“冬天晚上睡觉,只有一床破棉被,要用绳子把被子下面束起来”;为了补贴读书费用,妻子武钟谦连陪嫁的首饰也卖掉了。大学毕业后,在江浙一带漂泊5年,或因家庭矛盾,或因受误解的人际纠纷,或因被煽动的学潮、或因时局混乱,工资发放不足、不及时,辗转工作过六七所学校。其间生活总是十分窘迫。寄回家用的钱,也常常是借的。还曾因招待不起朋友,而深感不安。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后,也一直穷困。这些都可从上文《朱自清年谱》中得知。
“当家方知柴米贵,养儿才报父母恩。”这时“我”已生有4个子女,《儿女》一文中写到很多抚养子女的艰难情形。“我曾给叶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得还是自杀的好。”“近来差不多是中年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斥责,始终不能辩解,我的心里酸溜溜的。”“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材’的父亲”。“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来着。”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不禁凄然。(《朱自清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走过了一段艰辛的人生旅程,“我”才真正体会到了父亲抚养自己弟妹四个的不易,感受到父亲的困苦,感悟到父亲的慈爱。“我”曾不禁回忆起父亲带着我们弟妹,一起吃白煮豆腐情形,“‘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都喜欢吃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朱自清自述:传奇故事》,北京西苑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13页)其中充满了父爱温馨,充满了对慈父的怀念。
“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父亲年轻时,曾在江苏高邮、江西石港、江苏宝应等多处任职,“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而现今面对生活困境,却无可奈何,老境颓唐;“哪知”“如此”,融入了深深的沧桑感,饱含着对父亲的无限怜惜。作为长子,不能让他颐养天年,也没能像父亲一样仁慈地抚育好儿女,心中怎能不充满自责、愧疚、担忧和苦闷?
“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触目伤怀”、“情郁于中”,蕴含着对父亲的怜悯、疼爱。两个“自然”,突出了对父亲的充分理解。“我”意识到,父亲忘却的,是“我的不好”,这就蕴含了“我”的自省,自责,对父亲宽厚仁慈的感念,对家庭责任的担当。父亲在“家中光景一日不如一日”、不堪生活重负、心力憔悴、身体也每况愈下的背景下,还“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其中的千万个不放心,是现在的“我”可以想象,可以体会的。由此,“我”当会深刻感悟,父亲当年两经踌躇决定送我、嘱我路上小心、嘱托茶房照应等,这悉心所做的一切,都含着朴素真挚的父爱。虽然不幸的家庭有过不和睦,而父亲的慈爱总是一以贯之,永恒不变。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弥足珍惜。两个“惦记”饱含着“我”对父爱的深切领会,而不再是“暗笑他的迂”,也全然没有了“还不能料理自己么”的念头;有的却是“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的后悔。如果说《背影》写出了一个儿子的成长历程,这时的“我”才真正完全成熟。
“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作者曾说:“《背影》里引了父亲来信中一句。那封信曾使我流泪不止。”(《朱自清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06页)一封信使“我”流泪不止,写到文章里就引了这么一句,这就很值得品味。首先,稍一细看,父亲的语意前后矛盾,既然“身体平安”,又怎么会“大去之期不远”呢?这只能是很本能地先向儿子报平安,以免担心。这与前文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一样,质朴的言语中,渗透着真切的父爱;而且始终如一,永不褪色。这怎能不让“我”百感交集。其次,即便是“膀子疼痛厉害”,也不至于“大去”吧。事实上,父亲1945年才病逝于扬州,终年76岁。这说明父亲诚然身体不适,年迈多病,但更是因老境凄惨,精神颓唐,对生活、对生命几乎失去了信心和希望。这又怎能不让“我”无限担忧,而伤心流泪!
很自然地,“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因为五年后的这买橘的背影,已浸润了“我”对父爱深刻的生活感悟与情感体验。咀嚼这曾经背“我”而去的身影,它记录着父亲许多年的风雨历程,凝聚着父亲生活的种种不幸,镌刻着父亲的拳拳爱心,而成了父爱的象征符号;它使“我”懂得了父爱的至真精神,成了“我”铭心刻骨的记忆。
所以,这晶莹的泪水,饱含着“我”对父亲十分的感动、敬爱,对曾经不解父爱的懊悔,甚至忏悔,对年迈父亲的愧疚、牵挂、担忧,对家道衰败的悲哀,对生活不幸的无奈,乃至对时代的苦闷。
无限情思,汇成一句,“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这与文首“不相见”,不愿相见、有意不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知何时”,满含着痛苦的期盼之情。据朱自清弟弟朱国华回忆,父亲“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的文章《背影》,只见他的手不住地颤抖,昏黄的眼珠,好像猛然放射出光彩。”父子之间终于深切感受到了彼此的牵挂与关怀。由此,我们深刻感受到,两代人曾经的“爱的隔膜”消解了,爱的错位平衡了;名族人伦中的父慈子孝达到了默契,达到了圆满。这种民族文化的精髓,将永远放射着人性的光辉,闪耀在读者的心灵。
徐德湖,语文教师,现居江苏兴化。本文编校:舒 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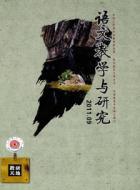
- 《背影》末段品读 / 徐德湖
- 《边城》教学反思 / 李玲
-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语言指瑕 / 姜涛
- 关于阅读教学的微博 / 王尚文
- 阅读教学需要教师对文本硬读的功夫 / 凌宗伟
- 《雨霖铃》与《声声慢》铺叙手法之比较 / 卢红
- 当前阅读教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 郑圣祖
- 《老王》教学片段及思考 / 韩筱燕
- 《鸿门宴》人物比较 / 吴立荣
- 中学生作文语言八股泛滥的原因及对策 / 张金保
- 《斑羚飞渡》文本解读及教学设计 / 张家岭
- 关于中学生作文出新的三点认识 / 董旭午
- 高考议论文写作中的材料选用 / 田泽生
- 江苏高考语言表达应用题命题特点分析 / 周万喜
- 初中语文美育探微 / 郑远祥
- 语文课堂教学细节处理的魅力 / 王碧峰
- 我的教材我做主 / 柏华之
- 优化设疑 有效提问 / 林春辉
- 春播桃李三千圃 秋盼硕果满神州 / 游贤合 刘少鸾
- 跨越中美时空的移民文学 / 严歌苓 江少川
- 细节的真谛 / 魏润身
- 红杏枝头春意闹 / 寇章云 李培明
- 也谈语文教学中的语言品味 / 陈亚娥
- 由一篇记叙文的修改而得到的三点启示 / 刘梅英
- 没有多媒体的语文常态课堂教学 / 陈蕾
- 慢慢走在文本细读的路上 / 王翠花
- 伊玛堪中的神奇婚姻母题及其文化意蕴 / 韩成艳
- 如何处理《论语》教学中文与言的矛盾 / 郑萍
- 夜吟桂华月一轮 / 史焕章
- 语文优质课存在的弊病 / 邓玉霞
- 片面限时是一种阉割语文美学的做法 / 卜廷才
- 流行歌曲与时代心理 / 黄志刚
- 中外传记作品教学初探 / 唐媛媛
- 追寻与探访 / 雷冬梅
- 隐喻 / 徐述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