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9期
ID: 143374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9期
ID: 143374
如何处理《论语》教学中文与言的矛盾
◇ 郑萍
于丹将《论语心得》搬上百家讲坛,继而高中教学和高考考纲中也添加了《〈论语〉选读》,我们对于《论语》这一部用古代汉语记载下来的以语录式样呈现的中华文化的经典仿佛越来越熟悉,一些大家的解读也有意带着我们往简单易懂的方向前行。可是,真正作为教学内容而言,我们处在论语教学的十字路口:向左走,是纯粹的知识丛林;向右走,是哲学的思品课堂。
从语言来说,它是古代汉语;从形式上说,它是古代特有的对话文体;从内容上说,它是传统文化的源头。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无论学什么学科,都该预先清楚为什么要学习它。所以,我们在教学中还是应从“文”和“言”两方面入手去把握。论语教学能不能体现出其应有的内涵,就是看如何处理好“言”与“文”这对矛盾。下面就围绕这一对矛盾,结合我的教学经验,谈谈我对论语教学浅陋的思考。
一.“言”和“文”的矛盾因何而来
何谓“言”?何谓“文”呢?各人的看法不同,但大体而言,“文”应为“文章、文学、文化”,“言”应是“词语积累、古汉语语法、诵读方法、文言语感”。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发现这两者的矛盾在论语教学中尤为明显,论语教学甚至比普通的文言文教学更难。这是为何呢?
1.高考考纲的影响:
根据考纲要求以及近几年的高考考题设置,很多老师认为,就《〈论语〉选读》而言,语录的格局、对话的语体仅仅是古代文章格式的萌芽,所以教学建议着重是在语言文字和文化内涵这两个教学层次上。《论语》的课,听得也比较多,很多老师受高考考纲的影响,在教学设计时重视文化内涵的挖掘和文言字词、文言语法现象的教学。然而这两方面固然重要,而且在考卷上能体现出其有效性,但是,在“文”和“言”的处理上却有很大的欠缺,文言语法分析得再清晰,文化内涵挖掘得再透彻,脱离了文学气息和语言艺术,那就不是语文,起码,它缺乏了语文味。
比如有位老师在上《诲人不倦》这一课时是这样设计的:①串讲词句,进行文言知识梳理。②师生互动,组织重点问题探讨。③自主学习,课文其他问题研读。例:对孔子的“述而不作”,你怎么看?④拓展提升,深入理解文化内涵。例:“有教无类”的认识。在这堂课中,他运用了很多教学手段,也补充了很多的课外知识和名家的论语赏析,但是我感觉他将“文”和“言”分离开来处理的方式不妥。特别是在分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一句时,除了提问“天何言哉”是什么特殊句式以外,就什么也没再分析。把这个绝佳的比喻轻轻的放过,也把圣人的寓教学于玩笑之中,以独特的方式引入正题,实行循循善诱的启发式教学方式给忽略不计。像这样的将论语教学中的“文”和“言”分离,其实是割裂了论语的整体性。
吕淑湘说:语文教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的确,语文教学是审美的活动。论语教学中教师应把一件件具体生动的事,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一句句深入浅出的话,通过孔子那优美而简约的语言,将它们再现在学生眼前,这样才能激起学生的共鸣和探究欲望。文言知识和语言艺术在论语教学中同样重要,文学气息和文化内涵也需共存。从根本性或者人文性的角度看,“文”的知识似乎比“言”的知识更具有魅力,“言”无疑是“文”的基础和载体,“文”才是根本。
2.论语教材的特点:
《论语》以其短小的篇幅,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笔墨,便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它在艺术形式上具有“简约美”,在思想内容上具有“真实美”,在章节之间又具有“对称美”。而我们教材中选择的篇目又是重新组合而成的,它不似传统的文言文,有整篇文章可以阅读、分析和体会,除了《沂水春风》外,其它的篇目都是由章节组合而成的。我们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对于这样的语录体不太能理解,而且章节之间的逻辑也不是特别严密,要很连贯的分析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们必须从孔子那简约而优美的语言中去细细体会他的感情,比如他对颜回、对子贡,甚至对子路的感情。
《〈论语〉选读》教材的特殊性,使得传统的“字字落实,句句清楚”的串讲模式在论语教学中也无法起到作用。对于语句的初步理解,学生完全可以对照文下的翻译进行自学,而由于这些翻译的存在,很多教师就认为对于文言字词、文言知识的分析是教学重点。殊不知,有了这些翻译,学生对大部分文言实词、虚词和特殊句式都能理解,他们需要的是透过这些语言,看到孔子等人物形象和其中包含的情感。因此,语言艺术和文学气息才是论语教学中的重难点。
二.“文”和“言”的矛盾如何解决
1.从文言知识中体会语言艺术。
言简意赅,惜墨如金,一字传神,是人们对《论语》语言个性的极好形容。清桐城派古文家已有“简为文章尽境”的精妙论述。一“简”字可以概括《论语》中遣词造句的语言特色。《论语》是语录体,它的语言虽是散珠碎玉,基本风格朴素简洁,却也文彩富赡,既精练含蓄,又韵味深长,处处流金溢彩,时时掷地有声,其表现的内在的深度和视界的广阔无与伦比。而这样优美的语言艺术我们完全可以在论语教学中通过对字词和特殊句式的分析,让学生在诵读的过程中体会到。
比如我在教《君子之风》时,对于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对于这一句的分析,首先让学生明确的是“贤哉,回也!”这是一个主谓倒置句,但是并不到此为止,还需从文言知识中品读语言艺术。于是我问学生:“为什么要把‘贤哉’放在前面呢?这和直接说‘回也’‘贤哉’有什么不同?前后反复出现,有什么作用呢?”这样的提问就能使得学生明确:主谓倒置是为了突出强调颜回的贤德;反复出现,加强语气,表现出对颜回的高度赞赏。
再比如上面提到的《诲人不倦》,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对于这一句的分析,我在课堂中先让学生诵读,首先明确“小子何述”和“天何言哉”两句是宾语前置,然后请学生将这两句的情景进行简单的表演,经过演绎,学生感觉到圣人有时候还真会开玩笑。教书先生突发奇想,居然说自己不想讲话了。不想讲话怎么教书呢?子贡自然而然地提出了疑问。如果我们来回答,那就只好改开聋哑学校了吧。可圣人却不这样回答。圣人话锋一转,抬头望天。请问,天讲了什么呢?不是照样运行四季、化育万物吗?原来,圣人并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真的不想讲话,而是以独特的方式引入正题,实行循循善诱的启发式教学啊。通过这样的文言知识理解,带动了他们体会语言艺术的积极性,也能感受到孔子那“言有穷而意无尽”的语言魅力。
当然,《论语》中的语言艺术不仅限于此,但由于课堂时间的限制,为了保证教学的有效性,我们只能从文言知识的分析中去体悟孔子的语言艺术魅力。
2.从人物对话中分析人物形象。
《〈论语〉选读》以语录体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教学中,那我们就应该从人物的对话中分析人物的形象,挖掘文化内涵,以期在“文”和“言”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论语》所使用的“师徒对话”的表达方式,内在地规定了它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的语言风格;朝夕相处的耳鬓厮磨,师生间达成的默契,使他们的谈话只须点到为止,形成其语言的简洁精练,含蓄隽永;坐而论道的潇洒雍容,使其于简单淡泊中透出生动的气韵。
比如在《雍也》中,孔子指天发誓:“天厌之?天厌之!”夫子回后他的得意门生子路脸色非常难看,夫子情急之下急忙发誓:我如果做了坏事,老天会惩罚我!老天会惩罚我!用重叠修辞格表白其确实没有在放荡的卫灵公夫人南子面前出过差错。其实这段在教学中学生非常感兴趣,因为这让他们感觉到孔子他老人家也有可爱的激动的一面。于是围绕这句,我和学生展开了讨论:“这里塑造了孔子怎样的形象?”学生纷纷举手:“可爱的!”“怕自己的学生误会的!”等等。最后,以一位学生的发言作结:“夫子很可爱,子路你也太小看老夫了,以为为师是为了在卫国谋取政治地位或是亲近美色去接近南子,其实于美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岂可灭绝心性?见色而不起淫心,如周敦颐之爱莲——“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是为中庸。”
论语教学肩负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语文课堂是对一代代民族继承者进行思想教育的主战场。《〈论语〉选读》在艺术上还给教师和学生解析文本含义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它语约义丰,简洁凝练,哲理深邃,启迪无穷,质朴自然,生动形象,它留给我们的“艺术空白”需要师生积极参与,发挥想象力,予以填补,从而与作者一起共同完成作品。所以说,我们在“文”和“言”之间行走的同时,也就是进行艺术创造的时刻。
郑萍,语文教师,现居浙江长兴。本文编校:王 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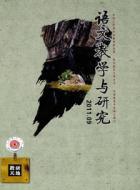
- 《背影》末段品读 / 徐德湖
- 《边城》教学反思 / 李玲
-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语言指瑕 / 姜涛
- 关于阅读教学的微博 / 王尚文
- 阅读教学需要教师对文本硬读的功夫 / 凌宗伟
- 《雨霖铃》与《声声慢》铺叙手法之比较 / 卢红
- 当前阅读教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 郑圣祖
- 《老王》教学片段及思考 / 韩筱燕
- 《鸿门宴》人物比较 / 吴立荣
- 中学生作文语言八股泛滥的原因及对策 / 张金保
- 《斑羚飞渡》文本解读及教学设计 / 张家岭
- 关于中学生作文出新的三点认识 / 董旭午
- 高考议论文写作中的材料选用 / 田泽生
- 江苏高考语言表达应用题命题特点分析 / 周万喜
- 初中语文美育探微 / 郑远祥
- 语文课堂教学细节处理的魅力 / 王碧峰
- 我的教材我做主 / 柏华之
- 优化设疑 有效提问 / 林春辉
- 春播桃李三千圃 秋盼硕果满神州 / 游贤合 刘少鸾
- 跨越中美时空的移民文学 / 严歌苓 江少川
- 细节的真谛 / 魏润身
- 红杏枝头春意闹 / 寇章云 李培明
- 也谈语文教学中的语言品味 / 陈亚娥
- 由一篇记叙文的修改而得到的三点启示 / 刘梅英
- 没有多媒体的语文常态课堂教学 / 陈蕾
- 慢慢走在文本细读的路上 / 王翠花
- 伊玛堪中的神奇婚姻母题及其文化意蕴 / 韩成艳
- 如何处理《论语》教学中文与言的矛盾 / 郑萍
- 夜吟桂华月一轮 / 史焕章
- 语文优质课存在的弊病 / 邓玉霞
- 片面限时是一种阉割语文美学的做法 / 卜廷才
- 流行歌曲与时代心理 / 黄志刚
- 中外传记作品教学初探 / 唐媛媛
- 追寻与探访 / 雷冬梅
- 隐喻 / 徐述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