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8年第2期
ID: 356388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8年第2期
ID: 356388
闽派·闽派语文·中学语文
◇ 史绍典
今天,我主要就两个问题谈一些想法:第一,我与闽派语文;第二,我与中学语文。
谈到闽派语文,我认为,闽派就是因了它的韧性和执著,才成就为闽派的;认准一个方向不倦地做下去,这是闽派最大的特色。今年暑假,我们到了新疆,我和之川先生一起去了新疆的惠远。那是林则徐的流放地。在惠远,我跟之川先生谈到这样一个话题:以林则徐这样一个省部级的高官,从东南富庶之地的闽侯(福州)流放到这偏远的边陲小城,茫茫沙漠,人烟稀少,语言不通,但林则徐为惠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做了很多好事。所以,惠远人民立碑纪念他,辟出纪念堂来纪念他。我觉得这就是闽派的根基。还有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过《天演论》、同样是福建人(侯官)的严复,他说,“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而这正是陈日亮先生“守正创新”思想的源头。不保留传统的东西,不把传统中优秀的东西继承下来,那就不会有创新。所以,“旧”和“新”、“守正”和“创造”就是这样的一个辩证关系。在闽派前辈的根基之上,闽派语文在发展着。
我们认识闽派语文,是跟一个个闽派语文的代表人物相关联的。如,孙绍振先生,在一些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上,他敏锐的思想,以及对语文的深邃的看法,令人深思。今天上午钱理群教授提到孙绍振先生用还原法来解读文学作品,给我们当前的语文教学尤其是阅读教学立下了一个标杆。我记得很清楚,孙绍振先生讲《雷雨》,讲到《雷雨》中的人物,他说,作品中最欣赏的人,就是繁漪,这跟作者曹禺先生感受颇为一致。《雷雨》中,繁漪是相当复杂的角色,繁漪的确干了很多破坏周萍和四凤关系的坏事,可以说她是恶的;但繁漪又是一个有个性、有情感的女人,她把自己的个性、感情看得比一切,包括面子、地位、人伦等都重要,从美学意义上说,她又是美的。孙绍振先生这些话,在引导语文教学走进文学作品,跟作品对话,跟作者对话,跟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方面,有了新的启迪。又比如,赖瑞云先生,他的《混沌语文》,提得很高妙,有非平常的见解。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在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走着那种跟政治、跟意识形态很靠近的文本解读的路子。而这,在赖先生那里被打破了。还有王立根先生,他的《作文智慧》,凝聚着王先生作文教学的机智。闽派的代表人物,常能以一句很简单的话,概括出他们对语文的独特感受,这是不简单的。今年暑期,我们到吉林通化,那里有一个“全国中语泰斗长白行”的活动,我与陈日亮先生都去了。陈先生送我一本书,拿起一看——《我即语文》。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讲,那是一种张力。同样,给我的冲击也是大的。书名本身就有一种张力,“我即语文”!“语文”,谁能讲清楚?每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语文,但陈先生用四个字、一句话,把语文是什么讲透了。——《我即语文》,极具张力,非同寻常,内含陈先生“守正创新,修身育人”的语文理念,体现了闽派文化韧性、执著的风格。这一句类似于禅语的“我即语文”,把语文教学的理念参得透彻,给人以极大冲击和震撼。
跟陈先生谋交,应该是在很多年前,在一次全国语文研讨会上,陈先生的讲话引起了我的注意。陈先生讲,当今的语文是什么样境况呢?他讲了一个例子,读鲁迅先生的《祝福》。“祥林嫂”站在“我”面前,课文怎么说?“祥林嫂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老师的提问出来了:“这句话的表达有什么特点?”我记得陈日亮先生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是“出离愤怒”了。他说,我们读鲁迅的作品,我们解读“祥林嫂”,难道仅仅用一个“定语后置”能办得到的吗?鲁迅先生笔下的末路的祥林嫂,她的际遇,是“定语后置”所能概括的吗?当时,他的这番话给与会者的冲击是很大的。这以后,在各种会议上,跟陈先生交往逐渐多了。
我对闽派语文的认识,就是从这样一些闽派语文的领军人物开始的。
近年来,全国中语会及一些相关学术组织组织的大规模的学术交流活动,闽派语文的一些后起之秀,往往在参会时找到我,说:“史老师,我是陈先生那儿来的,是日亮先生的学生。”听到这句话,觉得亲切。每每说是日亮先生弟子的老师,在一些全国级别的大赛上都有不俗的表现,多能得到很高的奖次,这是不得了的。难怪立根兄要说“今日东南风大作”。我看还不只是“今日”的问题,那是要长久的“东南风大作”的了。所以,我这样一个作为湖北省——号称中部崛起省份的语文的代表,今天是向闽派讨教来了。(拱手致礼,掌声)
第二,我与中学语文。
我今天带了我的几本书,这几本书是送给尊敬的陈先生的。我也想说说我对语文的追求,我的语文心。今天上午,钱理群教授谈了许多,我深有同感。我曾说过,俄罗斯的屠格涅夫称赞唐·吉诃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坚决相信,超越了他自身的存在,还有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须一片至诚地努力争取,方才能够获得。而唐·吉诃德的随从桑丘是现实的,现实的桑丘则是唐·吉诃德的另一面镜子,他们彼此交映出无限的深度。唐·吉诃德与桑丘折射出的自我,令人遐思神往。我曾“戏说”我的工作是“行走江湖”,江湖有其精彩与险恶,我却总是乐此不疲,以唐·吉诃德式的“疯狂”,实践着我的语文理想。当然,理想与现实之间有落差,但真正追寻自己的理想,应执著地朝着既定目标前进。钱理群先生最近写过评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的文章,谈到中国最伟大的两个知识分子,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鲁迅。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做孜孜不倦的追求。孔子与鲁迅不同的是,他总是寻求当政者给他一个平台,而鲁迅则总是始终不断地求索,从不谋求与当政者的合作。我想,钱先生自己应该也是这样的。他们都在为心中的理想不懈地追求。
我说说我的语文理想,我下面的一些话,散见于我谈中学语文的一些文章中。我说,语文,是情韵悠长、广博优雅、诗意盎然的……我说,语文,是很本色、很清醇、很生活、很自然、很人性的……我说,语文,是生活的、生命的、生态的……我说,语文,是诗意的、激情的、顾盼的、联想的;它有高山流水样的奔涌、一马平川式的倾诉,午夜黎明式的静寂、狂飙突进式的啸傲……我说,语文,是励志、交锋,感悟、体验,畅谈、浅吟;是抑扬顿挫、回肠荡气、余音绕梁……我说,语文是独立思想的家园,是民族精神的居所……我说,语文,永远是语文……
“语文永远是语文”,是2000年,北京《中学语文教学》杂志约我写文章时我用的一个标题。编辑对我说:“史老师,站在20世纪,展望21世纪,那时的语文会是什么样子?”我真正就站在20世纪,往21世纪看了一眼,看过后我说,即令是21世纪,语文还是语文,它不会变成别的什么!这是我们语文教师追寻的,我们立志去做的自己的事业。
这里,我还要谈谈民族精神与语文教育问题,这也是涉及守正与创新的话题。记得前年在上海,有一个民族精神与语文教育论坛。我做了一个即席发言。当时,正是12月25号,圣诞节。我说,在西方的圣诞节谈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这正好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融沟通的问题。百年来,中西方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总是处于劣势,总是处于一个下方的地位。记得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讲述中西方文化交流时说,就好比瀑布,西方文化总在瀑布的上端,我们总在下端,这也是一种交流,但这种交流是一种上对下的冲击。百年以来,一时西方文化谈多了,对传统文化冲击太大,于是便有一批人出来大讲传统文化以缓冲和平衡;等传统文化讲多了,包袱实在太重,肯定又会有一批人出来呼吁输入西方文化。如此循环往复,这一百多年就是这么折腾过来的。我认为,日亮先生恰好是走在一条很切合我们中国国情的道路上。当语文只注重知识,只注重知性教学时,陈先生说,不能那样。而当空虚的“人文”要掏空语文的时候,陈先生又呼吁,语文,必须有他自我的存在。我体会,“我即语文”,就好比说“佛祖在我心中”一样,就是语文在我心中,我就是语文,我这个个体与语文之间“合一”。这是难能可贵的。
今天,我主要就两个问题谈一些想法:第一,我与闽派语文;第二,我与中学语文。
谈到闽派语文,我认为,闽派就是因了它的韧性和执著,才成就为闽派的;认准一个方向不倦地做下去,这是闽派最大的特色。今年暑假,我们到了新疆,我和之川先生一起去了新疆的惠远。那是林则徐的流放地。在惠远,我跟之川先生谈到这样一个话题:以林则徐这样一个省部级的高官,从东南富庶之地的闽侯(福州)流放到这偏远的边陲小城,茫茫沙漠,人烟稀少,语言不通,但林则徐为惠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做了很多好事。所以,惠远人民立碑纪念他,辟出纪念堂来纪念他。我觉得这就是闽派的根基。还有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过《天演论》、同样是福建人(侯官)的严复,他说,“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而这正是陈日亮先生“守正创新”思想的源头。不保留传统的东西,不把传统中优秀的东西继承下来,那就不会有创新。所以,“旧”和“新”、“守正”和“创造”就是这样的一个辩证关系。在闽派前辈的根基之上,闽派语文在发展着。
我们认识闽派语文,是跟一个个闽派语文的代表人物相关联的。如,孙绍振先生,在一些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上,他敏锐的思想,以及对语文的深邃的看法,令人深思。今天上午钱理群教授提到孙绍振先生用还原法来解读文学作品,给我们当前的语文教学尤其是阅读教学立下了一个标杆。我记得很清楚,孙绍振先生讲《雷雨》,讲到《雷雨》中的人物,他说,作品中最欣赏的人,就是繁漪,这跟作者曹禺先生感受颇为一致。《雷雨》中,繁漪是相当复杂的角色,繁漪的确干了很多破坏周萍和四凤关系的坏事,可以说她是恶的;但繁漪又是一个有个性、有情感的女人,她把自己的个性、感情看得比一切,包括面子、地位、人伦等都重要,从美学意义上说,她又是美的。孙绍振先生这些话,在引导语文教学走进文学作品,跟作品对话,跟作者对话,跟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方面,有了新的启迪。又比如,赖瑞云先生,他的《混沌语文》,提得很高妙,有非平常的见解。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在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走着那种跟政治、跟意识形态很靠近的文本解读的路子。而这,在赖先生那里被打破了。还有王立根先生,他的《作文智慧》,凝聚着王先生作文教学的机智。闽派的代表人物,常能以一句很简单的话,概括出他们对语文的独特感受,这是不简单的。今年暑期,我们到吉林通化,那里有一个“全国中语泰斗长白行”的活动,我与陈日亮先生都去了。陈先生送我一本书,拿起一看——《我即语文》。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讲,那是一种张力。同样,给我的冲击也是大的。书名本身就有一种张力,“我即语文”!“语文”,谁能讲清楚?每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语文,但陈先生用四个字、一句话,把语文是什么讲透了。——《我即语文》,极具张力,非同寻常,内含陈先生“守正创新,修身育人”的语文理念,体现了闽派文化韧性、执著的风格。这一句类似于禅语的“我即语文”,把语文教学的理念参得透彻,给人以极大冲击和震撼。
跟陈先生谋交,应该是在很多年前,在一次全国语文研讨会上,陈先生的讲话引起了我的注意。陈先生讲,当今的语文是什么样境况呢?他讲了一个例子,读鲁迅先生的《祝福》。“祥林嫂”站在“我”面前,课文怎么说?“祥林嫂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老师的提问出来了:“这句话的表达有什么特点?”我记得陈日亮先生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是“出离愤怒”了。他说,我们读鲁迅的作品,我们解读“祥林嫂”,难道仅仅用一个“定语后置”能办得到的吗?鲁迅先生笔下的末路的祥林嫂,她的际遇,是“定语后置”所能概括的吗?当时,他的这番话给与会者的冲击是很大的。这以后,在各种会议上,跟陈先生交往逐渐多了。
我对闽派语文的认识,就是从这样一些闽派语文的领军人物开始的。
近年来,全国中语会及一些相关学术组织组织的大规模的学术交流活动,闽派语文的一些后起之秀,往往在参会时找到我,说:“史老师,我是陈先生那儿来的,是日亮先生的学生。”听到这句话,觉得亲切。每每说是日亮先生弟子的老师,在一些全国级别的大赛上都有不俗的表现,多能得到很高的奖次,这是不得了的。难怪立根兄要说“今日东南风大作”。我看还不只是“今日”的问题,那是要长久的“东南风大作”的了。所以,我这样一个作为湖北省——号称中部崛起省份的语文的代表,今天是向闽派讨教来了。(拱手致礼,掌声)
第二,我与中学语文。
我今天带了我的几本书,这几本书是送给尊敬的陈先生的。我也想说说我对语文的追求,我的语文心。今天上午,钱理群教授谈了许多,我深有同感。我曾说过,俄罗斯的屠格涅夫称赞唐·吉诃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坚决相信,超越了他自身的存在,还有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须一片至诚地努力争取,方才能够获得。而唐·吉诃德的随从桑丘是现实的,现实的桑丘则是唐·吉诃德的另一面镜子,他们彼此交映出无限的深度。唐·吉诃德与桑丘折射出的自我,令人遐思神往。我曾“戏说”我的工作是“行走江湖”,江湖有其精彩与险恶,我却总是乐此不疲,以唐·吉诃德式的“疯狂”,实践着我的语文理想。当然,理想与现实之间有落差,但真正追寻自己的理想,应执著地朝着既定目标前进。钱理群先生最近写过评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的文章,谈到中国最伟大的两个知识分子,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鲁迅。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做孜孜不倦的追求。孔子与鲁迅不同的是,他总是寻求当政者给他一个平台,而鲁迅则总是始终不断地求索,从不谋求与当政者的合作。我想,钱先生自己应该也是这样的。他们都在为心中的理想不懈地追求。
我说说我的语文理想,我下面的一些话,散见于我谈中学语文的一些文章中。我说,语文,是情韵悠长、广博优雅、诗意盎然的……我说,语文,是很本色、很清醇、很生活、很自然、很人性的……我说,语文,是生活的、生命的、生态的……我说,语文,是诗意的、激情的、顾盼的、联想的;它有高山流水样的奔涌、一马平川式的倾诉,午夜黎明式的静寂、狂飙突进式的啸傲……我说,语文,是励志、交锋,感悟、体验,畅谈、浅吟;是抑扬顿挫、回肠荡气、余音绕梁……我说,语文是独立思想的家园,是民族精神的居所……我说,语文,永远是语文……
“语文永远是语文”,是2000年,北京《中学语文教学》杂志约我写文章时我用的一个标题。编辑对我说:“史老师,站在20世纪,展望21世纪,那时的语文会是什么样子?”我真正就站在20世纪,往21世纪看了一眼,看过后我说,即令是21世纪,语文还是语文,它不会变成别的什么!这是我们语文教师追寻的,我们立志去做的自己的事业。
这里,我还要谈谈民族精神与语文教育问题,这也是涉及守正与创新的话题。记得前年在上海,有一个民族精神与语文教育论坛。我做了一个即席发言。当时,正是12月25号,圣诞节。我说,在西方的圣诞节谈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这正好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融沟通的问题。百年来,中西方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总是处于劣势,总是处于一个下方的地位。记得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讲述中西方文化交流时说,就好比瀑布,西方文化总在瀑布的上端,我们总在下端,这也是一种交流,但这种交流是一种上对下的冲击。百年以来,一时西方文化谈多了,对传统文化冲击太大,于是便有一批人出来大讲传统文化以缓冲和平衡;等传统文化讲多了,包袱实在太重,肯定又会有一批人出来呼吁输入西方文化。如此循环往复,这一百多年就是这么折腾过来的。我认为,日亮先生恰好是走在一条很切合我们中国国情的道路上。当语文只注重知识,只注重知性教学时,陈先生说,不能那样。而当空虚的“人文”要掏空语文的时候,陈先生又呼吁,语文,必须有他自我的存在。我体会,“我即语文”,就好比说“佛祖在我心中”一样,就是语文在我心中,我就是语文,我这个个体与语文之间“合一”。这是难能可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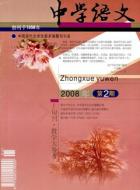
- 正确认识和处理语文教学中的多种关系 / 倪文锦
- 闽派·闽派语文·中学语文 / 史绍典
- 流转语文的灵性 / 刘 丹
- 语文素养的三大系统 / 赵文汉
- “课外拓展”的系统机制与教学建议 / 张悦群
- 课堂教学:现实对理想的挑战 / 陈元辉
- 作文教学必须立足素质教育 / 吴华月
- 警惕:说明文教学的去语文化 / 李明哲
- 中学生文学作品课内阅读动因的现状分析 / 杨仕威
- 教学创意呼唤“灵魂在场” / 郑可菜
- 阅读是自我的生命体验 / 陈连林
- 勾践:一位知耻而后勇的君王 / 何永生
- 《触龙说赵太后》课堂实录 / 佚名
- “靠得近点,再靠近点!” / 欧东栗
- 例谈如何将课本与文化相联接 / 黄俊玉
- 语文阅读教学的质疑艺术 / 王新伟
- 建立以文本细读为中心的阅读新理念 / 张禾青
- 语文味与综合性 / 吴宁亚
- 阅读议论文的基本步骤 / 鲁厚忠
- 重:“chóng”耶,“zhòng”耶? / 寇安炳
- 提示语、警示语之辨析 / 续云奎
- 以语文为圆心,以智慧为半径 / 林 丽
- 迷彩型重复语病透视 / 乔建军
- 试探湖北省高考语文作文命题走向 / 王启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