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6年第12期
ID: 355974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6年第12期
ID: 355974
为何不言“通感”?
◇ 王崇明
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是中学语文教材里的精美散文,其文词之典雅、用语之丰采、造句之奇特,令人心旷神怡。特别是文章中两处运用通感手法写出的美妙句子造成的奇妙感受,更让人回味无穷。对这种手法的理解和分析,就成为我们增长知识、提高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可惜的是,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审查通过的人教版必修本却有意淡化“通感”的提法。在课后练习第二题中将运用通感手法的句子说成是比喻句,又说“用诉诸听觉的音乐来比香味,来比光与影的组合,明与暗的变化”,根本未提及通感,不知编者何意。
但是,在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中却这样解释:“注意,本题将通感也作比喻的一种,其实,通感是一种特殊的比喻,和一般的比喻有着本质的不同。老师可结合课文说明,适当给学生做些讲解,帮助他们理解这种修辞想象。”既然通感与比喻“有着本质的不同”,为什么还要将通感等同于比喻呢?
通感是指人的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不同的感觉互相沟通,而把甲感觉的词语用于表示乙感觉。若追溯“通感”概念的由来,应首推钱钟书先生的《通感》一文。该文首刊于《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70年代末收入《旧文四篇》(后又收入《七缀集》等)。其文借西哲亚里士多德《心灵论》中“感觉移借”之说,博陈中西诗句、今文古典,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通感”概念的流行,全赖钱先生之力。
然而,钱钟书先生在《通感》一文的首句指出:“中国诗文有一种描写手法,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似乎都没有理解或认识。”周振甫先生也说:“像钱先生在《通感》里说的,古代修辞学家都没有认识,所以《发凡》(指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笔者注)里也没有。”其实不然,1921年,陈望道先生为《民国日报》读者介绍文学新概念时,曾撰有《官能底交错》一文,文中指出:
官能底交错——就是感觉底交杂错综。这是近代人神经极敏所生的一种现象。例如德国诗人兑梅尔(Dehmel)《沼上》诗中有“暗的声音”一语,明暗是视觉上的现象,声音在听觉上自无所谓明也无所谓暗的;说是“暗的声音”那是视听两官感觉底混杂。就所谓官能底交错了。余类推。
陈望道先生所说的“官能底交错”,正是钱钟书先生所定义的“通感”。正如钱钟书先生在《通感》中所讲的“亚里士多德《心灵论》里虽提通感,而他的《修辞学》里却只字未提”。陈望道先生这位修辞学大师竟未将其说录入《修辞学发凡》,让世人多忘记了他的挖掘之功。惜哉!
最早明确从修辞学角度对“通感”加以论说的,当推张弓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天津南开英华书局1926年),其书以“移觉”指称“通感”指出:
将甲种感官的作用,移道乙感官上,使文词别生一种美丽。如《史记》:“此与以耳食无异。”《唐书》:“道路目语。”《史记》:“十九人相与目笑。”
其中所说的“耳食”、“目语”都“感觉挪移”或“移觉”,即现在所说的“通感”。
清代叶燮在《原诗》中论及“晨钟云外湿”之句,对“通感”之法亦早有会心:
《夔州雨湿不得上岸作》“晨钟云外湿”句,以晨钟为物而湿乎?……为此语者,因外闻钟声有触而云然也,声无形,安能湿?钟声入耳而有闻,闻在耳,止能辨其声,安能辨其湿?……斯语也,吾不知其为耳闻邪?为目见邪?为意揣邪?俗儒于此,必曰“晨钟云外度”,又必曰“晨钟云外发”,决无下湿字者。不知其于隔云见钟,声中闻湿,妙悟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境界也。
叶燮不仅说其为“不知其为耳闻邪?为目见邪?为意揣邪?”,也高度赞扬“隔云见钟,声中闻湿”不仅是“妙悟天开”,更是“至理实事”。
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说,并不是前人没有注意、理解和认识,只是古代的诗话没有系统的专论,而现代的修辞学也仅是起步,没有达到钱钟书先生之宏论而己。
既然,古今几位大家都将“通感”作为独立的修辞手法,为什么在高中语文教材里却避而不谈呢?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论及唐代诗人李贺诗歌特色在于“修辞设色”时指出:
比喻之法,尚有曲折。夫二物相似,故以此喻彼;然彼此相似,只在一端,非为全体,苟全体相似,则物数虽二,物类则一,既属同根,无须比拟。长吉乃往往以一端之相似,推而及之于初不相似之它端。……如《天上谣》:“银浦流云学水声”,云可比水,皆流动故,此外无他处,而一入长吉笔下,则云如水流,亦如水之流而有声矣。
这种修辞手法,钱钟书先生称为“曲喻”,并被现代修辞学家广泛认同。如刘长卿《听弹琴》:“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听弦音犹如闻松风,这是比喻。而“冷冷”本属触觉,清凉之感,现用作听觉的清越之音。明明是乐声仿佛松风入耳,却听出寒意来。在这里,听觉向触觉发生了转移,从修辞的角度变成了“通感”。可见,诗句带给我们的美感享受是由曲喻和通感共同产生的,而诗句本身是曲喻的修辞手法,通感只是构成曲喻的条件。由此可知,通感有曲喻的作用,而曲喻有通感的铺垫,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共同带给我们阅读和理解的美感享受。编者不单列通感而将其归入比喻,从心理认知上来看就不难理解了。但是,通感与比喻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还是各自为营的好,这样既使于教学,也便于学生对修辞现象的认识与把握。为什么我们偏要让强扭的瓜也甜甜蜜蜜呢?
[作者通联:西藏林芝地区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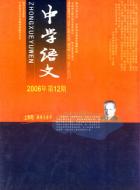
- 构建实用高效的语文知识体系 / 张建房
- 关键是明确课文的教学内容 / 钱吕明 曹伯高
- 情境教学与创造性思维 / 彭俊姣
- 个性化阅读的教学应对策略浅探 / 项晓红
- 阅读教学的三个指向 / 杜长明
- 课外阅读指导的心理缺失及矫正 / 陈万勇 王亚贤
- 语文味哪儿去了 / 张正耀
- 自主学习摭谈 / 朱新凤
- 似曾相识燕归来 / 闻冠军 幸晓艳
- 作文评分:到语言为止 / 黄助昌
- 源头活水与疏导灌溉 / 冯永忠
- 两情若是久长时,也在朝朝暮暮 / 李殿林
- 从《山中访友》看作者之心态 / 任明新
- 轮回思想——解读《赤壁赋》的一把钥匙 / 刘士东 吴秀梅
- 称呼上面见“风云” / 李涨源
- 牵一发而动全身 / 丁志新
- 真情在“打假”中涌现 / 周晓春
- 文言文教学的三个层面——文言、文学、文化 / 曹玉兰
- 一堂舍弃了对否的讨论课 / 徐地仁
- 实行文史课程整 / 吴 梅
- 专题教学不能荒了“自家的园” / 高满生
- 一个普通语文教师的教学感言 / 孙如明
- 文言文阅读中词义的“猜读” / 易国祥
- 说“Q” / 胡 晶
- 从Fans的意译到音译所想到的 / 陶 玲
- 也谈“自”的用法 / 谢政伟
- 为何不言“通感”? / 王崇明
- 应对2007年高考诗歌鉴赏试题的策略 / 陆建生
- 从高考试题看语言表达得体的方法 / 姚芹明
- 十只眼睛断病句 / 潘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