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6年第12期
ID: 355947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6年第12期
ID: 355947
构建实用高效的语文知识体系
◇ 张建房
新课标是对旧大纲的一次大变革,但在知识体系和知识观上,新课标却语焉不详。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树立新的知识观,构建实用的有利于形成学生语文素养的知识体系。
首先需要对旧的知识体系作一个分析。
语文课程里有太多的“垃圾知识”(徐江教授语)。这是语文教育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屡受诟病的原因之一。语文知识无用或者基本无用,可以说已经取得了广泛共识,兹不赘述。我这里要探讨的是语文知识为什么会无用或基本无用。
我认为造成语文知识无用或基本无用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错位:
第一,语言和言语的错位。我认为语文教育是言语教育而不是语言教育,通俗点讲就是语文教育的目的不是研究字、词、句、篇、语、修、逻、文之类,而是让学生学会听说读写。而我们以往的语文教育提供给学生的基本是语言知识。那些从语文现象中分析、归纳出来的知识并不是从言语实践中得来的,而是语文解剖学知识,这些解剖学知识根本不能指导学生的言语实践。言语是活的、动态的,是属人的。语言是死的、静态的,是从与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的。打个比方:言语是个大活人,语言是解剖台上等待解剖的死尸。解剖死人得来的解剖学知识自有其科学价值,正像语言学自有它的价值一样。但用解剖学知识把肢解的尸体拼在一起,绝对拼不成一个大活人。语言学知识同样不能创造活的言语作品。比如语法上讲主谓宾,但实际言语活动中没有人用主谓宾造句,而是用语感!再比如比喻这种修辞格,人们总结出什么明喻、暗喻一大套,先民在造出“硕鼠,硕鼠,无食我鼠”的句子时,何曾想到什么明喻、暗喻之类(那时候它们还没出世呢!),它纯粹是灵光一闪,是激愤和想象的产物。我们不去研究人创造比喻的心理、生活和文化动因,而喜欢把它像僵尸一样放在解剖台上千刀万剐,我们看到的其实已经不是真正的比喻,不是那个鲜活的灵性的产物了,那不过是一堆比喻的碎片!语言和言语的这种错位,使得语文知识跟学生的言语实践不搭界,因而不能指导学生的言语实践。这是百年语文教育低效高耗的根本原因。
第二、知识的辅助性和操作性的错位。百年语文一直在追求可操作性,幻想有一个像使用手册一样的东西,拿过来就能造句行文,就像我们拿着使用手册操作我们家的电器一样。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了解言语活动是发生在心灵里的极其复杂的“动作”,它需要一个人的生活经历、言语积累、文化精神积淀等多种因素的支撑,它不同于简单的、机械的揿按钮的动作。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这样的言语手册。最可悲的是那些基本无用的语言知识居然被当成了这样的言语手册!用使用手册操作电视我们收到了电视信号,用语言知识我们收到了什么呢?
其实有些知识并非完全无用。比如语法,虽然它不能用于造句,但用语感造的句子是否有语病,就不能再用语感检验,这时候语法就派上了用场。再比如文学常识,知道李白的生卒年和代表作,对一个人的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来说,基本上没有意义。但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知识了解李白生活的时代,用最少的时间较准确地把握李白的创作风格。这就像人体解剖学知识虽然不能把尸体碎块拼接成活人,但它能帮助人们了解人体生理结构,并进而了解人体各器官的功能,帮助人们治疗疾病。这实际上反映了语文知识的辅助性。语文知识顶多具有辅助性,而不具有操作性。
第三、手段和目的的错位。如前所述,那些语言学知识顶多具有辅助性,顶多不过是学习听说读写的手段,不料在实际教学中,它却成了教学的目的而教材却成了手段。最典型的就是“例子说”。叶圣陶先生是这么说的:“知识是教不尽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须不断地用心使用才能练成熟练技能的,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叶圣陶《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但在很多引用者那里,“例子说”实际上表达的是教材是落实语文知识的例子。人们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语文课堂上,最常见的就是把一篇篇的美文肢解成各种各样的碎块,然后再在这些碎块中提炼出语修逻文种种知识。在这样的课堂上,老师学生甚至都没有认真读过一遍教材,就更不要说细细地品味,深刻地感受和体验了。没有感受和体验,学生何从体会文字的表现力、文字的魅力和言语作品的诗性与美呢?没有体会,他们如何形成语感,如何学会听说读写呢?在这里不仅找到了语文教学低效的根源,而且找到了学生厌学的根源:没有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会喜欢垃圾。
造成上述三个错位的根源,就是人们经常批评的科学主义。现代教育从根本上讲是科学教育,它把包括语文、哲学等在内的人文学科也视为科学,表现在知识观上,就是形成了客观知识论:“知识是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具有客观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的真理,具有普遍性;它不受认识主体的经验、态度、价值观的影响,具有价值中立性。”(冯建军《让教育与生命同行》《人民教育》2006年第9期)语言知识实际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是纯客观的知识。既然是纯客观的知识,它和作为人的主观行为的言语活动当然就搭不上界了。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追求可操作性是技术主义的典型表现。在工厂里追求可操作性没有什么不对,但在语文里追求可操作性就变得荒唐可笑了。把知识作为教学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人们所说的“知识中心主义”,它是科学教育的灵魂。“知识中心主义”在自然科学学科里,多少还有些道理,因为自然科学学科里的知识确实具有客观性。而语文学科里的“知识中心主义”最终就只能剩下“垃圾中心主义”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知识观出了问题。旧知识观把语文知识看作纯客观的知识,这就把人排除在了语文知识的视野之外,而事实上语文是人学,是关于人的听说读写的学问,不仅不能把人排除在语文知识之外,而且必须把人放在语文知识的中心地位,这是其一。从另一个方面说,即使是对于具有客观性的自然科学知识来说“知识不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结果,而是一种需要主观参与的过程,不是客观存在于某个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的东西,而是要在学习者的参与中才能生成的存在。……知识本身是富有生命意味的,是生命对事物的一种理解、体验和意义的赋予,是基于客观性之上的主观构建,受个体经验、态度、价值观的影响,具有主观性和不断生成性。”(冯建军《让教育与生命同行》《人民教育》2006年第9期)。简言之,不论从知识的构成上,还是从知识的学习上,知识都不是纯客观的;不仅不是纯客观的,反而是以人为本的。旧的知识体系最大的问题是疏离了人,疏离了人的生活世界,扼杀了知识的生命意义。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对旧的知识体系进行彻底变革。我的意见是先不要忙于把它们全丢到垃圾箱里去,可以做一些挑选工作,把那些有用的留下来以作辅助之用。旧知识体系里之所以垃圾太多,除了跟知识本身有关外,也跟用之不当有关。它本来是辅助性知识,你偏把它当成操作手册,当成中心和目的,它当然难当大任了。就像南唐后主李煜一样,你让他当专业作家,他一准能干好,但你让他当皇上,他指定亡国!
其次是开发新知识。其实很多知识,观念一变就开发出来了。比如语感,过去是不把它当作知识的,因为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点也不客观。观念转过来,语感不仅是知识,而且是最有用的知识。有人不是把语感归入隐性知识和缄默知识嘛,当然叫什么名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能接受它。
再比如,文本算不算知识呢?饱读诗书的人叫没知识,一肚子垃圾的反倒成了有知识,这是什么知识观?所以我这里要大声疾呼,文本就是语文知识,是最生动、最富有诗意,因而也最迷人的知识,语文教育就是要倡导多读书,读好书,读经典。海德格尔反复教导我们要学会倾听,其实读书就是最好的倾听,倾听大师之言,在倾听中学会读书,学会言说,更重要的是在倾听中完成个人语文素养的生成和精神个性的全面发展。
再比如,生活知识算不算知识呢?旧的知识体系把人排除在它的视野之外,当然也就把生活排除出去了。没有生活知识,你言说什么?如何言说?又如何理解别人的言说?曹雪芹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红楼梦》就是他用“一把辛酸泪”、满腔悲愤情写就的,而我们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历练,也是读不懂《红楼梦》的。当然语文中的生活知识并不执着于生活的细节,比如如何穿衣、如何吃饭、如何种地、如何做工之类,语文知识指的是“世事”和“人情”。换个说法,语文就是要洞悉人性。一个对人性人情缺乏了解的人,他的语文程度高不到哪儿去。
再比如,可不可以把古今中外文艺理论中的一些适合学生的东西引入语文知识体系呢?例如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它要求我们在阅读一个人的作品的时候,首先要了解这个人,而要了解这个人,就必须了解他生活的时代。这是多么朴素的真理,多么明白易晓的知识。用这一知识指导读书,一下子就能进入文本,与文本展开亲密对话。而那一套文章解剖学知识,总是误导阅读,不仅使阅读效率低下,而且毫无趣味。还比如,古人留下来的一些宝贵的读写经验可不可以纳入语文知识体系呢?例如“书读百遍,其意自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是多好的知识!
新课标实施已经两年了,构建新的语文知识体系,可以说迫在眉睫。这个知识体系可以不是系统的,但必须是实用有效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知识体系必须是属人的,是以人为本的。
[作者通联:山东济宁师专附属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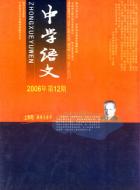
- 构建实用高效的语文知识体系 / 张建房
- 关键是明确课文的教学内容 / 钱吕明 曹伯高
- 情境教学与创造性思维 / 彭俊姣
- 个性化阅读的教学应对策略浅探 / 项晓红
- 阅读教学的三个指向 / 杜长明
- 课外阅读指导的心理缺失及矫正 / 陈万勇 王亚贤
- 语文味哪儿去了 / 张正耀
- 自主学习摭谈 / 朱新凤
- 似曾相识燕归来 / 闻冠军 幸晓艳
- 作文评分:到语言为止 / 黄助昌
- 源头活水与疏导灌溉 / 冯永忠
- 两情若是久长时,也在朝朝暮暮 / 李殿林
- 从《山中访友》看作者之心态 / 任明新
- 轮回思想——解读《赤壁赋》的一把钥匙 / 刘士东 吴秀梅
- 称呼上面见“风云” / 李涨源
- 牵一发而动全身 / 丁志新
- 真情在“打假”中涌现 / 周晓春
- 文言文教学的三个层面——文言、文学、文化 / 曹玉兰
- 一堂舍弃了对否的讨论课 / 徐地仁
- 实行文史课程整 / 吴 梅
- 专题教学不能荒了“自家的园” / 高满生
- 一个普通语文教师的教学感言 / 孙如明
- 文言文阅读中词义的“猜读” / 易国祥
- 说“Q” / 胡 晶
- 从Fans的意译到音译所想到的 / 陶 玲
- 也谈“自”的用法 / 谢政伟
- 为何不言“通感”? / 王崇明
- 应对2007年高考诗歌鉴赏试题的策略 / 陆建生
- 从高考试题看语言表达得体的方法 / 姚芹明
- 十只眼睛断病句 / 潘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