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5期
ID: 147138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5期
ID: 147138
谁在“还顾望旧乡”
◇ 丁明煌
《涉江采芙蓉》(选自《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关于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有人认为是男性,“涉江”者与“还顾”者都是男子;也有人认为是女性,“涉江”者是女子,“还顾”者则是“所思”的男子。《教师教学用书》采用前一观点,认为“这首诗写的是游子采芙蓉送给家乡的妻子”,至于为什么是“游子采芙蓉”而非妻子采芙蓉,“用书”没有作出解释。
对“用书”上的这种解读,笔者难以认同,感觉这种解读过于表面而粗浅。一是诗中“同心而离居”一句的“同心”找不到解读的依托,因为“用书”上的看法只是强调了“游子”单方面思念,因而诗的情感脉络被隔断了;二是诗的意味也浅淡了,无法浓烈地表现两个“同心”的人各怀“忧伤”地“离居”,乃至终老至死。
为此,笔者认为该诗的抒情主人公该是女子为宜,也即说话的人是留在“旧乡”的女子,是她在“涉江采芙蓉”,想送给“所思”的男子;与此同时女子“所思”的男子也在“还顾望旧乡”,感叹“长路漫浩浩”,欲归而不得。对此,朱光潜先生说了两点理由,极为精辟透彻,不妨转述:“头一点:‘远道’与‘旧乡’是对立的,离‘旧乡’而走‘远道’的人在古代大半是男子,说话的人应是女子,而全诗的情调也是‘闰怨’的情调。其次,把‘还顾’接‘所思’,作为女子推己及人的一种想象,见出女子对于男子的爱情有极深的信任,这样就衬出下文‘同心’两个字不是空话,而‘忧伤’的也就不仅是女子一个人。”“‘同心而离居’两句是在就男女双方的心境作对比之后所作的总结。在上文微嘘短叹之后,把心里的‘忧伤’痛快地发泄出来,便陡然煞住。表现得愈直率,情致就愈显得沉痛深挚。”(见人教版“必修2”《教师教学用书》第72页)
既然“涉江采芙蓉”的人是女子,而“还顾望旧乡”的人又是男子,那岂不是该诗有两个抒情主人公了吗?怎么就认定只有一个女抒情主人公呢?对此就该从本诗涉及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法——“对写法”作出解释了。
“对写法”(也有人叫“曲笔”写法等),即抒情主人公撇开自己,从想象对方入手,把“我思人”的情绪折射为“人思我”的幻觉,给人“心已驰神到彼,诗从对面飞来”(《读杜心解》)的感觉,以出乎常情之状,使情感表达更加深沉而余味无穷。《涉江采芙蓉》中“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两句的突然转换,正是使用这一特殊手法的体现。女主人公思夫心切,便想象远方的丈夫此时此刻也心灵感应似的正带着无限乡愁,回望故乡,思家念妻,以曲折的方式,造出“诗从对面飞来”的绝妙的虚幻之境,从而表现“采芙蓉”女子的痛苦思情。
其实这种“对写法”的表现手法在唐代一些表达“思情”的诗歌中常被使用。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本为诗人思念兄弟,却以“遥知”二句翻转一面,化出幻觉,写家乡的兄弟为失落诗人而遗憾不已,似乎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处境并不值得诉说,反倒是兄弟们“少一人”的缺憾更须体贴。又如高适《除夜》:“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诗歌第三句使用“对写法”,撇开自己,从对方入手,想象故乡亲人思念千里之外的自己的情景。再如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该诗三四两句说得更直白,想象家人坐到深夜,“还应说着远行”的诗人。再如杜甫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诗人远在长安望月思家念亲,却想象鄜州的妻子一定一个人在闺房中独自望月,幼小的儿女却还不懂得思念远在长安的父亲;香雾沾湿了妻子的秀发,清冽的月光辉映着她雪白的双臂;最后又回到自己这边来,感叹什么时候才能和妻子一起倚着窗帷,仰望明月,让月光照干他们彼此的泪痕呢?诗一开始便采用设想对方的方式来构思,写得哀婉凄切,韵味深沉。
笔者认为,从“对写法”这种特殊的表现手法角度来解读《涉江采芙蓉》,更能还原诗作的原滋原味,诗的情感脉络更为清晰,表情达意效果更为含蓄哀婉;同时男女抒情主人公之争的问题也将不复存在。
(作者单位:宁化县第一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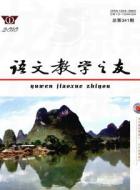
- 中学语文教学几个辩证关系之思考 / 柯孔泉
- 预设语文教学目标要追求科学性和规范化 / 秦海霞
- 好课“四要素” / 金清斌
- “最牛满分作文”引起的思考 / 张旭东
- 小说知识:新课程背景下小说有效教学实现的瓶颈 / 毋小利
- 《天净沙.秋思》配图疑义 / 都自祥
- 检查学生课堂笔记是最好的教学反思 / 赵同生
- 谈《背影》中的“泪” / 李丰旭
- 欢快社戏与悲情故乡 / 佚名
- 在文本细读中激活学生思维 / 钟菊莲 李 琳
- “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质疑 / 李建伟
- 阅读教学中突出重点与整体把握的关系 / 杨泉良
- 浅谈文化对话在文本阅读教学中的意义 / 骆 娟
- “白头”怎么会“搔更短” / 曹芙蓉
- 可将“未必”改为“弗” / 王德志
- 《幼时记趣》中的“物外之趣” / 王日军
- 对苏教版高中《语文》的一点看法 / 田秀娟
- 《六国论》备课二疑 / 陈国荣
- 谁在“还顾望旧乡” / 丁明煌
- 《石钟山记》指瑕 / 彭英姿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赏析 / 马 进
- 兰芝的眼泪 / 肖 武
- 浅析《登幽州台歌》中的孤独体验 / 陈妙珊
- 课文名句串联 / 罗益成
- 营造写作环境,写好记叙文 / 郭光臣
- 课文里的“瞪眼”细节 / 顾霞光
- 浅谈文学作品中的人称改换 / 张庆田
- 为什么作文课经常没有效果 / 任家斌
- 语言描写“三注重” / 倪凌云
- 我的一堂材料命题作文的指导课 / 洪国成
- 破译暗示 准确答题 / 邱世林
- 拨开迷雾见真淳 / 张 清
- “花旦”是怎样“当家”的 / 吴贤友
- 古代“谏”的方式 / 毕长元
- 辨析病句不能只看形式 / 张怡春
- 高考作文备考的理性追问 / 刘学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