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1期
ID: 136445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1期
ID: 136445
要有会看夜的眼睛
◇ 钱理群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新的话题:“睁了眼看”以后,会不会看?
我们还是从鲁迅的一篇文章说起。题目叫《夜颂》,文章一开始就宣布自己是一个“爱夜的人”。接着,就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
在白天,人是穿着衣服,戴着面具的。比如说,我现在站在大家面前,就戴了一个“北京大学教授”的面具。也就是说,我的言行自觉、不自觉地就要受到某种限制,对我自己就有所遮蔽,你在课堂上看见的我,和在我家里看见的我,是不完全一样的;你在白天,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见的我,和黑夜中的我,也是不一样的;到了晚上,特别是一人独处的时候,把衣服脱下,面具也拿下了,这时,就露出了一个真实的赤裸裸的自我。——我想再补充一句:这还不够,因为还有皮肤,皮肤也是一种掩饰,只有连皮肤也撕开,露出血淋淋的筋骨,那才是血淋淋的真实。鲁迅的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那里有血淋淋的真实。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敢面对的。
鲁迅的这一描述,可以看作是一个隐喻:白日,就意味着掩饰、遮蔽;只有黑夜,才有真实。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鲁迅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爱夜的人”:“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
一夜已尽,人们又小心翼翼的起来,出来了;便是夫妇们,面目和五六点钟之前也何其两样。从此就是热闹,喧嚣。而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
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这是一个重要的警示:表面上看,是一个大白天,社会一片光明,但是,在光明之下正“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鲁迅连用两个比喻:“人肉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膏”。这提醒我们:中国“吃人肉的筵宴”里的人肉缸上面有着金盖,吃人肉的鬼魅脸上是涂着雪花膏的。因此,不是你一睁开眼睛,就能一眼看出的。这就有了一个识别的问题,去掉伪饰的问题:能不能看到白日背后的大黑暗,能不能透过种种装饰、层层遮蔽,看到真实,这需要眼力,需要智慧。鲁迅因此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板书:要有看夜的眼睛)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的主题:睁了眼之后,还要有会看夜的眼睛。
我们来具体考察:鲁迅是如何看的?他练出了怎样一双会看夜的眼睛?这也就是前面所讨论过的,我们读鲁迅作品,不仅要了解他的独特见解,更要了解唯他所独有的看世界的方法。在我看来,鲁迅看世界的方法,有四个特点。
一、往深处看,仔细看,看出隐蔽的内情(板书)
鲁迅说过,我看事情太仔细,我对中国人的内情看得太清楚。一个看得太仔细,一个看得太清楚,这大概就是鲁迅看事情的不同寻常之处。他喜欢往深处看,希望看出内情,他要关注的,他要在文章里揭示的,是人最隐蔽的心理状态,而且是人自己也未必自觉的,即所谓无意识的隐蔽心理。因此,在一般人看来没有什么问题的地方,鲁迅却能一眼看出背后的内在问题,揭示出来,就让大家大吃一惊。
举几个例子。
鲁迅有一篇奇文,题目就很怪:《论“他妈的!”》。“他妈的”堪称中国的“国骂”,每个中国人都会骂,即使不在公开场合骂,私下的暗骂也是有的。鲁迅在他的文章里,就提到过这样的趣闻:“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鲁迅说,这里的“国骂”,“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问题是,全民都这样骂,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认真地想过:这样的“国骂”意味着什么,背后隐藏着什么,更不要说写成文章。在人们心目中,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人们忽略之处,正是鲁迅所要深究的;人们避之不及,鲁迅却偏要大说特说,要“论”。“论”什么呢?论国骂的背后隐藏着的国民心理,以及造成这种国民心理的社会原因。于是,鲁迅就作了“国骂始于何时何代”的考证。这样的考证,也是非鲁迅所莫为的,现在的学者不屑于做,也想不到要做。但鲁迅认真地做了,而且得出了很有意思的结论。
他发现,“他妈的”这种国骂大概始于晋代,因为那个时代强调“门第”,即所谓“出身”。人的地位价值不是取决于你的主观的努力,也不是决定于你的才能,而是决定于你的出身。出身于大家族,就可以当大官,这就是“依仗祖宗,吃祖宗饭”。这样的遗风犹存:过去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是“有个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仗势欺人,就是仗着自己父母、祖宗的势力欺人。当一个人受到仗势欺人的人的欺负时,他心里就有股怨气,特想反抗,但是又不敢反抗,那怎么办呢?于是就走一条“曲线反抗”的路:你不是靠着父母,吃祖宗饭吗?我就诅咒你的父母、祖宗,骂一声“他妈的”,出一口恶气,心理就平衡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反抗,但却是靠骂脏话来泄愤,是一种被扭曲的,甚至可以说是卑劣的反抗。这是典型的阿Q心理,“他妈的”一骂,心理便满足了,就忘记了一切屈辱,“闭了眼睛”,天下也就太平了。
你们看,鲁迅对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国骂”看得多细、多深,他看出了内情:一个是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等级制度;一个是中国人一切依仗祖宗,不思反抗,自欺欺人的国民性。而且鲁迅说:“中国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不知道同学们读了鲁迅的这样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有什么感觉?至少以后再有意无意地口出“国骂”,就会有某种反省和警戒吧?鲁迅这双“会看夜的眼睛”实在太厉害了,他把我们中国社会制度的毛病,我们国民心理的弱点,看得实在太透了。
这里还有一例。许多人都喜欢看京剧,尤其喜欢看男扮女装的戏,这本来也没有什么,无非是人们的欣赏兴趣和习惯而已。但鲁迅却要往深处看,要追问这背后隐蔽的心理。于是,他发现,同是欣赏,男观众和女观众欣赏的重点不一样:同是“男人(男演员)扮女人(女角色)”,男人(男观众)看见“扮女人”,女人(女观众)看见“男人扮”。(参看鲁迅:《论照相之类》)
这又是一个十分独到而深刻的心理分析。它所揭示的,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禁欲主义桎梏下所形成的变态性心理:在封闭的社会里,剧场就是一个男女间交往的场所,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借看“男人扮女人”的戏来满足被压抑的性欲。而这样的男人扮女人,不男不女,亦男亦女,也正好符合中国的中庸之道。所以鲁迅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从很普通的看戏,鲁迅却看出了如此深的“内情”:不仅是民族的心理变态,还有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这都是人们并不自觉的“集体无意识”,却被鲁迅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自然难以被接受,直到今天这点还被中国的京剧迷们视为鲁迅“全盘否定京剧和中国传统”的“罪证”。面对这样的误读和隔膜,我们也只有感叹而已。
鲁迅还有一篇分析张献忠杀人心理的文章《晨凉漫记》,我们的选本里有一个摘要。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中,最喜欢杀人的是张献忠,鲁迅从他反对滥杀无辜的立场出发,自然有尖锐的批评,这和毛泽东视农民起义为历史发展动力的立场,是有很大不同的。鲁迅最不能容忍的,是张献忠见人就杀,“仿佛他是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很多人都把张献忠的杀人,归结为他性格的凶残,鲁迅却不满足于这样的肤浅之论,而要深究其内在的心理动因。于是,他发现,张献忠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胡乱杀人,而是有所节制的,因为那时他和李自成争夺天下的时候,胜负未定,他还有可能当皇帝,就不能把老百姓斩尽杀绝。直到李自成在北京坐稳了天下,张献忠知道大势已去,就开始乱杀人了,心想反正这天下不是我的,就要通过杀人来泄愤,“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因此,在这样一种失败的没落的心理下的疯狂杀人,“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或许还有破落家庭的子女),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收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鲁迅在这里实际上揭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处在没落地位的阶级,个人和国家,常常会有疯狂的报复和破坏,看起来好象很猖狂,内心却是很虚弱的。同学们可以以此来观察许多国内国际现象,这样可以明白许多事情的真相与内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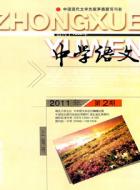
- 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与语文课程改革 / 吴格明
- 作文的本源及其对应的训练体系 / 王相武
- 困惑中思索:语文教学的可能走向 / 杨 旸
- 活化教法,提高教学效益 / 章移珠
- 高三,记叙文写作的瓶颈及应对策略 / 钟 斌
- 作为交际方式的语文 / 郑文华
- 谈“小贵” / 肖 兆
- 思想的蜕变与超越 / 贾小林 晓 喻
- 话说课文修改及其他 / 张厚感
- 物量词“个”的动量化 / 刘 慧
- 语文教科书中幽默语篇稀缺现象之透视 / 黄志军
- “裸”的新义和“裸X”新词 / 李 淼
- 何谓懂得语文教学 / 余映潮
- 《道士塔》的语言表达特色 / 李 华
- 向度 尺度 效度 / 袁 菊
- 要有会看夜的眼睛 / 钱理群
- 《药》教学实录 / 刘永康 朱大伦
- 字形考点:注意测试的综合性 / 李德伦
- 关于细读文本的三点新思考 / 施清杯
- 语言的局限性与活动的可能性 / 胡根林
- 谈选修课的引导探究之道 / 孙志玲
- 为孩子播下思索的种子 / 李爱梅
- 《选读》课堂教学面临的问题与出路 / 杨仕威 应慈军
- 语文教学中的学生主体参与 / 葛德均
- 作文应该是淌出来的 / 杨云法
- 高效课堂的核心 / 陈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