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1期
ID: 136451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1期
ID: 136451
谈选修课的引导探究之道
◇ 孙志玲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关于选修课程的设计与教学”中明确要求:“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是在必修课程基础上的拓展与提高,有的侧重于实际应用,有的着眼于鉴赏陶冶,有的旨在引导探索研究。”但从教学现状来看,许多教师关于选修课程的设计与教学其实是对必修课程的重复,比如作为文言读本的《〈史记〉选读》,要求学生反复诵读文本,归纳重点文言词,进行文本大意的疏通。即使有一些鉴赏陶冶,也终会止步于“引导探索研究”,未能真正实现课标所要求的“拓展与提高”。
本文结合笔者教学的心得研究,以《〈史记〉选读》第三专题中《高祖本纪》的教学为例,来谈一谈选修课的引导探究之道。
《〈史记〉选读》第三专题的名称是“不虚美,不隐恶——《史记》的史家传统”。编者在“专题教学说明”中提出的第一个专题教学目标就是“认识《史记》是司马迁对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余年历史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体会“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卓越品质和无私精神”。所以在本专题中,我们应该通过分析《高祖本纪》,对史家的这一传统进行探究。
一、从面到点抓切入
选修课本上的《高祖本纪》虽是节选,但在教材中的篇幅也有十页之多,在授课时不可能面面俱到、细细讲解,这时必须抓住一个点进行切入。结合本专题的核心“不虚美,不隐恶——《史记》的史家传统”,分析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特点自然是最佳的切入点了。
《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先生称刘邦为“雄主”,将他与楚庄王、齐威王、赵武灵王、秦孝公、秦始皇、汉高祖并列。尤其对《淮阴侯列传》中“汉王夺韩信军”一段作了如下评点:“其举动带有冒险性,而胆气足以震慑臣下之心,刘邦亦雄主也。”
那么在司马迁专门为这位“雄主”所作的传中,刘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这则本纪中,司马迁既写了汉高祖“美”的一面,也写了他“恶”的一面。
“美”的一面,如:抱负远大,豁达大度;善于纳谏,知错必改;审时度势,能屈能伸;知人善用;有人情味。“恶”的一面,如:不事生产,好酒及色,流氓无赖,言行粗鄙。
分析出刘邦的性格特征,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刘邦是一代开国君主,司马迁又生活在汉代,他为何不仅仅写刘邦的“美”,又如何有胆量来写刘邦的“恶”呢?
这时可以很自然地联系到作者描写人物的特点:有美有恶,对美不虚夸,对恶不隐讳。“不虚美,不隐恶”是《史记》体现出的史家传统,是古代良史实录精神的重要内涵。
二、从内到外探内涵
点出史家传统对于学生来说还仅仅在于了解了一个概念,对于文本阅读来说仅达到了表层。到底这一传统有着怎样的内涵呢?这时可以带领学生进一步探索。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然自刘向、杨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在班固以前,刘向、杨雄、班彪等人已经认识到了《史记》“实录”的特点,班固把他们的认识加以总结,肯定了《史记》实录特征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文直事核,要求“史家作史有据,要全面地占有材料,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书,不做任何曲笔或漏略”。对于史实,司马迁都作了细致的调查和取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疑者阙焉”——凡有弄不清的问题就让它空着。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写了孔子“受业身通”的七十七个弟子,明确介绍了在文献中流传的年龄、姓名以及受业情况的三十五人:“余以弟子名姓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不虚美,不隐恶”,是在文直事核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除了以严谨的态度记述,准确地反映事实,善恶必书,要“自觉地表明对史事人物的褒贬爱恨,而且要做到恰如其分”。
所以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既写出刘邦的雄才大略,肯定其统一天下的功绩,也写他好酒好色,奸诈圆滑的市井无赖嘴脸,更写他背信弃义、冷酷自私的本质。在《萧相国世家》中就发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感叹。
三国魏明帝与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王肃谈《史记》时,认为司马迁是因为遭受了刑罚的缘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则反驳说:“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序事理,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由此可知,王肃认为汉武帝是因《史记》直书而迁怒司马迁,这也正说明了《史记》实录的性质。
要做到实录,不仅要求史家要有根有据,全面系统地直书史书,而且要求史家有求是存真的高尚史德。这不仅需要唐代刘知几所说的一个历史家所应具备的“史学”“史才”“史识”,而且需要胆量和气魄。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的晚年,那正是一个酷吏横行、残酷迫害、罗织罪名、严刑苛法的时代,司马迁能够不顾忌当朝统治者的喜怒而秉笔直书,对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记述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北师大韩兆琦教授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一个人有先进卓越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一个人能够把这些思想如实地表达出来就更为难能可贵,而《史记》就恰好正是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勇敢无畏的批判精神和‘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态度。”
三、从本到源明发展
对史家传统内涵的把握不仅仅要停留在静态的层面上,还应引导学生进一步去探究这一传统的源头,了解它的发展情况。先秦时代的史传中已有这种史家传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
(齐)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齐太史和他的弟弟,哪怕牺牲生命也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坚持真理、秉笔直书,司马迁正是继承了良史的这种精神,发扬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传统。
但司马迁的成就比前代良史更进一步。《春秋》微言大义,晋国太史董狐直书叛臣弑君主恶行,但他的记事原则是不隐晦事实真相,评价事实的标准是当时被普遍认可的礼(宗法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虽然弑君者是赵穿,但董狐认为赵盾作为晋国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应对晋灵公之死承担责任,所以董狐写下“赵盾弑其君”,并让朝中大臣都知道。《左传》中记录齐太史和他的弟弟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在史册上记下:“崔杼弑其君”,却对齐庄公的所作所为作了讳饰。这些史家都是据“礼”直书。
而司马迁以一个史家非凡的胆气和高远的见识,无论在写人还是叙事上,始终坚持爱不溢美,恶不毁功的实录原则,不管帝王将相、圣人贤者,也不管酷吏佞幸、游侠策士,是其功,坚决写出;非其罪,决不无故添加。他敢于正视现实,不为感情所左右,对于政治、经济、官僚、文化、战争等诸多方面,真正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如实地写出历史的真相,“创造了崭新的直笔境界,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四、从文到史析影响
追溯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这一史家传统的根源,并了解了它在史学上的进步,可以说对这一传统有了一个纵深的探究。那么本课的探究是否可以到此为止呢?笔者想到了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人文学。于是笔者又带领学生从横向进行探究:从高祖刘邦这一形象中了解到的《史记》这一传统,对后世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描写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据韩兆琦教授研究:“要追溯我国写人文学,甚至明确说到中国小说戏剧的始祖,就不能不首推《史记》了。”文学评论家吴组湘先生在研究我国古代小说时,就特别谈到“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传统对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对人物描写的作用。吴组湘先生在《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一文中写道:
“史传文学作品如《左传》《史记》等采取‘实录’的态度写人物,写得真实丰满、有血有肉。我国古典小说中真正地吸收史传文学写人艺术经验的第一部作品,是文人参与创作的《水浒传》。……认为《水浒传》笔法好,首先表现在它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的高明的写人艺术上。这就使中国小说的人物描写大大推进一步。”明人李开先更是将两者紧密相连:“《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
比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温柔敦厚、敬爱亲友,扶困济弱、仗义疏财。但同时,他题诗明志、聚众反叛,又暗交江湖大盗、虚伪狡诈。又如鲁智深,相貌凶恶却颇懂礼数,自由随性却重情仗义,生性豪放却又粗中有细。
吴祖湘先生还认为:“从《水浒传》开始,而后才有《儒林外史》《红楼梦》。”比如《红楼梦》中的主角: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他们四人无疑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但作者在赞美他们时,并不讳饰他们身上的缺点。贾宝玉的反抗有其软弱性,身上有浓重的贵公子哥的生活习气;林黛玉有才气,却清高、孤傲、多愁善感;薛宝钗温柔敦厚、善解人意而又世故圆滑;王熙凤能干好胜、有魄力,又逞能要强、弄权害人,还有阴谋暗害、刻毒险恶的一面。
鲁迅先生就特别赞赏《红楼梦》:“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却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与写法都打破了。”
以《高祖本纪》为例,笔者对新课标下的选修课程作了一些思考与实践,由面到点、由内而外、由本到源、由文到史,从纵向和横向对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传统进行了探究,既注意到学生现有的接受能力,又扩大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在这一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到,如果每一专题都能真正做到引导探究,必能实现课标所提出的“拓展与提高”这一要求。
[作者通联:南京市第十二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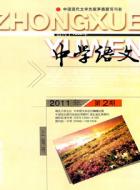
- 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与语文课程改革 / 吴格明
- 作文的本源及其对应的训练体系 / 王相武
- 困惑中思索:语文教学的可能走向 / 杨 旸
- 活化教法,提高教学效益 / 章移珠
- 高三,记叙文写作的瓶颈及应对策略 / 钟 斌
- 作为交际方式的语文 / 郑文华
- 谈“小贵” / 肖 兆
- 思想的蜕变与超越 / 贾小林 晓 喻
- 话说课文修改及其他 / 张厚感
- 物量词“个”的动量化 / 刘 慧
- 语文教科书中幽默语篇稀缺现象之透视 / 黄志军
- “裸”的新义和“裸X”新词 / 李 淼
- 何谓懂得语文教学 / 余映潮
- 《道士塔》的语言表达特色 / 李 华
- 向度 尺度 效度 / 袁 菊
- 要有会看夜的眼睛 / 钱理群
- 《药》教学实录 / 刘永康 朱大伦
- 字形考点:注意测试的综合性 / 李德伦
- 关于细读文本的三点新思考 / 施清杯
- 语言的局限性与活动的可能性 / 胡根林
- 谈选修课的引导探究之道 / 孙志玲
- 为孩子播下思索的种子 / 李爱梅
- 《选读》课堂教学面临的问题与出路 / 杨仕威 应慈军
- 语文教学中的学生主体参与 / 葛德均
- 作文应该是淌出来的 / 杨云法
- 高效课堂的核心 / 陈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