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8期
ID: 136302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8期
ID: 136302
“真美”与“苍白”
◇ 苑青松
《背影》结构严谨、情感真挚、内涵丰富,尤其是父子间那种难以言状的情感表达独具特色,使之得以成为中国20世纪的散文经典名篇之一。
一、“真美”的感情和感情的“真美”
《背影》的主旨和对主旨阐释的手法赋予了文章特殊的内涵,使《背影》的主题既属于父子之爱的普遍范畴,同时又极具典型化的特殊意义,它让读者感受到无比震撼的心理力量。
(一)“真美”的感情——跳出窠臼
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大陆作家张承志都写有散文《背影》,但其在广大读者头脑中已没有什么记忆。但朱自清的《背影》自从1925年在《文学周刊》上发表以来,许多名家都曾对《背影》发表过评论,一直受广大读者青睐,这主要得益于《背影》“真美”的主旨。《背影》的主旨从总体上说是写父子之情的,如果《背影》的主旨只是写笼统的父子之情,读者就不可能引起太多的共鸣,也不可能在众多抒写父子之情的文章中脱颖而出。《背影》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反响,主要得益于能被各色人等广泛接受的、独特的父子情怀——“真美”的主旨定位。《背影》中丝毫感觉不到父亲对儿子的“教训”和“威严”,感觉到的是由父子隔膜、家庭困顿、社会动乱等复杂因素造成的复杂情感在“背影”后的突然释怀,表现出来的主旨不仅是“善”,更多的是“美”和“真。”父子之情在忽然之间的相怜、相爱、相通,最能勾起读者关于人与人之间情感变化的共鸣,从而可以看出,《背影》的主旨跳出了一般父子之情的窠臼。
(二)感情的“真美”——回归本能
《背影》“真美”主题的确定跳出了一般父子之爱的窠臼,引起了广泛共鸣,极具美学价值。那么,《背影》在对这种主题的抒发上也体现出“真美”特色,它主要是采用点、线、面三位一体来实现的。
1.买橘片段——以点聚“真”
凡是读过《背影》的读者,印象最深的当属买橘片段,它近距离的为读者展示了“真美”的主题。
“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
这是“聚真”的前提,由此造就了一幅感人肺腑的图景。它主要通过细节来勾勒的,一是恰切的动词:走到——探身——攀着——缩——微倾——抱了——散放——爬下——放——扑扑。这些动词简洁恰切,准确地展现了父亲过铁道买橘的动作,然而这只是好像图画中的几个粗略线条而已,仍需衬托和修饰。二是传神的副词:蹒跚地——慢慢——向上——向左——慢慢——一股脑儿。这些副词的运用对父亲的动作作了很好的修饰和衬托,真正起到了传神的作用,使那些动词充满情感气息,细腻地表现了父亲的情感之真。
2.背影闪现——以线串“真”
文中四次出现父亲的“背影”,文章开门见山写道: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直接用“背影”点题。文章中间两处写了“背影”: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的背影。”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
这两处“背影”是析题。文章最后写道:
“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这是扣题。点题——析题——扣题,“背影”使文章浑然一体,充分显示出父亲对儿子的本真之爱,真爱之久。同时,也显示出“我”在父亲的本真之爱、细腻之爱面前,心中虽情感汹涌口中却几乎失语的真实状态,于是“我”丢弃了无力表达此时父子之情的语言,“无奈地”换成了一幅幅变换的“背影”图画,“我”在图画一次次地冲击下,眼泪一次次地夺眶而出: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我的眼泪又来了。”
“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背影”与眼泪在“我”的眼里不停地变换,自然、十足地表达了父子之间相爱、相怜、相通的复杂情感,真实感人,共鸣不绝。另外,“背影”贯穿文章始末,把情感之“真”从头到尾串连起来,极具震撼力和吸引力。
3.父亲之“迂”——以面铺“真”
作者在写父亲送站的片段里,着力铺陈父亲的“迂”,主要从两个方面着笔。
一是父亲的表现:
“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
“他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
“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
“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觉些,不要受凉。”
从父亲的这些举动里,确实显得面面俱到、啰哩啰嗦,体现出“迂”的行为特点。但父亲近乎“迂”的行为给人的感觉却不是“迂”,它展示出长辈对晚辈那种自然本能的纯真之爱到了近乎“迂”的程度。
二是“我”的反应: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
“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
“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在描绘“我”反应的这几句话里,作者变换着不同的时空来写。一方面写第一时空的感受——强化父亲之“迂”,一方面写第二时空的感受——反衬父爱之“真”,在时空变化之中,表现出“我”对父亲“真爱”的理解与释怀。
父亲的行为之“迂”和“迂”爱之真,与“我”的感“迂”和感“迂”爱之“真”互相映衬、融为一体,为作品铺下了深厚的“真爱”底蕴。
4.立体呈现——三维融“真”
买橘片段、父亲之“迂”和“背影”闪现呈现出三维立体的表现模式,三者或明或暗,或实或虚,或并行或重叠。
在买橘维度里,有两次“背影”的闪现;同时也有父亲之“迂”的铺垫:
“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
在这里买橘是聚焦点,“背影”闪现和父亲之“迂”是暗,是虚,是底。
在“背影”闪现维度里,“背影”是纲,是脊,父亲之“迂”和买橘片段是纲中之目,是脊上之峰,它们有时是并列的,有时是重叠的。例如:买橘构成“背影”中的一部分,有重叠之味,父亲之“迂”是衬托“背影”的,又有并行之味。
在父亲之“迂”维度里,它也经常闪现在“背影”和买橘维度里,以反衬父爱之“真”,对凸显“背影”起到了很好的铺垫和支撑作用。
总之,作者从点、线、面三个维度,采用立体呈现的方式,把“真”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凸现出来,很好地诠释了主题,把普通的主题往无限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延伸,让人体悟多多,品味无穷。
二、“苍白”的语言和语言的“苍白”
《背影》的语言质朴、简洁、饱含情感,叶圣陶对此作过高度的评价:“这篇文章通体干净,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多余的字眼,即使一个‘的’字一个‘了’字,也是必需用才用。”①大家对文中叙述性语言作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然而,最能揭示父子内心情感的对话语言,却或为大家忽视,或没有进行深入的追问,由此势必造成对主题理解的单薄。
(一)“苍白”的语言
《背影》中父亲总共说了五句话:
“事已至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进去吧,里面没人。”
《背影》中的“我”只说了一句话:
“爸爸你走吧。”
这六句话没有铺陈、渲染,也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漂亮的修辞,若单独抽出来看,平淡无奇,从文字表面看实在是“苍白”的语言。
(二)语言的“苍白”
《背影》中的对话语言可以说是“苍白”的,然而,但凡读过的人大都感受到了其震撼人心的力量,弄清矛盾的个中缘由,是阐释本文的关键所在。
这里牵涉到语言使用的层次问题,顾久先生对此作过较为细致地分析:“语言运用至少有两个层面:一是日常的、社会的层面,其间又可分为(1)关系政治制度、国家命运等的语言使用;(2)道德境界的语言使用。二是哲学的形而上境界的层面。其间又可分为:(1)审美境界的语言使用;(2)宗教境界的语言使用。”②由此可知,在道德和宗教层面,语言是“苍白”的,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样,当人面对情感之极和所谓万物规律的“天”时,只能“予欲无言”(《论语·阳货篇》)。
通过分析,语言在使用上大致有三个层次:日常交流层面的语言——很随意的表达;后天养成的语言——有一定文采的表达;道德宗教层面的语言——“苍白”的语言。
三、“真美”与“苍白”
《背影》中的父子之情,是在父子隔膜、家庭困顿、社会动乱、长期分离背景下,是在本能自然的情态中展示出来的,父子之情在瞬间达到了一种情感的极致,这种情感的极致使“我”内心澎湃、思绪万千。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父子的情感已经深入到人性的、本质的层面,上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
正因为它上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所以《背影》对话语言的“苍白”就不难理解了,人类的语言很难表达出上升到道德宗教等“形而上”高度的内涵;然而,这种“苍白”的语言运用正符合第三层面的语言运用特征,它反而真实地反映出父子情感之“真美”。
人性之“真”是具有永恒、普遍意义的主题,《背影》无论是主题还是语言,都在最高层次上展示出“真”字,极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这大概就是《背影》备受人们喜爱的原因吧。
————————
注释:
①郑国民:《中学语文名篇的时代解读》,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②顾久:《先秦诸子语言使用的层次问题》,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第4期。
[作者通联:河南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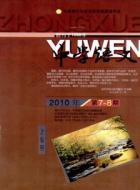
- 依“法”导读 / 李安全
- 《简笔与繁笔》课堂实录 / 刘永康 潘纪平
- 汉语的视觉动力感与审美愉悦 / 卢卫平
- 生命体验的真实课堂 / 史绍典
- 谈“肺腑” / 谢 葵
- 《陈情表》解读 / 王济凡
- 谈网络语“被××” / 朱大伦
- 关于《山羊兹拉特》的多重主题解读 / 朱前珍
- 把精致训练进行到底 / 刘 祥
- “真美”与“苍白” / 苑青松
- 与生活同行,与教材同步 / 张兴武
- 诗歌“多元解读”的底线是什么 / 代春生
- 敢问语法教学路在何方 / 余志明
- 《边城》人性探讨 / 金 艳 陈 鹏
- 新诗改罢自长吟 / 龚冬梅
- 归园田兮,归山水兮? / 林志强
- 评课之后话语文 / 邓木辉
- 经营精神道场 / 陆锋磊
- 构建“分组合作,目标具体,问题引领”的高效课堂 / 朱浩军
- 在个性化研读中提高精神品质 / 陈桂春
- 基于生本教育理念下的高中语文有效教学摭拾 / 周 刚
- 语文课堂:追求有效拓展 / 吴蔚萍
- 现代文阅读探究性试题的解题应对策略 / 浦培根
- 考场作文缺憾的临场补救 / 丁卫东
- 现代文阅读简答设题点探究 / 李弗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