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12期
ID: 136403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12期
ID: 136403
碎片与灵魂
◇ 苑青松
语文自单独设科以来,语文课程科学化一直是语文界同仁孜孜追求的目标。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外部形势的变化,语文教育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让人引以为豪的成就。然而让人困惑的是,这些成就在落实到“人”上时,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变化,甚至招致更多的批评,引来更多的问题。顷刻之间成果就变成了问题,于是再创造出新的成果,又出现新的问题,语文教育便在问题与成果之间的“振摆”中回荡,这让人不得不追问这样一个问题:语文课程到底缺少什么?
一、不解的现实:一派碎片化的繁荣
30年来,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语文课程理论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显示出一派繁荣景象。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产、多变的课程纲要
课程纲要作为具有国家法规性质的文件,反映了国家的意志,显示了学科发展的方向,决定了学科实施的成败。30年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与语文课程专家对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梳理20年来(1978-2001)语文课纲的发展,至少可以看出四方面的信息:时间跨度是20年,空间领域包括小学和中学(后来变为九年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数量是17个(中小学),称呼上有“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两种。我们再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在过去的30年间语文学科出台了17个课程纲要,课程纲要变更的时间跨度最大的为6年,最少的为1年,并且只有一次是6年,其余都是一至二年。从这些数字上可以充分说明两点:一是课程纲要的绝对数量是丰硕的,二是课程纲要的变换是快速的。从课程纲要的角度上体现了语文课程研究成果的多与快。
(二)多元、多维的语文课程理论
语文课程理论经过30年的发展,表现出“外延缩小、内涵扩大”的特点,“外延缩小”标示出语文学科的科学化,这主要体现在语文认识上的科学化。人们对语文的认识经历了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政治、语言文学、语言文明、语言文化等的发展轨迹。几十年来,语文课程在语文认识上的理论成果,使人们逐步明白叠加在语文上的种种外衣模糊了语文的界限,使语文成为囊括一切的“博物架”。“外延缩小”是语文学科剥芜离杂、不断科学化的结果,这一结果是由大量出现的语文学科理论来完成的。“内涵扩大”主要标示出语文学科的综合性,这主要表现在语文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广泛联系上,语文教育研究不再在蜗牛壳里造物,人们开始从教育学、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美学、哲学等方面来观照语文,极大地丰富了语文的内涵,引发了语文性质的大讨论,并由此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语文课程与教学方面比较著名的专著就有上百部。内容涵盖语文知识能力、过程方法、情感价值以及语文教师专业化发展等内容。这些都充分展示出语文课程理论成果的多元化、多维度态势。
(三)多套、多本的语文教材
“教本,教本,教之所本。”教材是教学的主要凭借。教材是语文课程理论研究成果的一个缩影。(1979-2003)24年来,语文教材的研制也逐渐走向繁荣,从语文教材信息表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以初中(新课改后划入义务教育范围)和高中为例,人教社共出版了16套语文教材。再加上新课改后“一纲多本”语文教材理念的提出,北师大版、苏教版、西南师大版、语文版等教材也相继研制成功。从内容、体例上看,语文教材尽力摆脱政治、经济、制度等外部因素的干扰,逐步转到学科本体上来。1979和1981年版是“拨乱反正”的产物;1982和1985年版开始转到语文知识上来,展现出明显的“工具”特色;1989、1996和2000年版是“工具性与思想性”并重的反映;新世纪版的是“工具与人文统一”的缩影。语文教材发展轨迹,是语文教育理论成果的综合反映,是对语文教育规律深入认识的结果。30年来新教材的陆续推出,展示出语文教材“多套、多本”的丰硕局面。
(四)多轮、多层的语文师资培训
教师、学生和教材是教学的三大基本要素。师资的好坏直接决定教学的质量。因此,新课程推行前国家颁布了《国务院课程改革与发展纲要》、《关于开展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师资培训文件,为适应新课程的需要推出了师资培训的“五年计划”,掀起了师资培训的高潮。
从上面以河南为例编制的语文教师培训信息表(全国也基本如此)可以看出这样几组信息:一是对语文教师的培训是全员的;二是对语文教师的培训是多轮的;三是对语文教师的培训是分层次的。如此全额、多轮、多层次的师资培训,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从客观上讲,师资培训能有力地促进语文师资水平的提高,进而优化语文课堂,提高语文教学的效能。
另外,语文学术期刊、远程网络课堂、电子图书馆建设等课程要素也都展现出勃勃生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综上所述,30年来,语文界同仁在语文课纲、语文教材、语文教法、师资培训等方面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这些所要服务的终极对象——语文教学,仍然没有多少起色,教师依然我行我素,学生依然兴趣不高,在众多繁荣之中难见语文教学的“繁荣”!于是,成果成了“碎片”,繁荣成了“碎片”的叠加。
二、直观的比对:一个神话般的案例
“语文是一门工具性、人文性、实践性、综合性的学科。”语文理论固然不可或缺,但也决不可能替代实践。个案是理论的实践化,同时也可佐证、创新理论。为此,我们打开一个神话般的案例,一为避开理论的灰色和说教的苍白;二为展示一个真实的语文形象,而不总是停留在对语文想象的理论勾勒中。
(一)课程技术上的简单化
贵州石门坎地处乌蒙山区深处,隶属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自治县,山高路险,土地贫瘠,终日浓雾不散,常年多雨且气候变化无常,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石门坎苗族在彝族土司制度的统辖之下,他们没有土地,集体上沦为土目的奴隶;几乎没有一个人读过书识过字,可以说苗族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一个“三零”层面。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Samuel·Pollard)在这样一个“三零”平台上,创办了石门坎光华小学,并形成了石门坎课程模式。
1906年,石门坎光华小学开办,这一时期正处于清政府实行“新政”,提出“废科举、兴学校”的口号,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它标志着我国现代教育的开始。从石门坎学校的课程来看,国民政府成立前,初小主要是启蒙教育,教儿童识字,了解一些自然风物;国民政府成立后,就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开设课程,另增加了圣经课和苗文课。石门坎教育的课程与当时国内其他地方并无二样。
从石门坎学校的教材来看,主要有四类:一是识字教材,例如《三字经》、《百家姓》、汉语版《圣经》等;二是经学教材,像《四书》《五经》等;三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语教材;四是自编乡土教材,《苗族原始读本》和《黔滇苗民夜读课本》(扫盲用)。
从石门坎学校的语文教材看,都是传统的识字和经学教材,外加《苗民原始读本》和《黔滇苗民夜读课本》,其内容和体例主要参照陶行知的《平民识字课本》。由识字逐步过渡到丰物、自然、习俗、求学等。
从石门坎教育的师资来看,历任校长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普通教师学历都不是很高,大多都是高小、中学毕业,薪水也极低。
从上面的梳理看出,石门坎教育中的课程、教材、教师并无高明之处,课程技术含量也很低,其实质不过是一场“识字扫盲”教育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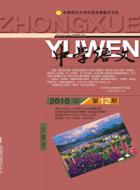
- 曾祥芹语文教育思想浅论 / 邱福明 曹明海
- 闻荒立拓乐为先 / 李杏保
- 曾祥芹教授语文教育理论探索之路 / 曹洪彪
- 作文教学必须回答的三个问题 / 代保民 丁雪梅
- 碎片与灵魂 / 苑青松
- 治学和做人是二而一的事 / 韩雪屏
- 探究《雷雨》(节选)的解读视角 / 郑莉萍
- 审视与反思:“语用问题”的特异个案 / 潘 涌 王奕颖
- 悲凉人生中的缕缕温情 / 徐昌才
- 让学生尽享成功的喜悦 / 李启明
- 语文新课改:并不等于拒绝教学返真归本 / 顾 勇 董旭午
- “冰山原则”下的《桥边的老人》 / 史绍典
- 红领:一个中西合璧的新词 / 刘昭琪
- 语文教材编制的审视与反思 / 孙慧玲
- 汉字教学方法摭谈 / 裴正菊 杨字玲
- “杯具”之“杯” / 刘 莉
- 高中生阅读理解能力发展研究概述 / 戴方文
- 从“奔奔族”说起 / 苏永慧
- 湖海江山作课堂 / 宁冠群
- 论深度阐释 / 王 飞
- “给力”正流行 / 肖皿舟
- 魏晋清谈与语言能力训练 / 黄妮妮
- 文本解读的“相对论” / 崔国明
- 撰写另一种学案 / 何明锋
- 快餐式语文教学PK烹饪式语文教学 / 陈颂善
- 《夏天的旋律》的语言教学尝试 / 张 颖
- 惯用语的离合 / 穆亚伟
- 谈语文教学中的诗词教学 / 韩世姣
- 香港中学语文听说课程设计管窥 / 杜少凡
- 高考作文的四大病灶 / 何 郁
- 200海内外学者参加的“曾祥芹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圆满成功 / 张正君 耿红卫 米格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