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4期
ID: 136173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4期
ID: 136173
新理性:语文教育的文化精神建构
◇ 邱福明
十年前的1999年,我们迎来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语文课程改革经过艰苦的摸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语文教育理念到语文教育实践,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初步实现了语文课程功能的转变,体现了语文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密切了语文课程与生活和时代的联系,学生的学习方式得到初步改善,正在逐步建立与素质教育相一致的评价与考试制度,语文课程资源不断得到开发和利用等等。然而,“语文课程改革在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理性看待并进一步研究。反思当前的语文教学,以下几个关键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工具性和人文性不能割裂,脱离文本、架空语言的教学不足取;对‘语文素养’概念的界定需要明晰;对话不等于谈话,教师的角色是‘平等中的首席’;语文训练不等于语文‘操练’;诵读是基于理解的一种声音表达形式,关键在于理解文本;语文教师的主体性不容漠视。关于语文教育体制、考试模式、选修课制度,也存在一些争议,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①语文课改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存在诸多困惑,也遭受了诸多批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可能走向天堂,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因此,对语文课改十年的文化思想进行检视,不仅有助于我们明了成绩、困惑与批评,还将引领我们走向更合理、更健康的语文课改之路。
一、回顾:课改十年语文教育的文化思想检视
文化思想作为某一阶段语文教育的指导思想,必定会影响到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内容选择、实践操作等。回顾语文课改文化思想的十年历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工具理性批判与人文精神回归阶段(1999年—2004年)
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对20世纪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一脉相承的语文教育无论在其理论建构还是时间探索上都受到了这一文化思想的冲击,呈现出明显的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倾向。比如教学大纲的明确化、教学内容的陈旧化、教学方法的机械化、教学评价的标准化等等。语文教育在追求“科学化”过程中陷入技术主义、伪科学主义的泥潭。对语文教育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倾向的大肆批判终于在1997年引发。《北京文学》第11期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刊登了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等三篇文章,由此引发了20世纪末语文教育问题大讨论。人们对语文教育的批评热烈而活跃,无论就批评的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语文教育批评无法相提并论的。矛盾集中在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上。如有学者批评指出“如何评价现代语文教育的问题,就其实质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语文教育观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对于人的观念的问题,关于人的价值的问题”、“回顾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我们的语文教育的确是大大忽略了‘人’。语文教育漠视了精神,忽视了精神,也就榨干了情感,泯灭了灵性,教材与课堂也就无趣无味,干巴枯燥,贫乏单调,形同于自然科学,形同文字游戏。”②这种批评体现出对人文性的弘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在该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中,一些论争者都希望语文教育能够承担起更多文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想赋予语文学科更多的审美意识、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等,张扬语文教育的人文精神,强调把语言看做生命主体、生命整体,强化人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1999年开始实施的语文课改可以说是顺应了这种呼声。《语文课程标准》在“语文课程性质与地位”一章开宗明义:“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是语文教育人文性回归的重要标志。随后,人文精神的回归在语文课程改革的理念和实践等各方面逐渐占据了上风。语文教育要回归人文根本,抓住人文血脉,这也是语文教育真实、自由、个性的本然所在。人文性是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显著标志之一,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不仅体现在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广泛的教学内容上,还体现在生成性的教学方式以及平等的师生关系上。强调立足于学生的培养与成长,立足于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用怎样的“人类文化”去滋润和培育他们,并采用正确而良好的培育方法,回归语文“人文性”的应有之义和基本内涵。
(二)人文精神泛滥与理性精神呼唤阶段(2004年—当前)
语文课程回归人文精神是语文本色回归的内在要求。比如教材摒弃了《狼和小羊》、《农夫和蛇》等经典的寓言故事,对这些不再符合时代发展的人文精神内容的清理,就已经体现了现代人文精神,是呼唤人文精神回归的有力表现。 但对于人文的理解偏差或者极端化强调,又导致了人文精神在语文中的泛滥。比如在具体的课程内容上,泛语文现象深受批评。“当语文教学擎着人文大旗一路高歌猛进时,忽然发现阵营里出了一个异端——泛语文现象,于是不断有人仗义讨伐。这种讨伐大都是在语文是什么或语文不是什么之类的本体论上展开。但是由于语文本体论的争执一直没有一尊可定,讨伐显得有些仓皇,自然收效不大。泛语文现象依然以人文之名,波澜壮阔地蔓延下去……如此泛化语文,其后果将会是如王尚文教授曾忧心忡忡地指出的那样,语文会走上‘自我消亡的悬崖’。”③“课程改革后课堂的最大特点就是学生的活动明显增加,课堂气氛较为活跃。但是,有的教师刻意追求课堂效果而冷落了文本。教者设计了一些‘画画、唱歌’等环节,使课堂多了些‘花拳绣腿’,华而不实,既浪费了宝贵的教学时间,又不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弄巧成拙,犯了教学之大忌,令人心痛。”④不难看出,经过几年的新课程改革实践,大多数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都已贯彻了新课改理念,但一些教师对新课程的精髓还没有真正理解,在人文精神“外衣”的笼罩下,脱离了语文课程人文性的正常轨道。例如课堂教学的形式化就是新课改的一大误区。课堂教学的方法上受到深刻批判,普遍认为语文课堂教学存在表面的形式主义。
经历热热闹闹的前期课程改革后,随着课改的深入,许多深层次问题不断涌现,近几年引发了一股理性反思与有效修正的热潮。人们逐渐开始沉静下来理性思考存在的问题,期望对语文课改有更为全面、辩证、清醒的认识。最先反思的大概是1997年语文教育大讨论发起人之一的薛毅,他认为当年的浪漫主义哲学情结,导致了新语文“语文特性”⑤的缺失。如有学者指出语文课改当前应该从理性回归的角度考量:“语文教学目标必须以提高学生语文素养为旨归、语文课程性质要真正达成“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共识、语文教材要坚持编审分开和讲究科学使用的原则、语文教学方法的选用要以‘不断优化,注重效果’为标准。”⑥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语文新课改“在弘扬人文精神的同时弱化了知识与理性精神”、“倡导开放性与多元性导致教学的随意与放纵”、“语文现代化进程中,丢弃了一些传统的做法与精神”⑦等。很显然,人们在热烈地呼唤着语文课程改革理性精神,提倡在面对当前语文课程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在理性反思下科学践行语文课程改革。
在检视语文课改十年文化思想后,我们发现其存在两点错误:一是错误地将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同起来;二是错误地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这一等同,这一对立,使过去的语文界对人文精神的极度忽视,将科学理性狭隘地窄化成工具理性在实践中大行其事。而在课改后人文精神的回归又把握不准确,还将科学理性像泼脏水一样全然抛弃。因此,我们不禁要问:提倡科学理性为什么一定要将科学理性狭隘成工具理性和实用理性?人文精神的回归又为什么要全然抛弃科学理性?语文课程改革走到今天,下一个思想路标是什么?我们不禁茫然起来。在本文中,我们选择“新理性”作为未来语文课程改革新路标的概念总称,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立场的理论表述来建构语文课程改革的文化思想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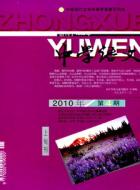
- 新理性:语文教育的文化精神建构 / 邱福明
- 2009年度语文理论热点追踪(下) / 温立三
- 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整合的取向和实质 / 周子房
- 一元层层深入的文本分析是多元解读的基础 / 步 进
- 阅读课“问题教学”的有效性审视 / 马 磊
- 在课堂上播下发现和创新的种子 / 王 敏
- 试析语文选修教学探究性学习的探究角度 / 徐 静
- 三维链接 点燃诗情 / 李正浪
- 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刍议 / 萧兴国
- 善于从问题的对立面入手 / 冯述田
- 试论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形式逻辑训练 / 陈宏明
- 感悟韩军的“一”和“三” / 夏玉桥
- 呼唤真情回归 促进读写结合 / 李 娟
- “秒杀”的秒变 / 陈维贤
- 试论苏教版写作指导的有序整合与训练 / 丁爱华
- 文言文注释问题商榷 / 熊惠芳
- 存在的神话 / 文 勇
- 借助语文选修教材加强高考诗词教学 / 戚光宇
- 《荷叶 母亲》课堂教学实录与点评 / 余映潮
- 高考作文,事例也“开花” / 姚尚春
- 秋水芙蕖,倚风自笑 / 邓嗣明
- 语文,暖暖的诗意 / 史绍典
- 无意寻秋秋自现,有心藏情情难掩 / 王纬明
- 论开放的高中语文课堂教学实践 / 黄明勇
- 质疑的策略探究 / 孙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