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12期
ID: 356345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12期
ID: 356345
在史官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报任安书》的写作目的
◇ 张福旺 王桂霞
公元前91年,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因“戾太子事件”受到牵连,蒙冤入狱,待死之际,写信给司马迁,请他在汉武帝面前为自己明冤辩屈。司马迁后来给任安写了一封长信回复,即《报任安书》。此封长信经删节选入了高中语文教材。按常理,司马迁在回信中,对任安的求助该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是去汉武帝面前帮他明冤呢,还是不帮?但司马迁在信中却以极委婉含蓄的方式,回避了对任安求助的直接答复,而是详细地述说了自己六年前因替李陵辩诬而触怒汉武帝,下狱获死罪,而后自乞宫刑,在屈辱中隐忍苟活的处境,以及自己撰写《史记》的情况和心愿。书信往来是当事人双方在特定语境下的话语交谈,故司马迁的婉转之辞,任安定能深明其义,而我们今天解读这篇文章,是在时隔两千多年之后,又是在当事人特定的语境之外,要明了文章的内容,特别是在书信内容被大幅度删节的情况下,却有很大的难度。具体说来,在此文的教学过程中,最难把握的问题就是此信的写作目的,换成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他在信中,针对任安的求助,表明了自己怎样的态度?要理清这个有些费解的问题,除了要把握此信的内容,还须联及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史官文化背景。
一、著成《史记》,是司马迁的历史使命,也是他人生的最高价值、终极追求
尽管是在这封长信的最后,司马迁才向任安谈到了自己撰写《史记》的情况,但这一部分的内容,恰是理解司马迁写这封长信目的的关键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是先秦三代绵延相继的史官文化。史官文化写史、读史、并通过历史对现实人生作价值裁判的传统,形成了中国人特别是社会主流阶层(统治者、文人士子)强烈的历史意识。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不仅培养了中国人以史为鉴、注重用传统的规范指导现实生活以及用传统的价值衡量现实人生的实践理性,更重要的是,它还塑造了中国人是从历史的存在中寻找生命的超越性和人生的终极价值这一文化心理,通俗地说,就是把名垂史册、流芳百世看成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并由此获得生命的不朽。《左传》记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在回答晋国大夫范宣子问什么是“死而不朽”时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最早对人生的终极价值、生命的超越性所做的明确的阐述,后人把它概括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史官文化对司马迁人生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出身于史官世家(司马迁祖先世典周史,其父司马谈为汉太史令),自己后来亦做了史官的司马迁,既受父命、也因史官职责的要求,要自觉地承担起写史著书、延续史官文化传统的历史使命(《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载:(1)司马谈临终前遗命司马迁,要他记史著书,延续司马氏一族在先秦三代记史的传统,不废天下之文。(2)司马迁也自认为有延续孔子作《春秋》的文化使命)。其次,司马迁也从父辈那里秉承了史官文化从历史的存在中寻找生命的超越性和人生的终极意义的价值传统:司马谈临终前亦曾遗命司马迁一定要“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他自己在《报任安书》中也说:“立名者,行之极也。”这样,司马迁撰写史书就有了双重意义:首先,是完成文化使命,是对家族、对历史的责任;其次,是通过“立言”获得生命的超越性,走进历史,名垂千古,死而不朽。关于这两者,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明确的表达:他说自己因“李陵事件”获死罪后,为求生而自乞宫刑“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私心”是自己的内心追求,个人承担的义务、责任;“文采”是指自己的文章著作。
那么,司马迁的私心是什么?文采又是什么样的?他在《报任安书》中直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通过记史论史完成这样一个宏大的文化目的。基于自己的家学、职业和师承(司马迁从10岁起即从师儒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司马迁比一般文化人更能洞见到那些具有创造性的文化活动,对人类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所以,他在信中列举的那些已经名垂千古、并引以为自己人生楷模的人,如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都是在人类的思想文化领域有创造性贡献并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人。而司马迁自己呢,他坚信自己从青年时代就着手准备、已积蓄多年并正在撰写过程中的《史记》,无论是从规模、形制、史料的完备与真实,还是从记史的语言能力、考察历史的思想深度及论史的学术追求等方面看,都一定会成为中国文化史中不朽的鸿篇巨制。这种自信,在《报任安书》中的这两句话里可以看出来:“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已着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二、幽于粪土之中隐忍苟活,只是为了完成《史记》
司马迁对于生命的价值有明确的认识和选择,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重于泰山”的人生,就是让生命通过创造性地活动,在现实世界建立非凡的功业,对历史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从而使人类个体生命的存在,超越自我、超越现实,走进历史,获得不朽。司马迁当然选择的是重于泰山的人生,他相信《史记》的创作,能让他实现对人生的这种超越性追求。所以,他在信中和任安说,自己当初因“李陵事件”入狱获死罪后不能选择死,因为那时《史记》正“草创未就”,以自己一个普通士子文人的身份,“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当时选择受死,人生无疑“轻于鸿毛”,对社会和历史没有丝毫的价值。
但对司马迁来说,选择活下来又何其艰难:首先,他身为文人士子,深知中国文化传统注重“士节”,主张文人、士大夫在生死关头,为维护人格尊严要坚持“临危不辱”的价值操守,他也认同这一人格操守;因为熟知历史,他又深知古往今来,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黎民百姓,只要获罪入狱,就要遭受种种肉体和精神上的凌辱。他在信中说:周文王、李斯、韩信、彭越、张敖、绛侯、魏其、季布、灌夫这些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因此,他本应该在获罪之后、入狱之前就通过自杀的方式,有尊严地死去,而免受入狱后在精神和肉体上的种种屈辱。其次,他要活下来,唯一的途径是自乞宫刑,而这一求生的方式是要承受人世间最极端的人格侮辱。为了向任安说清自己为了活下来,所受耻辱之深之重之极,他在信中由高而低罗列了十个等级的人在世间所能遭遇的耻辱:“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这十个等级的耻辱,绝大部分都因获罪入狱而让他遭遇到了。而宫刑这一极端伤害人的肉体、摧残人的人格尊严的酷刑,在他看来,是远远超过了死刑(“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是死刑受辱)对人的侮辱。接受宫刑这一奇耻大辱,对他来说等于生不如死,故他在信中反复向任安说到:“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慨之士乎!”“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
既然生不如死,活着是如此的痛苦,为什么要活着?他在信中向任安详细申明,自己并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一则自己在朝廷上力排众议,为李陵辩诬,是基于道义,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二则自己也不须顾恋亲人家眷;三是自己身为士子,深明士节操守。故司马迁在信中说:“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
不怕死却没有能做到有尊严地死去,而是选择了承受人世间最深重的耻辱,痛苦地活下来,为什么?司马迁向任安说,这只是因为《史记》正“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所以才“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并说《史记》一旦成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三、不是不愿援救朋友,而是无法援救
任安是司马迁青年时代的好友。以司马迁的人格品德,对任安蒙冤入狱获死罪的遭遇不会无动于衷,当老友在濒死之际,带着求生的渴望向他求助,请求司马迁借助自己官职的便利,在汉武帝面前为自己明冤辩屈,司马迁更不可能因顾及自己的利害得失而袖手旁观。但他此时却无法也无力救助朋友。为了向任安说清内心的苦衷,他在《报任安书》的开头先陈述了自己受宫刑后在社会和朝廷上的处境:自古以来,人们就鄙视宦竖阉人,以和其共事相处为耻。自己受宫刑后虽在朝中做太史令,但已是身同宦竖,为朝臣和世人所不齿。如果自己在朝廷上还以朝官自居,论列朝政是非(为任安辩冤),反而会适得其反。用信中的话说就是“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和“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为了不使任安产生误解,司马迁接下去又向任安细述了自己当初为李陵辩诬而获罪的过程,意在表明自己和李陵只是同朝为官,并无私交,(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但却激于道义,在百官皆诬其降敌叛国的情形下,为其在汉武帝面前力辩其有忠于朝廷、献身国难的高尚品格和抗敌卫国的大功,以期援救李陵及其家人于灭族的大难中。对素无私交的李陵尚能如此,那么对老友落难临危,怎会不想出手相救?(这一部分的文字竟占了全信近半的篇幅,高中《语文》全部删去了。)
司马迁向任安细述自己为李陵辩诬而获死罪,因无家财救赎,只有自乞宫刑这一条活路的经历,还意在说明,自己现在即使如任安所请,去汉武帝面前为他明冤辩屈,不但无助于使任安死里逃生,还会让自己重蹈李陵事件的覆辙:再一次因触怒汉武帝而获死罪入狱。但司马迁这一次再获死罪,如果为完成《史记》而再一次想苟活求生,却也万般不能做到了——他还能自乞宫刑吗?如果做不到,《史记》也就功败垂成了。
四、披肝沥胆,赤诚相见,以求朋友死前无怨
如果明知道去汉武帝那里为任安仗义直言,其结果是既不能救任安于死地,又要搭上自己一同送死,那么这样做对司马迁来说,意义只有一个:救不了朋友,只有激于道义或出于友情,陪朋友一同赴死。司马迁自己固然可以为了担当道义、成全友情而陪朋友一同死,但《史记》能为司马迁的道义、友情随任安一同毁灭吗?当然不能。不能的理由有二:其一,完成《史记》的著述,就能使天下史文上继三代、下续《春秋》,得以延绵不断,就能使史官文化承载的精神和价值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以《史记》在文化传承上所起的作用而论,《史记》的价值远超过司马迁的性命,当然也远超过任安的性命。其二,《史记》承载着司马迁的精神生命,完成《史记》,就能使司马迁的人生获得超越性——超越肉体生命的存在、也超越个体生命的存在,从而使司马迁走进历史,名垂千古,获得生命的不朽,而这正是司马迁所认定的人生的意义和终极价值。故从对人生终极意义、生命的超越性价值的追求这一目标来说,司马迁的精神生命重于他的肉体生命,当然也重于任安的肉体生命。
既无法援救朋友,又因《史记》尚未定稿成书的缘故,不能陪朋友一同赴死,司马迁只能回绝任安的请求。但对司马迁来说,要做回绝,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表达上,又绝非轻易之事——这不是回绝朋友日常交往中的寻常求助,而是要回绝深陷灭顶之灾中的朋友,在濒死之际带着求生的渴望,向自己发出的求救呼声——在这封回信中,他必须要做到能让任安明白自己的处境、遭遇,深入自己的心灵深处,明了自己的情感和人生追求,从而使任安认同自己的人生选择,虽遭拒绝而无怨无恨(即如信中所言,不使“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
为了达到上述的写作目的,司马迁在信中向任安披肝沥胆,展示了自己那个常人难以理解的心灵。故他先从自己受宫刑后在耻辱中苟活写起,接着详述自己几年前因为李陵仗义直言入狱获死罪,那时本应该为免遭凌辱和守士节而主动去死,但却选择了耻辱而苟活,他承受的耻辱有多重?他说为活下来自乞宫刑是接受了人世间最极端的屈辱,失去了人格,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这种耻辱比死还可怕千万倍、痛苦千万倍。他讲自己并不贪生怕死,之“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为了完成《史记》。他向任安述说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史记》的创作情况,婉转含蓄地向任安表明:《史记》的价值远远超过他和任安生命的价值,《史记》的成废重于他和任安的生死,他是为《史记》活着,他的生命是属于《史记》的。他甚至暗示任安,一旦《史记》最后成书,也就是偿自己“死债”的时候了:“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向任安披肝沥胆、悲切泣血的灵魂独白,向任安、也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深远博大,有着“重于泰山”般崇高价值的心灵。当这个不朽的心灵,带着坚不可摧的生命尊严,穿越了两千年的时空,依旧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努力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时候,我们自然可以相信:两千年前,任安在狱中读到此信时也会因之而感动,更会因之平静地面对自己的生死。
[作者通联:河北唐山师院玉田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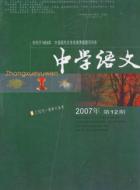
- 重读叶圣陶 / 顾黄初
- 愤悱启发:“达到不需要教”的基本规律 / 董菊初
- 科学精神 人文情怀 / 邹贤敏
- 一堂好课的两个发展性含义 / 张一山
- 语文知识系统的重构与阐释 / 王乃森 屠锦红
- 两个先于语文课程的语文谢水泉 / 谢水泉
- 文本语言,拨动生命乐章的琴弦 / 毕泗建
- 综合性学习活动:边界与准则 / 乐中保
- 浅谈视野融合对阅读教学的启示 / 张朝昌
- “文本多元解读”的解读 / 李儒大
- 文学作品意义的课堂解读 / 王 飞
- 林语堂的作文观 / 吴永福
- 材料作文写作内容四病 / 高凤君
- 一幅铺展于大自然的美丽巨画 / 周红阳
- 《鸿门宴》中项羽形象新解 / 张小忠
- 谁是主角 / 张 瑛
- 在史官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报任安书》的写作目的 / 张福旺 王桂霞
- 《皇帝的新装》教学案例与反思 / 胡明道
- 语文课堂资源生成例谈 / 郁 萍
- 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文化判断力形成方略初探 / 覃春来
- 新课程“名著导读”环节的教学背景及其对策 / 赵文汉
- “诗眼”特征透视 / 周加银
- 从“吊”(弔)字窥探中国上古的丧葬习俗 / 汤广文
- 释义辨证二则 / 王垂基
- 文化经典阅读答题失误及备考方略 / 程必荣
- 思维有路,理解有方 / 谭未为 谭德华
- 东海惠风 / 陈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