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12期
ID: 356333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12期
ID: 356333
语文知识系统的重构与阐释
◇ 王乃森 屠锦红
以“八字宪法”(即所谓的“字”、“词”、“句”、“篇”、“语”、“修”、“逻”、“文”)为主体的既有语文课程知识系统,它不能体现语文课程的自身特性,不能顺应语文教育的应有规律,对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也无法自给自足——狭隘的理性主义知识观、传统封闭的课程理念、过激的工具价值主义,是其不可逾越的三重障碍。新课程改革以来,语文课程知识系统的重构一直是语文教育界探讨的热点。某种意义上讲,这一问题构成了语文新课程改革继续深入推进的瓶颈所在。本文不揣浅陋,就这一问题摭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在哲学范畴里,“系统”它是指由许多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具有整体性、结构性、相对稳定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等特征。结构是任何一个系统的外显方式,它使得系统得以客观表征,因此,从外在来看,系统的建构实质上即为一种结构的设置。系统结构的设置总是以某种内在的关联为基本要求的,这种内在的关联是这一结构中各要素之间结合在一起的依据。从结构的外围来看,在逻辑学里,这种“依据”便是给要素划分类别的标准,所谓划分标准,即把母项分为若干子项的依据。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系统的具体建构首要的是确立给这一系统结构中诸要素分类的标准。这里重构语文课程知识系统,同样首先要做的工作便是要确立划分语文课程知识要素的标准。
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无疑是逻辑学中的经典分法,它有着哲学意义上的学理支撑,即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事物的一个基本特性。对于作为母语教育的语文课程而言,语文形式教育与语文内容教育的统一,是其基本特性。从课程论的视角来看,语文形式教育与语文内容教育的统一,则是语文课程目标的基本特性。课程知识受制于课程目标,课程目标呼唤着课程知识,达成语文课程目标的这种特性也就从根本上规定了语文课程知识的选择。因此,从逻辑上讲,语文课程知识系统中必然存在着与语文课程目标相对应的两种基本形态的知识,在此,我们分别用“语文形式”类知识与“语文内容”类知识来对其指称。
逻辑性是分类的内在依据,客观性是分类的外在要求。根据语文课程的实际情形,遵循一定的逻辑思路,我们对“语文形式”类知识与“语文内容”类知识各自再进一步作了细致划分,从而使得确立于抽象逻辑意义上的这两块知识得到了具体呈现,经过这样的二级划分,一个崭新的语文课程知识系统诞生了:
语文课程知识:语言形式(规则类语科类)
语文内容(事实类情意类)
如图所示,“语文形式”类知识有两个亚类,即规则类与语料类。和“语文内容”类知识相比,这两类知识主要不关涉语言内容,它们都是作为语言运用的“形式工具”(前者为抽象的理论,后者为具体的用件)而存在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这两块知识看作是语文课程“形式”范畴里的知识。“语文内容”类知识它也有两个亚类,即事实类与情意类。和“语文形式”类的两块知识相比,这两块知识所体现的全是语言内容方面的知识,它们都是作为语言运用的“内容实质”(事实类是客观的,观点类与情感类是主观的)而存在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这两块知识都看作是语文课程“内容”范畴里的知识。下面对“语文形式”类知识与“语文内容”类知识进行一一阐述。
一、关于“语文形式”类知识
1.规则类知识
这一块知识反映的是语文课程的理性的规律法则性的知识,它主要是由各相关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知识组成,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关于语言方面的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文字学等学科的知识;二是关于语言运用方面的修辞学、逻辑学、语用学、口语交际学等学科的知识;三是关于语言作品方面的文章学、文艺学等学科的知识。这三方面知识遵循着“精要、好懂、有用”的原则进入语文课程。具体到语文课程中,这些知识主要表现在:
(1)语音知识,(2)文字知识,(3)词语知识,(4)语法知识,(5)修辞知识,(6)逻辑知识,(7)文章知识,(8)文学知识,(9)文言文知识,(10)标点符号知识,(11)工具书的使用知识,(12)阅读知识,(13)写作知识,(14)口语交际的知识,(14)语文学习方法、策略的知识。
2.语料类知识
在语文课程里,这块知识反映的是关于语言运用所需的基本的语言元素、部件方面的知识,它们作为表情达意的基本的材料工具而存在着。主要包括:
(1)声母表;(2)韵母表;(3)声调符号;(4)标点符号;(5)常用字;(6)常用词;(7)常用短语(包括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8)古今名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常用短语”、“古今名句”虽然本身也可能会承载一定的事实或情意,但从使用者的角度而言,“常用短语”、“古今名句”它们常常是在一种较为宽宏的背景下使用的,是依附于特定的语境里而被引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本身的“内容”也只能看作是“形式的内容”。和一般的字、词一样,它们实际上也是作为某种材料工具而存在着的。
二、关于“语文内容”类知识
1.事实类知识
在语文课程里,这块知识反映的是相关自然、社会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的文化常识,它是作为客观的事实性知识而存在的。如:
①“岁寒三友”:松、竹、梅。
②封建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
③伯(孟)仲叔季: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序,伯(孟)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最年幼的。
④阳文阴文:我国古代刻在器物上的文字,笔画凸起的叫阳文,凹下的叫阴文。
2.情意类知识
在语文课程里,这块知识反映的是相关个体对自然、社会、人生等进行反思与体验而产生的种种情思态度方面的知识。当然,这种反思与体验并非学术意义上的追问与探讨,而是旨在个体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某种省察与重构。这块知识在语文课程里相当丰富。如:
①幸福并不与财富、地位、声望、婚姻同步,它只是一种心灵的感觉。(毕淑敏:《提醒幸福》)
②俭朴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品行问题,勤俭可以涵养美德。(马铁丁:《俭以养德》)
③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
④爱情宣言: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舒婷:《致橡树》)
最后对这一知识系统作几点说明:
第一,这一知识系统建构的逻辑理路或者说理论依据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范畴里“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一基本命题,其二是现代认知心理学广义的知识观。“语文形式”类知识与“语文内容”类知识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知识系统的基本特性,以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知识观来看,“语文内容”类知识所包含的三块知识全部属于陈述性知识,“语文形式”类知识的两块知识中,其中语料类知识属于陈述性知识,规则类知识中则既包括陈述性知识,也包括程序性知识及策略性知识。
第二,重构语文课程知识系统只是一种手段,其深层动因或者说根本目的在于,把应然状态下的所有语文课程知识类别放在一个系统中加以观照,在课程层面上确认它们的合法性,并希望能促使某些类别语文课程知识的教学由自发状态转变为自觉状态,从而实现语文课程知识教学能“从单一的静态的社会语言规律,向多重的动态的社会言语规律延伸;从读解一篇范文,向从范文中提取有益的言语经验升华;从一般的语言学习,向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深化;从一个个孤立的文篇,向大文化观念扩充。”
以“八字宪法”(即所谓的“字”、“词”、“句”、“篇”、“语”、“修”、“逻”、“文”)为主体的既有语文课程知识系统,它不能体现语文课程的自身特性,不能顺应语文教育的应有规律,对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也无法自给自足——狭隘的理性主义知识观、传统封闭的课程理念、过激的工具价值主义,是其不可逾越的三重障碍。新课程改革以来,语文课程知识系统的重构一直是语文教育界探讨的热点。某种意义上讲,这一问题构成了语文新课程改革继续深入推进的瓶颈所在。本文不揣浅陋,就这一问题摭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在哲学范畴里,“系统”它是指由许多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具有整体性、结构性、相对稳定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等特征。结构是任何一个系统的外显方式,它使得系统得以客观表征,因此,从外在来看,系统的建构实质上即为一种结构的设置。系统结构的设置总是以某种内在的关联为基本要求的,这种内在的关联是这一结构中各要素之间结合在一起的依据。从结构的外围来看,在逻辑学里,这种“依据”便是给要素划分类别的标准,所谓划分标准,即把母项分为若干子项的依据。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系统的具体建构首要的是确立给这一系统结构中诸要素分类的标准。这里重构语文课程知识系统,同样首先要做的工作便是要确立划分语文课程知识要素的标准。
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无疑是逻辑学中的经典分法,它有着哲学意义上的学理支撑,即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事物的一个基本特性。对于作为母语教育的语文课程而言,语文形式教育与语文内容教育的统一,是其基本特性。从课程论的视角来看,语文形式教育与语文内容教育的统一,则是语文课程目标的基本特性。课程知识受制于课程目标,课程目标呼唤着课程知识,达成语文课程目标的这种特性也就从根本上规定了语文课程知识的选择。因此,从逻辑上讲,语文课程知识系统中必然存在着与语文课程目标相对应的两种基本形态的知识,在此,我们分别用“语文形式”类知识与“语文内容”类知识来对其指称。
逻辑性是分类的内在依据,客观性是分类的外在要求。根据语文课程的实际情形,遵循一定的逻辑思路,我们对“语文形式”类知识与“语文内容”类知识各自再进一步作了细致划分,从而使得确立于抽象逻辑意义上的这两块知识得到了具体呈现,经过这样的二级划分,一个崭新的语文课程知识系统诞生了:
语文课程知识:语言形式(规则类语科类)
语文内容(事实类情意类)
如图所示,“语文形式”类知识有两个亚类,即规则类与语料类。和“语文内容”类知识相比,这两类知识主要不关涉语言内容,它们都是作为语言运用的“形式工具”(前者为抽象的理论,后者为具体的用件)而存在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这两块知识看作是语文课程“形式”范畴里的知识。“语文内容”类知识它也有两个亚类,即事实类与情意类。和“语文形式”类的两块知识相比,这两块知识所体现的全是语言内容方面的知识,它们都是作为语言运用的“内容实质”(事实类是客观的,观点类与情感类是主观的)而存在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这两块知识都看作是语文课程“内容”范畴里的知识。下面对“语文形式”类知识与“语文内容”类知识进行一一阐述。
一、关于“语文形式”类知识
1.规则类知识
这一块知识反映的是语文课程的理性的规律法则性的知识,它主要是由各相关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知识组成,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关于语言方面的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文字学等学科的知识;二是关于语言运用方面的修辞学、逻辑学、语用学、口语交际学等学科的知识;三是关于语言作品方面的文章学、文艺学等学科的知识。这三方面知识遵循着“精要、好懂、有用”的原则进入语文课程。具体到语文课程中,这些知识主要表现在:
(1)语音知识,(2)文字知识,(3)词语知识,(4)语法知识,(5)修辞知识,(6)逻辑知识,(7)文章知识,(8)文学知识,(9)文言文知识,(10)标点符号知识,(11)工具书的使用知识,(12)阅读知识,(13)写作知识,(14)口语交际的知识,(14)语文学习方法、策略的知识。
2.语料类知识
在语文课程里,这块知识反映的是关于语言运用所需的基本的语言元素、部件方面的知识,它们作为表情达意的基本的材料工具而存在着。主要包括:
(1)声母表;(2)韵母表;(3)声调符号;(4)标点符号;(5)常用字;(6)常用词;(7)常用短语(包括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8)古今名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常用短语”、“古今名句”虽然本身也可能会承载一定的事实或情意,但从使用者的角度而言,“常用短语”、“古今名句”它们常常是在一种较为宽宏的背景下使用的,是依附于特定的语境里而被引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本身的“内容”也只能看作是“形式的内容”。和一般的字、词一样,它们实际上也是作为某种材料工具而存在着的。
二、关于“语文内容”类知识
1.事实类知识
在语文课程里,这块知识反映的是相关自然、社会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的文化常识,它是作为客观的事实性知识而存在的。如:
①“岁寒三友”:松、竹、梅。
②封建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
③伯(孟)仲叔季: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序,伯(孟)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最年幼的。
④阳文阴文:我国古代刻在器物上的文字,笔画凸起的叫阳文,凹下的叫阴文。
2.情意类知识
在语文课程里,这块知识反映的是相关个体对自然、社会、人生等进行反思与体验而产生的种种情思态度方面的知识。当然,这种反思与体验并非学术意义上的追问与探讨,而是旨在个体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某种省察与重构。这块知识在语文课程里相当丰富。如:
①幸福并不与财富、地位、声望、婚姻同步,它只是一种心灵的感觉。(毕淑敏:《提醒幸福》)
②俭朴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品行问题,勤俭可以涵养美德。(马铁丁:《俭以养德》)
③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
④爱情宣言: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舒婷:《致橡树》)
最后对这一知识系统作几点说明:
第一,这一知识系统建构的逻辑理路或者说理论依据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范畴里“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一基本命题,其二是现代认知心理学广义的知识观。“语文形式”类知识与“语文内容”类知识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知识系统的基本特性,以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知识观来看,“语文内容”类知识所包含的三块知识全部属于陈述性知识,“语文形式”类知识的两块知识中,其中语料类知识属于陈述性知识,规则类知识中则既包括陈述性知识,也包括程序性知识及策略性知识。
第二,重构语文课程知识系统只是一种手段,其深层动因或者说根本目的在于,把应然状态下的所有语文课程知识类别放在一个系统中加以观照,在课程层面上确认它们的合法性,并希望能促使某些类别语文课程知识的教学由自发状态转变为自觉状态,从而实现语文课程知识教学能“从单一的静态的社会语言规律,向多重的动态的社会言语规律延伸;从读解一篇范文,向从范文中提取有益的言语经验升华;从一般的语言学习,向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深化;从一个个孤立的文篇,向大文化观念扩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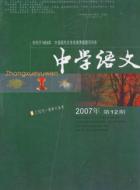
- 重读叶圣陶 / 顾黄初
- 愤悱启发:“达到不需要教”的基本规律 / 董菊初
- 科学精神 人文情怀 / 邹贤敏
- 一堂好课的两个发展性含义 / 张一山
- 语文知识系统的重构与阐释 / 王乃森 屠锦红
- 两个先于语文课程的语文谢水泉 / 谢水泉
- 文本语言,拨动生命乐章的琴弦 / 毕泗建
- 综合性学习活动:边界与准则 / 乐中保
- 浅谈视野融合对阅读教学的启示 / 张朝昌
- “文本多元解读”的解读 / 李儒大
- 文学作品意义的课堂解读 / 王 飞
- 林语堂的作文观 / 吴永福
- 材料作文写作内容四病 / 高凤君
- 一幅铺展于大自然的美丽巨画 / 周红阳
- 《鸿门宴》中项羽形象新解 / 张小忠
- 谁是主角 / 张 瑛
- 在史官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报任安书》的写作目的 / 张福旺 王桂霞
- 《皇帝的新装》教学案例与反思 / 胡明道
- 语文课堂资源生成例谈 / 郁 萍
- 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文化判断力形成方略初探 / 覃春来
- 新课程“名著导读”环节的教学背景及其对策 / 赵文汉
- “诗眼”特征透视 / 周加银
- 从“吊”(弔)字窥探中国上古的丧葬习俗 / 汤广文
- 释义辨证二则 / 王垂基
- 文化经典阅读答题失误及备考方略 / 程必荣
- 思维有路,理解有方 / 谭未为 谭德华
- 东海惠风 / 陈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