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12期
ID: 136406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12期
ID: 136406
审视与反思:“语用问题”的特异个案
◇ 潘 涌 王奕颖
近期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的韩寒,已经成为无法回避、也无需回避的语文教育话题。影响力是一种综合和中性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由主体不自觉地借助时代推力而幸运获至。不过,《时代》周刊给我们提供一种契机来重新审读和透视韩寒,借以反思并展望我们的语文教育。
当代中国,“语用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个社会公共问题。简言之,“语用问题”是指语文教育的庸俗化而导致青少年学生语用品质的低劣化。前者具体表现为语文教育应试倾向与政治本位倾向的泛化,后者则暴露在青少年已经习以为常、深入骨髓的伪劣语用行为上,特别是校园“课堂语用”与日常“生活语用”的严重悖离上。“语文人物”是“语用问题”的派生概念,在本语境中是指面对庸俗化的语文教育秉持己见、守护理想甚至不惜与其断然决裂的特异个案。韩寒就是这种“语文人物”的代表。一方面,他个性化、真实化的言语表达遭到庸俗化语文教育的排斥和压制;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冲破这种庸俗化倾向,竭力保持独立、真实、个性的表达。而韩寒作为这种符号性语文人物,为我们提供了省思语文教育的鲜活样本。韩寒曾经的曲折命运,集中反映了应试教育的弊端、素质教育的盲点,当然还有他自身的语用品质问题等。同时,韩寒在文化市场和网络世界上的暂时成功也昭示了语文教育的某些应然取向。这就是韩寒作为一个语文人物提供给我们的特殊价值。
一、韩寒的背景:中西文化的交汇
韩寒成长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汇中。九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地方化与全球化结伴而行,文化的同一性受到文化多样性坚持不退的挑战。”①韩寒的脱颖而出,得益于偶然的契机,也包含了一些时代造就的必然因素。
契机一:开放的“新概念”作文赛给韩寒提供了一夜成名的时机。“新概念”作文之前,韩寒是一名背负着学业沉重挫折感的普通高中生。韩父是某杂志的编辑,为童年的韩寒创设了宽松自由的阅读环境。韩寒的文字功底在其父不懈的教诲中日渐扎实,其尖锐、独立的批判性思维同时也在对中外名著的自由涉猎中逐渐养成。然而,韩寒锋芒毕露的个性化表达并没有受到所在学校语文教育的青睐,而是屡屡遭受排斥和压制。他曾多次参加学校的写作比赛——成绩之差,令人发指。与此同时,他的语文考试成绩也只勉强在及格线徘徊,其它成绩更是惨不忍睹。在这种困厄的境遇中,是“新概念”作文让韩寒的命运发生了转折性的突变。相对于传统的作文比赛来说,“新概念”作文极大地放宽了学生写作的自主尺度,宽容地对待早恋、逃学、颓废、贪污等主流之外的另类题材,不急于在单纯的歌功颂德中进行思想的“规正”。1998年,韩寒以一篇活力迸溅的《杯中窥人》来“窥视”社会对人性的浸染,幸获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在媒体的炒作中,韩寒这位文笔老练却学业告危的“另类少年”开始走入公众的视域。之后,社会及各家媒体将韩寒放大为一种具有反思价值的教育现象,由此引发了“学校应当培养全才还是专才”等问题的热烈讨论。而现实生活中的韩寒却面临着留级的煎熬。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韩寒决定选择与主流学校教育诀别,摆在他面前的是不可预知的体制外的精神流浪。而同时期成名的其他80后少年作家,则一边涂抹着忧郁、自恋、早熟、叛逆的文字,一边无奈地为高考日夜兼程地苦苦撑持。韩寒从正统教育体制中出走,一方面源于反抗庸俗化语文教育对生命本真的表达欲的深度禁锢;一方面源于受多元的外来文化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浪潮凸起,麦当劳、NBA、美国电影,特别是互联网承载的西方消费观念、自由主义、民主意识和拜金主义,不断消融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成长于中西文化交汇中的80后一代无所适从,一度被媒体谴责为“垮掉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学名词,本身就来源于美国的文学流派,其代表作家是二战后一群桀骜不驯、追求自由、目无法纪、反对一切成规陋习的青年男女。韩寒正是传统语文教育的叛逆者,被主流媒体归入“垮掉的一代”。
契机二:互联网提供韩寒跃为名博主并被世界主流媒体认可的机会。辍学后,韩寒一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陆续发表了《像少年啦飞驰》、《长安乱》、《光荣日》、《通稿2003》等作品,构建着理想中的教育体制;一面成为众人眼中“不务正业”的赛车手,在或谴责或惋惜声中“就这样漂来漂去”。此时,互联网改写了文化媒介的历史,成为了文化交流的最主要载体。网民作为新新人类的身份在虚拟开放的无限空间中不断创生着新的文化景观。2006年,韩寒也开始新浪博客写作,以自由任性的文笔对一些撞击眼帘的现实话题发表评论,并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生诸多方面的热点一一纳入他新锐的视野。此后,他的博文赶超“博冠”徐静蕾,升为国内点击率第一。2010年5月初,韩寒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其评价如下:Han Han's first novel, based on his experience as a high school dropout in Shanghai, became a best seller in China and sparked a debate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country's rigid education system. An avid rally car driver, he writes a mega-popular blog that pokes fun at prominent cultural figures and incompetent officials.(韩寒的第一本小说,基于他在上海读中学辍学的经历。如今,韩寒已经是中国畅销书作家,并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僵化的教育体制的争论。他不仅是一个狂热的赛车手,还写着超级流行的博客,借以批评文化名人和不称职的行政官员。)对此现象,有论者认为,《时代》此举是基于文化后殖民的险恶用心,韩寒的所谓真实、开放、愤世嫉俗,正好迎合了西方的价值观。也有论者认为,美国人无法理解韩寒的“中国价值”,因为“如果韩寒出生在美国,他说不定也是千千万万不满青年中的一个,没有工作,家庭破碎,教育低下”②。还有论者认为,韩寒充当了“文化公厕”的职责,让民众借以泄私“粪”。但我们应该看到,不管是“公民”、“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的韩寒,还是入选《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的韩寒,80后作家已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开放背景下蜕茧长大为拥有独特话语的个体。
二、韩寒:反抗庸俗化的语文教育
韩寒作为值得我们深度反思的语文人物,集中反映了庸俗化语文教育的种种弊端及其对基于生命本位的个性表达的压制。而韩寒曲折的精神成长,实质上就是他对庸俗化语文教育抗争与决裂的艰难过程。其中不乏值得深入省思之处。
(一)反抗语文教育应试化倾向
中国作协原副主席王蒙对韩寒曾有这样一段评价:“你就是一个差生。烂泥扶不上墙,最终辍学,你是个教育的残次品,还充当起精神领袖。”③王蒙的话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的主流教育体制对韩寒的评价。提取“教育”、“辍学”、“差生”、“精神”几个关键词,我们不难发现,“学校教育”仅以“考试分数”衡量学生的语文素养,作为划分“好生”与“差生”的标准。概而言之,传统语文教育存在极端的应试化倾向,甚至连不便条分缕析的“人文精神”也要以一纸考卷来细细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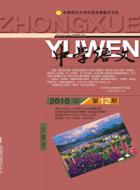
- 曾祥芹语文教育思想浅论 / 邱福明 曹明海
- 闻荒立拓乐为先 / 李杏保
- 曾祥芹教授语文教育理论探索之路 / 曹洪彪
- 作文教学必须回答的三个问题 / 代保民 丁雪梅
- 碎片与灵魂 / 苑青松
- 治学和做人是二而一的事 / 韩雪屏
- 探究《雷雨》(节选)的解读视角 / 郑莉萍
- 审视与反思:“语用问题”的特异个案 / 潘 涌 王奕颖
- 悲凉人生中的缕缕温情 / 徐昌才
- 让学生尽享成功的喜悦 / 李启明
- 语文新课改:并不等于拒绝教学返真归本 / 顾 勇 董旭午
- “冰山原则”下的《桥边的老人》 / 史绍典
- 红领:一个中西合璧的新词 / 刘昭琪
- 语文教材编制的审视与反思 / 孙慧玲
- 汉字教学方法摭谈 / 裴正菊 杨字玲
- “杯具”之“杯” / 刘 莉
- 高中生阅读理解能力发展研究概述 / 戴方文
- 从“奔奔族”说起 / 苏永慧
- 湖海江山作课堂 / 宁冠群
- 论深度阐释 / 王 飞
- “给力”正流行 / 肖皿舟
- 魏晋清谈与语言能力训练 / 黄妮妮
- 文本解读的“相对论” / 崔国明
- 撰写另一种学案 / 何明锋
- 快餐式语文教学PK烹饪式语文教学 / 陈颂善
- 《夏天的旋律》的语言教学尝试 / 张 颖
- 惯用语的离合 / 穆亚伟
- 谈语文教学中的诗词教学 / 韩世姣
- 香港中学语文听说课程设计管窥 / 杜少凡
- 高考作文的四大病灶 / 何 郁
- 200海内外学者参加的“曾祥芹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圆满成功 / 张正君 耿红卫 米格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