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12期
ID: 136399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12期
ID: 136399
曾祥芹语文教育思想浅论
◇ 邱福明 曹明海
语文教育在基础教育中具有奠基性作用,语文教育研究源远流长,伴随着语文教育风雨兼程。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曾祥芹,长期以来致力于语文教育、文章学、阅读学研究,提出了语文“一语双文”的结构体系论,运用文章学和阅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提高语文教学效率,在国内外语文教育界引起广泛的关注,推动了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这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研读曾祥芹教授的语文教育思想,一直萦绕在心头的迷惑渐渐清晰起来。他是一位富有学术力度的学者,以理性的审视和全面的通透游走在语文教育的历史与现实间,在极富生命理思与情感的言说中,窥见了语文教育研究的魅力,打通了一条通往语文殿堂的逐渐明朗的语文教育研究之路。
一、鲜明的“三足鼎立”:建构语文学体系
对语文学科性质的争论一直以来是语文界的热点和难点。语文研究可能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无私奉献才能完成,否则语文建设这个工程就很难实现。中国语文教育自1904年独立设科以来,围绕课程性质、目的、任务等问题展开的争论,延续了百年之久。要想说清楚语文学科到底是什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一种有代表性的课程定义都有一定的指向性,即都是指向当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课程所出现的问题,所以都有某种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着某种局限性。而且,每一种课程定义都隐含着作者的一些哲学假设和价值取向。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选择这种或那种课程定义,而是要意识到各种课程定义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伴随的新问题,以便根据课程实践的要求,作出明智的选择”。①曾教授敢于直面语文的难点问题,从自身对语文的独特理解出发,做出了关于语文学体系的选择与建构。即由他的语文内涵“一语双文”、语文理论“三大支柱”和语文课程“三足鼎立”构成的语文学体系。
1.语言、文章、文学合成“一语双文”。他综合分析和反思了语文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及“语言文化”说,认为这些关于语文的学说都有其历史贡献又都存在一些偏颇。于是提出了更为圆通的“一语(语言)双文(文章、文学)”说。一方面,承认了“语”和“文”的区别,将口语和书面语分开;另一方面,弄清了“文字”、“文章”、“文学”、“文化”四个义项的涵盖面和彼此之间的相容性、相斥性,特别是将文章和文学相对分开。曾教授“一语双文”的理念,是在充分批判和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拓宽语文内涵的一大突破和推进,深化了对语文的认识和研究,必将推动语文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2.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三大支柱”。如果把语文学科内容分为语言、文章、文学三大部分,那么自然就需要以语言、文章、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三门学问——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曾教授倡导让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构建成语文学的理论基础,以此扩充长期以来相对狭窄的语文学科内涵。他把文章学定位为与语言学、文艺学并峙的独立学科,语言学和文艺学之间的“桥梁”学科,发展语言学和文艺学的“动力”学科,可与语言学,文艺学争雄的主干学科。将长期以来语文中对“文章”的忽视填补进来,力图实现“文章”在语文中的复归,充分彰显了文章学的独立性、桥梁性、动力性和学术性,确认了其在语文课程体系中的主干地位。从而建立了以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构成的语文理论三大支柱。
3.语言课、文章课、文学课“三足鼎立”。语文到底该教什么?我想这是困扰很多语文工作者的世纪难题。吕叔湘早就说过“学校里的语文教学应该以语言为主呢,还是以文字为主?应该语言和文字并举,以语言为门径,以文字为重点,达到语言和文字都提高的目的。”②可见吕老看重语言文字这一义。尽管在今天看来,我们未必都认同吕老的观点,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语文到底该教什么”这一问题的意蕴所在。新的语文课程改革背景下,尤其是新理念、新术语泛滥的今天,不少语文教师都不知道语文该怎么教了。曾教授非常注重对语文教学内容的研究,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了语言、文章、文学三足鼎立的语文学科内容结构观,这不仅体现了他对语文教学内容的独特构建,更体现了他超前的学术意识。
语言、文章、文学合成的“一语双文”,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组成的“三大支柱”和语言课、文章课、文学课构成的“三足鼎立”建筑了完备的语文学体系,超越了传统语文学的狭小天地。以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为研究对象,既涉及了语言工具,又涉及到言语作品;既包容了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学,又包容了语言文章和语言文化。这一语文学体系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为目标,既把握了语文形式,又注重研究语文内容;既注重了语文的工具性,又关照到了语文的人文性;既揭示了语文知识和技能的本体规律,又探讨了学习者学用语文的主体素养和环境优化。他在20世纪末叶构建形成的语文学体系所体现的语文教育理念与21世纪初叶的语文课程改革理念不谋而合,可见其学术的前瞻性。
二、交响乐的重要声部:彰显文章学效能
曾祥芹教授对文章学情有独钟,对文章不仅有深入的研究,更有深厚的痴情。他向我们诠释了文章学的内在意蕴与独特魅力,将文章学与语文教育的有机结合作为语文教育发展必经的一步。一方面,立足国内,回溯历史,从几千年语文教育的历史发展娓娓道来,向我们展现了文章学与语文教育的天然血缘关系。古代文章教育源远流长,近代文章教育新潮澎湃,现代文章教育波浪起伏。在他看来,几千年来的历史中,文章教学一直成为语文教育的中心内容,历代的文章大家又都是语文教育家,文章的原理和技术同时也是语文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因此,他突出强调了文章学与语文教育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放眼世界,考察了美、英、德、法、俄等国家语文学及语文教育界的研究和实践状况,认为国外文章理论研究还未形成独立的概念体系,国外母语教育具有从“语义训释到文艺主义再到实用文章”的演变轨迹。
语文教学科学化的追求是语文教育发展史上一条永恒的主线。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追求有成就,也有偏颇。曾祥芹教授基于对文章学的研究与挚爱,把开展文章学的研究作为语文教学科学化的路径来开进。他归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学走过的弯路和出现的偏向,即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文学课或语言课。曾教授认为这些偏向,究其根源,是忽略了文章的本质,没抓住语文教学的主要矛盾,因而不能明确语文课的性质、目的和任务。而从教学目的任务看,语文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读文章和写文章的能力;从教学内容看,语文教材实际是优秀文章的集锦。因此,如果能抓住文章教学这个主要矛盾,语文教学的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在他看来,文章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文章本体及其写、读规律的一门学科。若语文教学主要是文章教学,那么决定语文课性质的特殊的主要矛盾,只有靠文章学的指导,才能正确解决。曾先生在几十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中摸索出了规律,那便是按文章规律办事,以文章读写为主线建立语文教学体系;以文章体裁为单元编排语文教学课本,以多练精练为途径改进语文教学方法。他的这些独到的见地,不禁让我们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关于国文读本的选材标准讨论以及编排。当时,周予同就提出了几条:一是凡违反人道或激起兽欲的文章,一概不录;二是凡卑鄙龌龊的应酬文章和干禄文章,一概不录;凡虚诞夸浮的纪传碑志及哀祭文章,一概不录……七是生存人的文章,主张入选。③当时对国文教材的选材标准,有种观点就是认为中学生将来并非个个是文学家、语言学家,所以主张国文教科书要加强“实用性”,应多收录应用文。由此看来,曾祥芹教授也是很看重文章对中学生的重要性的,认为语文课的文学教学不仅必须服务于文章教学,而且语文课的语言教学必须从属于文章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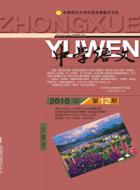
- 曾祥芹语文教育思想浅论 / 邱福明 曹明海
- 闻荒立拓乐为先 / 李杏保
- 曾祥芹教授语文教育理论探索之路 / 曹洪彪
- 作文教学必须回答的三个问题 / 代保民 丁雪梅
- 碎片与灵魂 / 苑青松
- 治学和做人是二而一的事 / 韩雪屏
- 探究《雷雨》(节选)的解读视角 / 郑莉萍
- 审视与反思:“语用问题”的特异个案 / 潘 涌 王奕颖
- 悲凉人生中的缕缕温情 / 徐昌才
- 让学生尽享成功的喜悦 / 李启明
- 语文新课改:并不等于拒绝教学返真归本 / 顾 勇 董旭午
- “冰山原则”下的《桥边的老人》 / 史绍典
- 红领:一个中西合璧的新词 / 刘昭琪
- 语文教材编制的审视与反思 / 孙慧玲
- 汉字教学方法摭谈 / 裴正菊 杨字玲
- “杯具”之“杯” / 刘 莉
- 高中生阅读理解能力发展研究概述 / 戴方文
- 从“奔奔族”说起 / 苏永慧
- 湖海江山作课堂 / 宁冠群
- 论深度阐释 / 王 飞
- “给力”正流行 / 肖皿舟
- 魏晋清谈与语言能力训练 / 黄妮妮
- 文本解读的“相对论” / 崔国明
- 撰写另一种学案 / 何明锋
- 快餐式语文教学PK烹饪式语文教学 / 陈颂善
- 《夏天的旋律》的语言教学尝试 / 张 颖
- 惯用语的离合 / 穆亚伟
- 谈语文教学中的诗词教学 / 韩世姣
- 香港中学语文听说课程设计管窥 / 杜少凡
- 高考作文的四大病灶 / 何 郁
- 200海内外学者参加的“曾祥芹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圆满成功 / 张正君 耿红卫 米格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