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2期
ID: 136147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2期
ID: 136147
新课程背景下文学教育的思考
◇ 李惠英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颁布施行,文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得以彰显,文学作品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加强文学教育”成为了语文界的共识。但面对教材中众多的优秀文学作品,教师如何进行教学,却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回顾过去乃至现在的文学教育,我觉得不少师生在解读文学作品时,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读文学作品时,用政治观点图解文学。面对一篇文学作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其置于“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下去观照,总是不自觉地用二元对立的思维去研究作品“歌颂了什么”、“揭露了什么”,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评判作品中人物的好坏。这样,我们就将充满生命底蕴和人生意趣的文学作品简单类化为一些标语和口号,不仅对文学本身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还使学生从根本上形成对文学的片面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认识,更使学生在这样的熏陶下变成一个政治人,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们的语言日益泛政治化。
二是解读文学作品时,用科学阉割了艺术。明人杨慎评论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时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 杨慎的评论成为千古笑谈。为何被讥笑?因为杨慎用科学思维阉割了文学思维,把生活真实混同于艺术真实,文学艺术丰富的想象力被他扫荡殆尽。杨慎式的评论在我们今天的语文课堂教学中有没有?笔者觉得不但有,而且很普遍地存在着。
那么文学教育应怎样改变这一现状呢?
首先教师要转变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文化心态的调整。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从“单元封闭的文化心态”向“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转换。如果我们完不成这一文化心态的转换,只用一种单一的阐释角度和价值标准去观照文学作品,或以自己的好恶作为评判的坐标,势必导致误读,做出有失公正的评价。作为教师来说,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尤其重要,因为一元化的思维定势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学生创造性的扼杀。下面试举几则原初、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课文提示略加申说。
《竞选州长》一文的“提示”说:“作者以夸张的漫画式的笔触,艺术地再现了美国社会中竞选的种种秽事丑闻,揭露了竞选的虚伪性、欺骗性,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竞选’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尖锐的批判。”
《守财奴》一文的“提示”说:“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这对我们深刻理解这篇课文的思想内容无疑会有很大的启发。葛朗台的妻子是作者赞扬的好人,作者认为笃信宗教才不至于陷入金钱的泥沼。课文中对葛妻隐忍贤德的描写,意在反衬葛朗台的凶狠丑恶。这虽然有一定的揭露作用,却也恰恰反映出作者世界观的局限。”
我们不必对这些提示作太多的评论,稍微有点独立思考能力、对世界现状有点了解的人都会发觉这套思维方式完全还是文革式的思维方式。以《守财奴》为例,作者所要表现的恐怕主要是人性的贪婪与愚昧。这是人性共有的弱点,不是某种社会制度专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有这样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里照样存在。《守财奴》的作者主要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而是批判人性的弱点,进而寻找对人性的疗救之道。作者最后找到了宗教,宗教能否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当然值得进一步探讨。但是,我们不应当对别人的选择指手画脚,不负责任地随口乱说。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不能否定别人的宗教信仰,自己怀疑宗教,但不能指责别人对宗教的真诚。否则就太专制了。
此类评价,在通行的教科书中比比皆是。如果我们不对此进行一番批判性反省,必将封闭我们的思路,使我们的思想粗糙化,思维教条化。
其次要接受新知,扩大视野,更新方法。知识更新,是跨世纪人才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在文学阅读和研究中,固守传统的批评方法固然可以做到“守正”,但难以“出新”,尤其在知识更新节奏加快、新的批评方法层出不穷的当今世界,它已日益显示出自己捉襟见肘的窘迫。所谓知识更新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扩大“支援意识”的过程。文学鉴赏中多一重“支援意识”,就会多一种观照问题的视角和方法。
如语文教材中的《我国古代文学》介绍“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时作了这样的点评:“李白的诗,嘲弄庸俗世态,反抗权贵,充满了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精神。他歌颂祖国壮丽的河山,歌颂自由生活,对于社会现象的不合理和自己才能的不得施展,表现出强烈的愤慨。杜甫生活饱经忧患,比较接近人民,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生活的痛苦……他的诗富于现实主义精神,发扬了《诗经》、《离骚》、乐府的优良传统,给后来的诗人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这个点评初一读,似乎无甚不妥,其实此类评论看多了,就会发现这些说法千篇一律。既没有评出作者性灵的深度、力度,也没有讲清诗人作品的艺术性、文学性。而此时我们如果多一重“支援意识”,就会多找到一种观照问题的视角和方法。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读过钱钟书的《谈艺录》关于唐宋诗的分析,你就会有耳目为之一新的欣喜感觉。钱先生说:诗分唐宋,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宋诗多以筋骨思想取胜。在人的一生中,少年时才气发扬,所以诗文近于唐体之风格;晚岁时思虑深沉,于是诗文又染上了宋调。个人如此,历史亦如此:古人写的诗真朴自然者居多,因为当时他们的情感、思想、心理不太复杂。类似于唐体,今人写的诗刻露见心思,又近乎宋调。从人的性格来说,外倾兴奋型的人,所写之诗文类似于唐体,内倾沉潜型的人所写之诗文同于宋调。李白性格外倾,诗乃奔放飘逸;杜甫性格内向,诗乃沉浑厚实。当然对于大诗人来说这种区别只是大概的,不可能一概而论,比如杜甫的诗兼备众妙,人人只要学到其一方面就足称名家,陈后山学到了他的细筋健骨、瘦硬通神;陆放翁学得了逸丽,但苍浑不足;其他人能放不能敛,学了杜甫单方面的一半……所以,杜甫诗远不是“现实主义”一词所能概括。
因此,对这些大诗人简单地贴上一个标签,方便是方便了,但这无助于我们对诗人的理解。
第三,要观照作品的文化层面,发掘作品的文化内涵。文化批评在文学阅读中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如中国古代戏曲的“大团圆”结局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融容和合”思想在叙事中的体现,也即这一思想在暗中统合支配着作者的叙事行为,并构成潜藏于叙事过程中的一种“文化文法”,引导故事向“大团圆”的结局发展。正如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的:“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理解了中国戏曲的这一特性,对理解中国文学作品的大团圆结局帮助大矣。
再如《红楼梦》中的晴雯,如果对她作一番文化层面的观照和文化内涵的发掘,就会有许多新的发现。在《红楼梦》研究中,褒晴贬袭,是一般研究者所持的态度,这无疑有它的合理性。但在对她大加歌颂的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正是造成晴雯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一个“反省意识”空缺的悲剧。常日里,她动辄以主人自居,对地位比她低的丫头,稍有过错,非打即骂,平时说话带刺,凡事掐尖要强,锋芒毕露。这一切说明她对自身的奴隶地位,缺乏起码的自审意识和反省意识,直到被赶出大观园之后,才醒悟道:“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初也另有一个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处。不想平空里生出这一节话来,有冤无处诉。”真是“痴心傻意”得可怜,作为一名奴隶,怎么能和主子横竖是在一起呢?到头来,既没有保住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被逐,也未获得实际的爱情而夭亡。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把“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中为她所下的判词,作为她的“存在编码”试加破译的话,我们对她的悲剧性就会获得多层面的理解,而这也正是这一形象塑造成功的地方,决非单一的阶级论所能概括的。所谓“霁月难逢,彩云易散”——这是一个“真”之难以在世的悲剧;所谓“风流灵巧招人怨”——这是一个“自我意识”被摧毁的悲剧,也是一个“文化偏见”的悲剧;所谓“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这是一个“精神对话”落空的悲剧。加之上述的“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共同构成了晴雯悲剧的存在。尤其“风流灵巧招人怨”的文化内涵,更值得我们去发掘之,深思之。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见出,如果不从文化的角度入手,我们就不能发掘出晴雯悲剧的深层内涵,对她的解读也就会流于表面,有负作者的深心;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文化解读,将有助于我们的文化反省。文学作为“人文学科”,不正是借助文学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来开启我们的人文关怀,培养我们的人文意识,建构我们的人文精神吗?不然,你即使把作品完全背下来,又有何意义呢?
蔡元培先生认为,文学艺术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给予国民以心灵的慰藉、情感的陶冶,使人与人能建立起一种非功利的精神联系,拓展人的精神空间。所以,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作用如何估价都不为过分。作为一位语文教师,自身必须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以建立对文学的感性认识,同时要学习系统科学的文学理论知识,以建立对文学的理性认识,从而培养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和相当的文学情感。因为教师的文学素养直接关系到文学教育的效果,只有具备了深厚的文学修养,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学作品的意韵;只有具备了深厚的文学修养,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文学鉴赏;只有具备了深厚的文学修养,才能濡染学生,给学生的人格、情操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者通联:云南楚雄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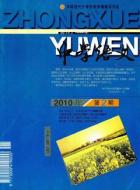
- 语文审美的逻辑 / 张 中
- 新形势下口语交际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 耿红卫 乔双莹
- 高中学生语言发展与教学促进 / 戴方文
- 阅读教学:如何有效组织\引导学生体验和反思 / 王聚元
- 细微的角色 宏大的主旨 / 田小华
- 在高一年级开展语法与修辞专题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 成 龙
- 是兄弟情深,更是纵情自任 / 周成华
- 品一品那些有意味的语言 / 屈伟忠
- “知行式”语文阅读课教学模式 / 孙秀丽 苑海燕
- 《教学大纲》规定的120个常见文言实词全攻略 / 姜有荣
- 从艺术思维的角度看喻代之别 / 王志生 陈礼林
- 对作文知识的再认识 / 顾忠民
- 文言句中“特殊动宾关系”十式 / 陈继民
- 闲笔不闲 巧夺天工 / 王 君
- 中学作文教学中教师的低效行为及不作为现象探析 / 冯齐林
- 新课程背景下文学教育的思考 / 李惠英
- 作文教学贵在有度 / 刘永红
- 陈寅恪的对子与语文教育考试 / 张慧腾
- 努力培养学生写作的深刻思维 / 陆明泉
- 学作君子之文 / 刘艾国
- 人性的绞索与祥林嫂的死 / 文 勇 孙绍振
- 《始得西山宴游记》设计践行 / 章浙中
- 《邹忌讽齐王纳谏》教学实录与点评 / 余映潮 丁亚宏
- 关注教学细节,演绎课堂精彩 / 卜盈姣
- 谈谈文本的多元探究 / 田政强 陆宝初
- 精心设计课堂作业 创造学生读写新空间 / 梅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