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2期
ID: 136141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2期
ID: 136141
从艺术思维的角度看喻代之别
◇ 王志生 陈礼林
借喻metaphor与借代metonymy的区别,尤其是关于鲁迅《故乡》中“圆规”和夏衍《包身工》中“芦柴棒”的喻代界定,语文教学界已有不少讨论文章,大家都从修辞学的角度作了深入有益的探索。笔者在此旧话重提,是想从艺术思维的角度重新梳理一下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所有的修辞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作家的艺术思维问题。因此,研究修辞中的喻代之别,必须站在艺术思维的角度进行审美分析。
我们先从剖析喻代之别的修辞学观点开始研究:
(1)“概括地说,借喻在以下三点上区别于借代:
第一, 借喻的本体喻体之间有相似点,借代的本体借体之间没有相似点。
第二, 借代的本体与代体之间是相关的关系,不应当把相似关系(借喻)也包容进去。
第三, 本体与喻体之间的联系具有临时性,本体与代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固定性。”①
(2)“圆规很不平”不是借代,理由是“圆规与杨二嫂没有不可分离的相关性”,且“借代因有代而不喻的特征,它同比喻是不相容的。”②
要而言之,以上所论皆建于“相关性”与“相似性”这两个概念之上。然而这两个概念本身并没有被界定清楚。硬说“花白胡子”与“长花白胡子的人”是相关性(没有相似性),“圆规”与“(圆规式的)杨二嫂”是相似性(没有相关性),在逻辑上是令人捉摸不透的。或说因为“花白胡子”生在“长着花白胡子的人”身上,故具有“密不可分”的相关性,“圆规”因为是新式的画图仪,故与旧式的杨二嫂没有血缘关系,只能定为相似(没有相关性),这其实将相关性理解得非常狭隘。
我们有必要重新解读一下这两个概念。众所周知,喻代皆是一种省略性修辞,是表现力很强的修辞手段,都是用一个名词或名词性短语表达一个句子才能表达的意思,使句子非常洗炼,使表达产生出人意料的新奇效果。从修辞要素上讲,它们都必须具备本体、借体(喻体、代体)和足以造成借用关系的(借代、借喻皆是借)审美契机。因此,喻代的不同首先表现为审美契机的不同。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是这样论述借代的:“所说事物纵然同其他事物没有类似点,假使中间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时,作者也可借那关系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所说的事物。如此借代的,名叫借代辞。”由此,构成借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从审美机制上看,因为此物的某一鲜明特征或标志,足以代表彼一事物,所以此物与彼物之间必须具有某种亲密关系甚至不可分离;二是从审美效果上看,借物一定比原物更形象、更生动。借代的认知心理是:把握事物的特征是其基础,在此基础上,发挥想象,用特征说话,使认知升华,创出新名,以点带面。如: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正气歌》)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李白《菩萨蛮》)
汗青——史册,玉阶——秦娥,本有互相关联的属性,史册以汗青显示,玉阶为秦娥所站立,汗青、玉阶因其极富特征化的个别属性,典型地传达了史册、秦娥的一般属性,这种特征化、典型化的表达常常使本借体之间浑然一体、不可分离,俗言“换名”有时也很难见出破绽。由此可见,借代也未必是指这些真真切切、不可分离的现实关系,有时它只是一种背景式的关联,是一个语境中的照应。此处的背景关联或语境照应,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常识,借此物替彼物,目的是使语言更形象、更有情趣,“和日常生活的语言作斗争”,但也造成了一种陌生,即以一种新的形象替代旧形象出来活动,简化和凸现了形象的特点,但这个新形象的内在是于旧形象的基础上突然创造出来的一个新形象,思维上有灵感性,语言上有“噱头”,结构上很精细巧妙,位置上因为依靠接近联想而造成了欣赏的临时语境性,这种审美契机也限制了借代的使用频率。“艺术品的本质在于把一个对象的基本特征,至少是主要的特征,表现得越占主导地位越好,越明确越好。”③借代之所以有生命力,原因就在这里。
借喻,是比喻的一种复杂形式,“大概感情激昂时,譬喻总是采用形式简短的譬喻;譬喻这一面的观念高强时,譬喻总是采用譬喻越占主位的隐喻或借喻。”④如:
你这人真是狗嘴里长不出象牙!
有麝自然香,他的才华不怕没有人欣赏!
学生总爱临渴掘井,这几天图书馆座无虚席。
老师又教训了我们一顿,真是恨铁不成钢!
因此,借喻是一种观念性的、省略性的比喻。“比喻能把印象扩大增深,用两种东西的力量,来揭发一种东西的形态和性质,使读者心中多了一些图象。”⑤由此可见,本体和喻体两个语言载体血缘关系越近,其差异性越小,它所产生的信息量越小,形象性也便越模糊。所以,借喻的“相似性”必须具备一定的距离性、隐蔽性。如“她的眼睛长得像妈妈一样”也可说是广义的比喻,但强调其非比喻,也是要造成陌生,增加阅读旨趣。
简单地说,借喻也是两事物的横向糅合,是修辞中的“蒙太奇”,但“一个意象是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⑥。因此,这种形象的组接,它不仅要依赖于语境,更要符合象征,更关注思想灵魂的深层吻合,它隶属于一个更为广泛的语义系统,因为互相之间位置较远而具有自由灵活的使用空间。
同时,“一种感情在找到它的表现形式——颜色、声音、形状或某种兼而有之之物之前,是并不存在的,或者说,它是不可感知的,也是没有生气的”⑦。作为一种形象的证明,借喻也是全方位的类比联想,颜色、声音、形状,充满了语义的和谐与形象的深刻。因此,一个比喻往往含有多种意思,谓之“喻之多边”,这也是借喻区别于借代的重要特征。“夫比之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⑧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诗人选中春蚕吐丝这一意象,除了表现对于爱情的至死不渝这一点外,还有丝是纯洁无瑕的,是温柔细腻的,是短暂而又美丽的等爱情喻意。
借喻的这种形象化的类比思维,我们也可以从构词中一眼看出:
雪白、火红、漆黑、带鱼、剑麻、凤尾竹、马尾松、鹅卵石、鞭策、熏陶、滑坡、风起云涌、鲸吞蚕食、枯木逢春、东施效颦、雪中送炭(重视视觉效果)
借代的这种典型化的接近联想,则需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才能知晓:
缙绅、巾帼、须眉、布衣、丹青、梨园、铁窗、干戈(重视联想效果)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概念+音响形象,借代立足于音响形象进行概念交换,形象的变化不大(外延变化不大,相关性),但内涵加深了(特征化了);借喻则立足于概念进行形象交换(外延变化了,内涵却是一样的)。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中“意义”一类字眼出现最多的是“meaning”一词,包括class-meaning(类义),element of meaning(义素),central meaning(中心意义),normal meaning(正常义),widened meaning(广义意义),narrowed meaning(狭义意义),dictionary meaning(词典意义),transferred meaning(转移意义),denotative meaning(内涵意义),grammatical meaning(语法意义), lexical meaning(词汇意义),借代依靠的是语法意义,借助语法寻找审美契机;而借喻依靠的是类义与转移意义,通过联想拓宽审美空间。
从审美功能学的角度看,借喻是通过本体和喻体的对接,拓深审美意境的。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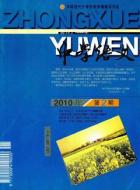
- 语文审美的逻辑 / 张 中
- 新形势下口语交际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 耿红卫 乔双莹
- 高中学生语言发展与教学促进 / 戴方文
- 阅读教学:如何有效组织\引导学生体验和反思 / 王聚元
- 细微的角色 宏大的主旨 / 田小华
- 在高一年级开展语法与修辞专题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 成 龙
- 是兄弟情深,更是纵情自任 / 周成华
- 品一品那些有意味的语言 / 屈伟忠
- “知行式”语文阅读课教学模式 / 孙秀丽 苑海燕
- 《教学大纲》规定的120个常见文言实词全攻略 / 姜有荣
- 从艺术思维的角度看喻代之别 / 王志生 陈礼林
- 对作文知识的再认识 / 顾忠民
- 文言句中“特殊动宾关系”十式 / 陈继民
- 闲笔不闲 巧夺天工 / 王 君
- 中学作文教学中教师的低效行为及不作为现象探析 / 冯齐林
- 新课程背景下文学教育的思考 / 李惠英
- 作文教学贵在有度 / 刘永红
- 陈寅恪的对子与语文教育考试 / 张慧腾
- 努力培养学生写作的深刻思维 / 陆明泉
- 学作君子之文 / 刘艾国
- 人性的绞索与祥林嫂的死 / 文 勇 孙绍振
- 《始得西山宴游记》设计践行 / 章浙中
- 《邹忌讽齐王纳谏》教学实录与点评 / 余映潮 丁亚宏
- 关注教学细节,演绎课堂精彩 / 卜盈姣
- 谈谈文本的多元探究 / 田政强 陆宝初
- 精心设计课堂作业 创造学生读写新空间 / 梅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