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2期
ID: 136150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2期
ID: 136150
陈寅恪的对子与语文教育考试
◇ 张慧腾
一
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有一段佳话。1933①年7月,陈寅恪应邀为清华大学代拟入学考试国文科的题目。作文题为“梦游清华园记”,此外陈寅恪还拟了一道对子题,上联为“孙行者”,要求学生对出下联,这道对子题后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有趣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邓云乡和吴小如对这“孙行者”对子的标准答案进行了一番争论,邓云乡《也说“孙行者”》认为“行”应读去声,所以“祖冲之”应是绝对,而吴小如《释“行”》坚持“行”是平声。好在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中明明白白地写道“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这段公案自然有了了结。从二人如此针锋相对的争论足以看出,陈寅恪的对子着实不容易,尽管后来吴小如《再谈“孙行者”对“胡适之”的公案》谈到答对“胡适之”的“不止一二人”②。当然,陈寅恪自己认为对对子“能于阅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这是后话了。
从今天看,陈寅恪的对子应当是特别之人在特定时期的特殊试题,这是一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个人行为,甚至有人认为这个对子是陈寅恪“借孙大圣来映衬、比照胡适的治学风格”③,但它毕竟是针对高校入学考试的,也必然会对当时的中学教育起到“导向”作用。直到今天,陈寅恪出对子给人们的启发仍应是多方面的,甚至包括教育改革和考试研究等等。许多论者在评价这道题目时似乎没有特别注意《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信的前半部分,在其中陈寅恪对语文学科性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和看法。
二
可以与《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进行异文比较的是傅斯年的遗稿整理者发现的陈寅恪《致傅斯年论国文试题书》④,后者再度阐明了陈寅恪出对子的用意,甚至他坚定地认为明年清华若仍由他出题,“不但仍出对子,而且只出对子一种”。两文的共同点是陈寅恪指出了中国语言的根本特征,认为在缅藏语系比较研究未发展之前,可以用对子来代替文法考试。陈寅恪强调印欧语系文法不能适用于中国语言,呼吁正确认识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两封书信还都怒斥了《马氏文通》的弊端,《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有“文通,文通,何其不同如是耶?”而《致傅斯年论国文试题书》中更是称其为“马眉叔之谬种”。
对对子与中国的“小学”相关,“小学”以训诂为核心,以音韵学、文字学为辅,从文字中心出发,符合汉语言的传统。而《马氏文通》则是以语法为中心来研究语言的,由西方语法学而来,并不适合于汉语的研究⑤。陈寅恪的考试命题行为背后体现着对中国语言本位的确认,这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时代背景之下更显得尤为可贵。从新文化运动介绍西方思想理论起,学界就引发了各种论争,诸如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论争,关于文言、白话乃至后来大众语的论争。这些论争都强烈地冲击了中国固有的传统语言文化。而当时大多数人对语言文化的认识和定位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左右。比如参与文白之争者无非三种观点,提倡文言、提倡白话,以及两者并举,其理据无非是从传承与发展,功能和使用角度出发。陈寅恪的看法超越了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回归到语言本体,从与西方语言比较中指出中国语言的独特性,这在当时无疑是相当超前的,在今天也可以给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西方化、现代化给20世纪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对教育尤其是语文学科教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今天的语文课程建设上,我们在引进西方先进教育理论的同时,更需要对我国现有的语文教育特征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把握,而最重要的是对汉语文学科本质有正确的定位。不再简单地生搬硬套西方教育法,这也是延续百年之久的“中西之争”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三
关于对子的命题意图,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中有四条说明,一是“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是“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是“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是“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
关于语文考试目标的指向,现代研究者一般认为要重在测试学生的语文能力,但具体而言,则无外乎听说读写四种能力⑥,按照这样的分类,这道对子题似乎难以进行目标的归类。其实,听说读写能力只揭示了语文学科的交际功用这一方面,类似语文课标所提出的语文的“工具性”,而对对子这一试题形式涉及了语文能力的多个层面。
重新审视陈寅恪的四条说明,第一条和第二条分属语法和语音的范畴,属于以文字为本位的语言本体知识,第三点“语藏”一词与陈寅恪好用外译汉的术语有关。“语藏”可以理解为词汇,因为《致傅斯年论国文试题书》一文原稿边上注有“Vocabulary”,“语藏”重在考察学生的语文积累和素养。第四点则指向学生的思维水平,洪堡特曾提出“每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思维观”,可见在语言运用之上是思维的支配。
对照今天的语文考试,多借助标准化的客观性试题来检测学生的语言本体知识,缺少应用情景的创设,或者所创设的情景远离生活实际。对于学生词汇掌握的考核无法进行简单的量化,其实学生能应用的词汇要远远少于认知的词汇。至于对学生思维水平的考察,或许可以在作文考试中体现,但现有的评分标准从一类卷到五类卷侧重于学生表达方式的量化,而忽视了学生写作情感和思想方面的探讨,这种看似公正而客观的评价标准却无法完全反映学生具有的思维水平。
科学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尤其是提高了人类各种行动的效率。但科学主义的涵义和价值并非完全正面。现今的语文教育考试力求精确的标准化试题,本身就体现了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忽视了语文学科的人文特性。科学主义固然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而在语文教育中的“去科学主义化”还前路漫漫。
四
陈寅恪的对子是当年清华大学的入学试题,尚没有多少人能对出正确答案,在当今除了专业人士之外,恐怕会对对子的人更少,而能对对子似乎成了一种让人羡慕的本领,正如高考用文言写作获得高分甚至满分者让人如此追捧一般。
近年来,上海市古诗文大赛高中组试卷的最后一题都是古诗创作。要完成这些试题需要基本的诗词格律常识,但学生并不能从平时的语文课堂上学到这些。甚至这些内容在当前语文教学中或许会被认为是超纲题或竞赛题,不符合素质教育“减负”的要求,这就不能把问题完全归结于语文考试本身了。
因此,就目前而言,过多地批判考试对日常教学的影响,甚至偏激地高呼取消考试意义不大。改善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语文学科、认识语文教育从而给予语文考试相对正确而合理的定位。
————————
注释:
①也有论者认为是1932年,如吴小如等。
②论争文章详见吴谷平主编:《都是媒体惹的祸》,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③转引自赵志伟编著《旧文重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王丁:《陈寅恪的“语藏”——跋〈陈寅恪致傅斯年论国文试题书〉》,《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2005年第1期。
⑤潘文国:《汉语的危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⑥章熊:《语文学科的考试》,《思索·探索:章熊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通联:华东师大中文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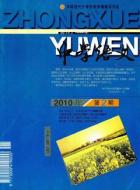
- 语文审美的逻辑 / 张 中
- 新形势下口语交际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 耿红卫 乔双莹
- 高中学生语言发展与教学促进 / 戴方文
- 阅读教学:如何有效组织\引导学生体验和反思 / 王聚元
- 细微的角色 宏大的主旨 / 田小华
- 在高一年级开展语法与修辞专题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 成 龙
- 是兄弟情深,更是纵情自任 / 周成华
- 品一品那些有意味的语言 / 屈伟忠
- “知行式”语文阅读课教学模式 / 孙秀丽 苑海燕
- 《教学大纲》规定的120个常见文言实词全攻略 / 姜有荣
- 从艺术思维的角度看喻代之别 / 王志生 陈礼林
- 对作文知识的再认识 / 顾忠民
- 文言句中“特殊动宾关系”十式 / 陈继民
- 闲笔不闲 巧夺天工 / 王 君
- 中学作文教学中教师的低效行为及不作为现象探析 / 冯齐林
- 新课程背景下文学教育的思考 / 李惠英
- 作文教学贵在有度 / 刘永红
- 陈寅恪的对子与语文教育考试 / 张慧腾
- 努力培养学生写作的深刻思维 / 陆明泉
- 学作君子之文 / 刘艾国
- 人性的绞索与祥林嫂的死 / 文 勇 孙绍振
- 《始得西山宴游记》设计践行 / 章浙中
- 《邹忌讽齐王纳谏》教学实录与点评 / 余映潮 丁亚宏
- 关注教学细节,演绎课堂精彩 / 卜盈姣
- 谈谈文本的多元探究 / 田政强 陆宝初
- 精心设计课堂作业 创造学生读写新空间 / 梅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