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13年第10期
ID: 361043
语文教学之友 2013年第10期
ID: 361043
细品《金岳霖先生》的“三味”
◇ 邹凤翔
经典作品如陈年佳酿,越品越有味;品味经典作品则如嚼橄榄,先涩再苦又甜,多味杂呈,越嚼意味越丰富。
汪曾祺先生所写的《金岳霖先生》是一篇值得一读再读的好文章,拿南京教研室徐志伟老师的话来说,小学可以抓住一个“趣”字,初中可以抓住一个“真”字,高中可以抓住一个“苦”字。笔者认为,作为高中生来说,不仅要读出“趣”,还要读出“趣”之“雅”;不仅要读出“真”,还要读出“真”之“贵”;不仅要读出“苦”,还要读出“苦”之“涩”。
一、读“趣”之“雅”
金岳霖先生为人天真,率性自然,而汪曾祺先生为文更是涉笔成趣。“哲学教授”穿体育教员才穿的夹克,“无儿无女”却自得其乐,“雅士”却好养斗鸡,“大人”和孩子比水果,“老人”却东张西望。汪曾祺充分运用对照手法,自身年龄、身份和情态的对照,金岳霖与周围人的对照,在对照中凸显出无穷妙趣。这趣因独特而分外分明而富有个性,这趣在对照中分外夺目而有趣。
但这趣,不仅是好玩而让人发笑,更多的是“雅”,这趣的精神底子是魏晋名士风度。冯友兰先生曾这样评价:“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我认为这几句话可以概括嵇康的风度,这几句话对于金先生的风度也完全可以适用。”讲课捉虱一节,汪曾祺先生写得极为传神:“小动物”“捏”“看”“甚为得意”,寥寥几笔,有语言,有动作,有神态,不以为窘,更不以为苦。一个严肃的演讲,一个庄重的论题,以没有关系结束,以捉虱收场,让人忍俊不禁。金岳霖先生的讲课捉虱之趣,与桓温扪虱而言如出一辙,但绝非刻意模仿。
而真正能代表金岳霖先生趣味之内涵的是他对学问的态度,乍看有趣,实际上是雅之至。他不仅说“我觉得它很好玩”,而且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金岳霖研究学问,摆脱名利之目的,只为好玩,正是对逻辑热爱到近乎痴迷,才一玩就玩了一辈子,一玩就玩成了“中国哲学第一人”,《知识论》一书六七十万字,初稿写成后毁于战火,只得重写,写了两遍。他对哲学真可谓一往情深,这种趣不可复制。
这“趣”的个性底色是率真、无机心、纯洁的赤子之心,这“趣”的文化根基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名士风度。这“趣”是童趣,也是情趣和志趣。超凡脱俗,不可复制,也无法模仿。
二、品 “真”之“贵”
文中记叙的金岳霖先生的诸多言行貌似有趣,实则是孟子所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他在学术问题上说真话,待学生、朋友一派真诚,为人天真不造作有真性情。
他真诚,“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这是每一学年对新生上课的“实情告白”。如实告诉学生,直陈原因,消除学生的疑虑。
他真实,讲《小说和哲学》,“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他的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面对大家的期待,他不故弄玄虚,也不随众附和,尽管“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
他天真,不仅与斗鸡同桌吃饭,还养过蟋蟀,斗蛐蛐,家里的蛐蛐罐一大箩,雅士俗好,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不必附庸风雅,只是在理性的王国之外进行自由的释放。
他认真,林国达死了,“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面对年青而美好的生命的不幸逝去,金先生之“一直没有笑容”与《晋书·阮籍传》中所记载的阮籍为“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之哭,何其相似。一样的坦荡率真,一样的珍惜美好,痛惜伤逝。林徽因已然去世,金岳霖的情意依然萦怀,专门为其生日请客,特地到北京饭店这样豪华的地方,到了之后“才”宣布,态度郑重几至神圣。而林徽因活着的时候,不过“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 死后如此隆重,两相比照,恐怕满座都要为之感佩吧。
金岳霖之“本然”,可谓到极致,真正可贵。
三、思“苦”之“涩”
汪曾祺先生在《蒲桥集》自序中说:“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感伤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很明显,汪曾祺不主张倾泻式地任感情的洪流肆意奔涌,而是有意将感情加以节制,将感伤藏于家常语之中,如泉水行于冰下,有点幽咽,有点苦涩。但反复细读,还是能读出平淡语之后的感伤,因此回味特别悠长。
最典型的莫过于作者记叙金岳霖先生晚年按毛主席的指示坐平板三轮车接触社会:“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本已深居简出,却要接触社会;80多岁的老人,坐着平板三轮车;名满天下的大哲学家,无人识得出。这样的境遇,俨如“独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但凡用心读的人都难免唏嘘不已。
此外,本文提到的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岳霖的3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底以前。“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在时代的浊流中,这样一个有雅趣、有真性情的人,也不免被要求,被作出改变,不能不让人哭笑不得。
而文章的首尾作者一再说:“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许多教授”,金岳霖只是其中一位,值得写的还有很多很多;“应该有人”,饱含不尽的期待和隐隐的无奈;“好好地写一写”,带着意犹未尽的遗憾。写这篇文章时,汪曾祺先生也已年近古稀,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十年,汪先生也去世了。
细细去读,汪曾祺先生的弦外之音中带着一代人对一个时代的苦涩记忆,吕冀平在《负暄琐话》的序言中曾经这样评价张中行散文的特点:“作者对他所谈的人和事倾注了那么深沉的感情,而表现出来的却又是那样地冲淡隽永。我们常常能够从这冲淡隽永中咀嚼出一种苦味,连不时出现的幽默里也有这种苦味。这苦味大概是对那些已成广陵散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伤感,也是对未来的人、未来的事虔诚而殷切的期待。”这段话用来评价汪曾祺的这篇文章也非常合适。他怀念的不仅是逝去的金岳霖先生,还有那如《广陵散》般不可复制的西南联大教授们的美好精神。
(作者单位:江阴市第一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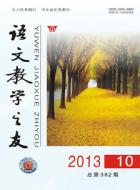
- 精心营造语文课堂教学的“亮点” / 李娟
- 有效,还是有趣? / 黄海燕
- 提高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有效性的策略 / 陈祥云
- 浅谈中职语文教学中实践能力的培养 / 黄茜
- 语文课堂有效教学反思 / 张隋全
- 在细雨中静待花开 / 陈海亮
- 在初语教学中实施研究性学习初探 / 罗贤云
- 语文课堂教学应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 吉晓祥
- 《风筝》教学内容述评 / 张聪慧
- 对《史记(选读)》教学的一点思考 / 李叶
- 课堂,让生命诗意地徜徉 / 万中方
- 散文阅读教学初探 / 焦春艳
- 初语课外阅读常见误区及对策分析 / 邓振娟
- 谈引导学生走进文言文本的有效方法 / 姜维聪
- 蜩与学鸠笑大鹏探因 / 杨亚民
- 《史记》中的“赘笔” / 杜茂利
- 飞鸟意象与陶渊明的精神历程 / 张俊杰
- 浅议《安恩与奶牛》对比中的人性美 / 陶波
- 论李舵《美丽的西双版纳》之美学特质 / 鲁昌曾
- 困境中的正能量 / 张慧
- 谈《雷雨》中周朴园的性格悲剧及其价值取向 / 王云雨
- 细品《金岳霖先生》的“三味” / 邹凤翔
- 说说《雷雨》的讽刺艺术 / 张怡春
- 抓住四个环节 贯穿一种精神 / 王奎群
- 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思辨能力 / 李文军
- 美化板书设计 美丽语文课堂 / 王丽华
- 语文教师应如何把握“课文” / 保宏超
- 实施分层教学 提高教学质量 / 童雪
- 语文教学设计的策略探究 / 赵云
- 谈高中作文“自评、点评、互评”教学模式 / 朱广龙
- 浅谈举例论证在议论文中的作用 / 李军
- 言论式材料作文写作指导 / 李冬梅
- 议论文写作如何“反弹琵琶” / 汪雪梅
- 高中生小小说写作“四步曲” / 严红艳
- 《那树》的文化性探究课堂设计与实践 / 陈发明
- 撬开金口 激活课堂 / 詹宝仙
- 言说贵思:课前“三分钟”活动的启发 / 陈李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