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12期
ID: 137820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12期
ID: 137820
深情凝眸生命的长河
◇ 万仲永
【摘 要】文学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学还是一种生命现象。综观沈从文的小说,在奇思妙想之后,无不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对人性的执著探求,是沈从文小说的基点和纲要,沈从文以此来构筑属于他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
【关键词】沈从文 生命意识 乡土 人性 非理性 悲观
生命意识,意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所呈现出的种种生命形态作自觉的沉思与探索,它是人对自身生存状态所作的一种返观。生命意识作为一种创作观被得到强调,是因为生命与文学是相伴相生的。文学表达的应当是对万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不倦探寻,真正纯粹的文学精神要求作家用生命的曙光去烛照读者的心灵,借此唤起他们对于生命的热烈向往以及对高质量生命的健康追求。所以,生命意识能够成为我们窥探作家创作观念的一个窗口。下面,我们试着对沈从文创作观中的生命意识作一剖析。
一、乡土:生命的根
作家与故土的联系是一种生命联系,尤其对于一个生长在乡村的作家而言。故乡生活在作家创作中的地位,除了题材倾向的决定外,更为主要的是对于作家人生观与审美观的铸造,对于作家基本生命素质的确定。那么创作中的乡土意识,在深层意义上,它应该是作家对生命之根的一种寻找。
沈从文的生命意识孕育在他那片风貌独具的湘西故土中。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使湘西一隅的地域色彩显得异乎寻常的浓厚。在地理分野中,湘西和黔北、川东接壤,有“中国盲肠”之誉,边域荒僻,却不乏大自然的灵秀之气,万山细流,亦处处洋溢着生机,湘西的山与水、城与乡,均非贫瘠偏僻所能概括。人文方面,山民们猎兽充饥,对歌定情,在原始野性中爱与被爱,凭着山民特有的胃口品尝着生命的种种欢愉和忧伤,他们强悍但却充满深情,他们粗犷但却懂理,他们不乏野性却具有璞玉般的品质,湘西人在自己独特的生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独特的生命体验,湘西的人与事、哀与乐,亦非蛮悍蒙昧所能表达。雄浑而又灵动的湘西山水,自由流动的生存形态生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氛围。沈从文,一个“在这地面上”过了二十年日子的青年毫无选择地在其中完成了自己生命意识中最基本的铸造。
沈从文对乡土的依恋并不意味着他对那种近于原始的生命形态的完全认同。事实上,沈从文着眼的是现代人生命结构的建设,只不过他是站在昨天的时空里,力求从过去提炼出于今天有益的精神元素。按照沈从文的说法,他是在倾心于“国家重造的设计”。沈从文凝结在乡土情绪中的寻找意识一方面是对现代文明的怀疑,因而强调它的缺陷,比如《八骏图》里八位教授均心灵空虚,行为乖离,精神异常,由于断了传统之根而害了很蹊跷的病。在沈从文看来,他们共通的病是现代文明对自然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但沈从文又并非反对文明的现代进程,他只不过是从建设的角度探讨如何保存和发展自然人性及其他生命素质,使之成为现代人的生命要素。另一方面,沈从文对于故园乡土的眷恋又并不能使我们据以判定作家是在亲近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传统文化。事实上,童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已开始抵触《诗经》、《论语》、《幼学琼林》一类的教材了,并且形成了自己“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此外,湘西特异的地域环境也使这片土地相对较少地受到儒家文化的熏染。沈从文借乡土以寻生命之根的特殊性就在于他力图从一个地区性的少数民族(苗)的观点出发,考察一个较大的文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仍然是在中国文化内部对中国文化所作的批判。怀疑现代化文明却非主张原始性的回归,寻找传统之根又非对正统文化的盲肯,这就是沈从文乡土意识的基本特征。
沈从文的乡土意识具有典型性。一方面,沈从文的乡土情绪源于对我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历史过渡的思考,带有明显的现代中国特色,它有别于西方后工业社会那种彻底的原始主义态度。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沈从文的乡土意识又能让我们窥见一些传统的精神基因。作品中某些超然的气息,让人想到道家的生存哲学,作家对生命的苦苦探索,让人联系到屈原的上下求索,作家对自然风情的亲昵描绘,又让人忆及陶渊明的与万物同化。所以传统文化中关于自然与人生的理解依然流淌在沈从文的乡土意识中。沈从文乡土意识中的时化印痕与民族色彩使他能够成为乡土小说作家群中的特立者。
二、人性:生命的内核
既然沈从文要用一支笔去解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复杂多方”的生命现象,那他就不能不涉足人性的领域。虽然文学与人性是一道复杂的创作命题,但沈从文依然凭着“乡下人”的任性,热情地去表达自己对人性的理解和追求,重视“人性”为自己生命意识的内核所在。他这样写道:“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在沈从文的创作观念中,人性应当是文学生产的起点和归宿。他说:“人心与人心的沟通和连接,原是依赖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的”,“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对文学使命的理解,沈从文方自称为“人性的治疗者”。
沈从文对人性有自己的理解。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是这位作家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不倦探索的主题,同时也正是这一“共通人性”一度给沈从文带来了“抽象人性论”的批判。时代发展到令天,随着人性探讨的深入发展和人们人性的不断趋于科学与合理化,那种否定人性存在、将人性等同于阶级性的庸俗社会学人性已被摒弃,阶级社会中的人性除了带有阶级性外还存在共同人性的观点已为众多人所接受。相应的,在对沈从文人性探求的评判中,人们已经能够运用永恒性与历史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事实上,认为沈从文的人性表达既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内容,反映了某种历史生活的真实,又客观地存在抽象化的瑕疵这种评判已成为共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的解释和辩证评价。
这里我们想谈及的是鲁迅与沈从文两位文学巨匠在人性领域里的不同探索。著名学者金介甫在研究沈从文时指出:鲁迅和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可以比肩的两位巨人。如果说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毕生用作品表达了对中国人的恨,那么沈从文的伟大则在于他表达了中国人的爱。尽管这一说法不无商榷之处,但却正确地发现了这两位作家独特性的巨大反差,如同沈从文自视为“人性的治疗者”一样,鲁迅致力于“国民性”的探索,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但他们的思维角度及侧重点明显迥异。鲁迅遵循的是历时性原则,在他看来,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沿着从落后、愚昧的“原始”向进步、文明的“现代”这一进化轨迹演变。这种进化论的生命信念恰如摩尔根所表达的:由于人类是同一起源,因而他们的经历也基本相同。尽管发展不同,但在所有大陆上发展渠道是一样的。人类所有部落和民族都发展成极为相似的进步形态。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差异在于他们所处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不同。前者被后者取代也是历时性逻辑上的必然。鲁迅着眼于国民性的改建,而不考虑人性的普遍性,原因正在于此。与此相反,沈从文在作品中则灌注着共时原则和共同人性的观照,他更愿意关心的是全人类在经济时代都共有的普遍的人性,即生命的自然本质和原始形态的现代遗存。他曾表达过这一信仰:因为我说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行影,永远是一种德性,也因此使我们永远对它崇拜和倾向。可以说,沈从文对于人性的共同性的关注和鲁迅对于人性的历时性探索互补地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对人性问题比较完整的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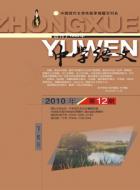
- 浅谈语文教学中的对话教学 / 王 成
- 语言文字教学取向变迁带来的反思 / 叶诞丰
- 浅谈合作学习与教师的自我转变 / 邰雨春
- 浅谈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与学生的文学教育问题 / 孙立刚
- 新课程呼唤高中教师教研活力的蓬发和教研方法的改变 / 邱康源
- 豪华落尽见真淳 / 范菁华
- 当前学生厌学语文情绪呈现的新特点 / 邱宇良
- 高效课堂的“谋”与“导” / 赵秀兰
- 学生日常行为习惯与学习成绩关系研究 / 陈 敏
- 师生互动,创设有效课堂 / 任 媛
- 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审美能力的培养 / 邓云政
- 浅谈语文学科精神的培养 / 莫鸿娇
- 从学生实际出发 构建高效课堂 / 孙立新
- 优化课堂教学 提高课堂效率 / 陈裕毅
-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教学反思 / 禤 莉
- 如何在体验式教学中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 谢永春
- 浅谈语文课堂的实效性 / 王 梅
- 幽径觅佳趣,探究现洞天 / 欧有萍
- 巧用插图,图为文用 / 章壮年
- 点燃阅读的智慧 / 刘雪玲
- 经历与反思 / 苏正淮
- 自由是灵感的源泉 / 王 晶
- 悦读名著:让高考语文轻舞飞扬 / 张莉娟
- 高中语文感悟式教学的思考与实践 / 成志刚
- 读中有真味,写中有真情 / 方秉正
- 现代文阅读教学实效性初探 / 吕新毅
- 初中语文课堂如何创设教学情境 / 张美荣
- 优化课堂教学以提升初中生口语交际能力 / 余巧燕
- 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如何指导学生自主学习 / 王 羽
- 从两节课看教学设计的有效性 / 张桂萍
- “评点式教学法”在小说教学中的运用 / 王海蓉
- 优化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探微 / 向 荣
- “学”字立骨,提升文言文教学的有效性 / 钱 艳
- 一首涵蕴甚深的诗 / 曹淑芳
- 品味诗趣 渐长涵养 / 黄静冰
- 高中文言文教学方法之我见 / 张 伟
- 一样怀念别样情 / 汤丽萍
- 语言和精神的同构共生 / 隋淑萍
- 《用“心”抒写颁奖词》教学设计 / 郑玉涛
- 黄鹂婉转柳间啼 景美更须人心善 / 李姗苗
- 例谈叠音词的表达效果 / 杨华军
- 阅读教学中实施情感教育的有效策略 / 许海霞
- “泡”以通关,写以增效 / 李元洪
- 《语言规范与创新》补正 / 胡彦民
- 关于现代文阅读试题的反思 / 谈 娟
- 以《雨霖铃》为例谈古典诗词文本细读教学策略 / 范芝芝
- 浅谈作文写作之细节描写 / 叶群章
- 审清题意,贴切选材,发表新见 / 陈 玲
- 关注生活,关注阅读 / 钱 丽
- 深情凝眸生命的长河 / 万仲永
- 让你的观点脱颖而出 / 董志龙
- 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 / 吴贵阳
- 文化解读张爱玲小说中的怀旧意识 / 王晓娟
- 叙议结合.繁简得宜.准确对接 / 陈 荣
- 新课程背景下的“还”与“让” / 唐运兰
- 在自由写作中流淌心灵的声音 / 张 锋
- 让互动使学生作文既会说又会写 / 游德发
- 对语文高效学习的一点思考 / 李启明
- 仿写课文,挖掘农村初中学生写作潜力 / 沈素艳
- 中学阶段口头作文有效教学尝试 / 周益鸣 裴莉莉
- 以情教人,以情育人 / 赵娴丽
- 学会遣词运语,轻松点亮文采 / 张 华
- 如何培养学生修改作文的能力 / 吴春凤
- 在模仿中不断创新 / 吴政国
- 浅谈《滑稽列传》“滑稽”之思辨艺术 / 李春草
- 几棵树苗, 一片森林 / 曹 洁
- 语文课呼唤感性教学 / 周文辉
- 摭谈中国古代的“避讳” / 徐 江
- 给激情与智慧以舞台 / 沈晓航
- 语文教学中的语感培养 / 孙晓星
- 异彩纷呈的民俗风情画 / 周秀荣
- 清风润眸,明泉洗心 / 张 弦
- 初中文言文阅读教学目标宜少不宜多 / 王梅花
- 高中语文教学要关注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 邹应谋
- 关注课本里的谐趣,培养学生幽默素质 / 李君山
- 涉浅水者见鱼鳖,入深海中擒蛟龙 / 郭丽华
- 地方文化在语文教学中大有作为 / 赵明发 孟存荣
- 写身边事 论平常理 抒心中情 / 涂淑琴
- 科技文阅读设题特点及答题技巧 / 黄胜利
- 拨开云雾见天日 / 张洪峰
- 浅谈破解江苏卷现代文阅读瓶颈的方法 / 张 英
- 考场作文的十种意识 / 杜 波
- 高考作文要写得“大气” / 杨亚雄
- 从信马由缰到戴着镣铐飞舞 / 卫元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