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11期
ID: 137755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0年第11期
ID: 137755
困境中精神家园的守护
◇ 丁春美
【摘 要】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几乎每个流派都有重要诗人遭贬谪流放。忠而被贬,贤而被迁,不平则鸣,发而为文,写出了对现实的认识,抒发了心中的愤懑之气。要把握贬谪文学的思想内容,理解他们当时的心态是关键。
【关键词】贬谪文学 贬谪心态 精神家园
士,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阶层,不仅有强烈的文化自我意识,而且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士人的一种普遍意识。于是由士而仕,有了参政的机会,与君主政体形成了相互依存的格局。但宦海有不测风云,当士大夫的文化精神与君主专制制度发生冲突时,士大夫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凉之境。于是历朝历代贬官迁客不乏其人,形成了特殊的知识文化群体。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因此他们的心态更为复杂,他们的诗赋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似乎正为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作了注释。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几乎每个流派都有重要诗人遭贬谪流放。忠而被贬,贤而被迁,不平则鸣,发而为文,写出了对现实的认识,抒发了心中的愤懑之气。因此,要把握贬谪文学的思想内容,理解他们当时的心态是关键。
贬谪对士人来说,绝对是一场悲剧,但“兼济天下”的理想并未因此彻底破灭,许国忘身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使得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充满了历史使命感。饱读诗书的士人当然忘不了孔子的谆谆教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们接触了解的生活环境只有两种:庙堂和草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的这句话很好地总结了士人的心境:不仅达时要兼济天下,即使穷时也不能忘记为国家为君主为百姓操心。因此贾谊在被逐的情况下,仍关心国家的命运,用《过秦论》总结亡秦的历史教训,想为汉代借鉴。李白,被流放夜郎后仍“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期间,写作了彪炳史册的“三吏”、“三别”,关心的仍是民生疾苦。元稹在同州时,曾经将当地旱灾归罪于自己:“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苏轼在《江城子》中,曾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为国效力的心情体现得更是迫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即使处于被贬这种尴尬的境地中,他们仍然自觉地、主动地背负起沉重现实的十字架,明知再也没有施展自己抱负的政治舞台,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历史使命感在贬谪文学中表现非常突出。
士大夫遭贬谪,或是因为忧民疾苦,与当权者政见不合;或是才高遭妒,受小人谗毁;或是卷入党派斗争。因此贬谪士大夫普遍存在一种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怨愤之情。但君主专制力量的强大优势,忧谗畏讥的心理,使他们不便于直抒胸臆,于是他们或用比兴手法,抒发心中对君主的不满,自己内心的委屈。屈原在《离骚》中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托儿女之情以写君臣之事,以花草自喻,表达自己内心的忧虑。辛弃疾用“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那人”表现自己的清高自守。骆宾王借蝉自喻,用比兴手法寄托自己遭谗被诬的悲愤心情。或借评论历史人物,表达对自己所受遭遇的不满。辛弃疾用历史上的美人陈皇后遭嫉妒,比喻自己被排斥及政治上的失意。苏轼用三国时羽扇纶巾、风流倜傥的英雄周瑜形象,含蓄地表明自己的抱负。或用今昔对比手法,感旧伤今。秦观《望海潮·梅英疏淡》中用大量笔墨描写旧时的欢宴游赏,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和当今重游时的伤感形成鲜明对照,自然是为了表达在新旧党争中遭到贬斥,经历过宦海浮沉与人事的巨大变化后作者个人痛感世事沧桑的抑郁情怀。更多时候,贬谪士人们用满眼凄凉的景物来映衬自己满腹的悲凉。杜甫《登高》中看到的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悲凉凄清。白居易《琵琶行》中贬居的九江是“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柳宗元描写他被贬到的柳州是“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的蛮烟瘴雨之地……其实这些贬谪之地在当时也不一定都如此荒凉,只不过在贬谪士人眼中,远离了政治中心的“朝”,这些地方就是“野”,哪怕它经济上已是“闾阎扑地,舸舰迷津”,在失意人眼中也只有蛮荒凄凉。说到底,这些景不过是贬谪士人悲凉怨愤心情的一种投射。
士人十年寒窗,饱读诗书,本是要投身宦途、大济苍生的,如今却被废置于蛮夷之地,才学难施的生命荒废感随着贬谪时间的延续愈加强烈。浪漫如李白者在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已达八年之久的天宝十一年,在美酒会友时仍唱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悲叹时光的流逝,生命的易老。豁达如苏轼者在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时,仍忍不住自嘲“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更不用说念念不忘报国的杜甫“艰难苦恨繁霜鬓”,一生以收复失地为己任的陆游“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辛弃疾“可怜白发生”,前途渺茫,打击沉重,抱负难以实现,壮盛之年就这样缓慢而又迅速地度过,取而代之的是惊心的白发,衰老的心境。
贬谪士人的政治悲剧也激发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使得一些人对功名逐渐淡漠,在优游山水中追求一份心灵的恬静。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时,遍游永州境内山山水水,写成“永州八记”,生动表达人对自然美的感受,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中那高于群山、卓尔不群的西山何尝不是作者人格精神的象征?苏轼在《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中把归隐视为傲视独立的表现,把返归自然当作精神的慰藉和享受。于是贬官后的士人情有所系:苏舜钦有沧浪亭,欧阳修有醉翁亭,苏轼有超然台,苏辙有喜雨亭……他们在求得心灵平静的同时,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既然不能“铁肩担道义”,就让我“妙手著文章”,让我的名声才华显露于后世!
由于个人经历及心性的千差万别,贬谪士人的心态也有不同,如北宋士人就比唐朝士人更容易从困境中超越出来,在具体阅读中尚需我们细细体会。但作为一个有类似遭遇的文化群体,还是存在大量的共性。
★作者单位:江苏省海安县立发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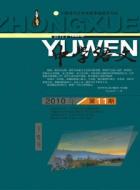
- 融合“三维目标”是实施课程改革的关键 / 官炳才
- 从“主演”到“导演” / 钱海霞
- 新课程背景下语文教学的误区 / 薛海峰
- 制造矛盾冲突 提升教学艺术 / 谭晓春
- 人文素养之于语文教学的重要性 / 沈 俊
- 策略是杠杆,情感是支点 / 李奇生
- 浅论中学语文情感教育 / 杨 武
- 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探析 / 朱 燕
- 引导学生进行正确而有效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感发 / 王春建
- 新的语文课程需要新型语文教师 / 郑勤敦
- 激发学生情感潜能 迎来课堂高效曙光 / 高 云
- 谈新课标下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 张德青
- 浅谈如何让学生真正走进语文课堂 / 顾蓓蓓
- 浅议如何在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 陈家武
- 妙用导语打造成功课堂 / 杨文清
- “教是为了不教”的文言文教学实践 / 蒋永华
- 高中新课程背景下语文专题学习初探 / 李龙宗
- 创设高三课堂情景 培养自主思考能力 / 黄为民
- 为有源头活水来 / 赵冀长
- 贯彻新课程理念,科学实施新课程 / 毛 伟
- 课堂评价的“敏感地带” / 杨 梅
- 转变叙事视角,有梯度地感受诗歌 / 李 珍
- 浅谈如何提高普通高中学生的语文素质 / 邓佩娟
- 用程序单让集体备课有备而来 / 陈宽明
- 《直面苦难》教学案例 / 韦宏梅
- 创新中学语文多媒体教学的路径 / 张义敏
- 重新审视新课改下的语文阅读教学 / 顾维萍
- 来一点怀旧式阅读 / 韩秀清
- 诗歌选修教学的审美与实用价值探讨 / 黄铁英
- 探索阅读教学方法 发挥阅读教学功能 / 周利燕
- 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人文精神浅析 / 余晓琳
- 传承与创新 / 楚学群
- 从阅读中受启发,在启发中感悟教学 / 黄永凤
- 人类文学的主题:寻找精神家园 / 杨彦辉
- 文言文教学要强化诵读 / 段纪学
- 张扬个性精神 促进主动发展 / 孙广朋
- 《选读》杂多特点及其心流目标的达成 / 杨金华
- 用成语巧破文言教学三难关 / 周卫芳
- 阅读教学有效对话一二三 / 马 平
- 韵味无穷的意境美 / 王安逸
- 关于阅读教学中实施“有效问答”的几点思考 / 屠洪根
- 试谈李商隐《安定城楼》的用典艺术 / 席 红
- 古典诗词语言艺术品味方法例说 / 许海霞
- 从论据使用看《朋党论》《留侯论》 / 洪 建
- 怎样把握古代诗歌的思想感情 / 宋美华
- 中学作文的问题与对策 / 顾金友
- 志伟景壮 情昂物跃 / 杜彩恒
- 浅谈影响诗歌鉴赏教学的因素 / 陆红艳
- 多渠道引来作文的活水 / 孙道朝
- 于平淡中暗响惊雷 / 蔡成兵
- 形象 / 杜峦洲
- 巧用多媒体提高写作能力 / 黄振菊
- 《守财奴》 中葛朗台行动描写的几个特点 / 赵武之 李晓奎
- 受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 倪 林
- 一堂特殊的作文指导课 / 朱 敏
-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 吕春宝
- 一个值得商榷的注释 / 龙开泉
- 从中西文学发展看国民性 / 杜 金
- 对新课程下考试制度改革的另类思考 / 王忠宝
- 充实你的素材库 / 雷思容
- 谁“偷走”了学生对母语的感情 / 肖君章
- 正“本”清“源” 返“朴”归“真” / 盛伟华
- 万绿丛中一抹红 风光不与他家同 / 王广东
- 与语文同行 / 陈晓春
- 灵活运用教材进行作文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 史庆华
- “二分对照,辩证分析”:辩证议论文的基本模式 / 杨志芳
- 作文创新能力提升浅议 / 陈麒宇
- 做好语文人,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 / 罗忠秀
-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 顾叶斌
- 困境中精神家园的守护 / 丁春美
- 语文教师的幸福感从哪里来 / 李冬梅
- 学校要发展 教师是关键 / 史生有
- 让琅琅的读书声走进高三语文复习课堂 / 秦慧华
- 浅谈《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 蒲 浩
- 音乐是学习语文的一股清泉 / 刘克凤
- 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打造幼儿兴趣课堂 / 范菁华
- 让试题讲评课由低效走向高效 / 王永刚
- 班刊:培养学生语文自主学习能力的试验田 / 罗宇中
- 高考散文阅读答题能力提升之我见 / 岳林水
- 浅谈如何培养学生的平民情怀 / 李惠英
- 为学生配一把思维的钥匙 / 曾志洪
- 农村中学语文教学的困惑 / 王 华
- 材好一半文,考场占先机 / 陈宝祥
- 安徽自主命题高考作文命题趋势 / 葛徐栋
- 一道令人叫好的高考试题 / 金方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