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2年第2期
ID: 133827
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 2012年第2期
ID: 133827
背景:标签或者补丁
◇ 周晓冬
【摘 要】长久以来,在解读文学作品和文本教学中,“时代背景”或“写作背景”的解说占据着重要地位。“背景”被当做理解、阐释一切作品的前提和基础,并决定着作品的意义。其实,接受理论告诉我们,“背景”可能是一张大而无当随处可贴的标签,有时甚至是成了一块破坏作品整体美感,消解读者审美愉悦的补丁。背景批评应当允许存在并作为探寻意义的一条途径,但不应让背景替代人们的阅读与理解,更不应让背景越俎代庖地取代审美主体的感悟。
【关键词】写作背景 阐释 意义 诗无达诂
“时代背景”或说“写作背景”,向来在语文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分析文学作品,“背景介绍”更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翻翻各种版本的教材,每篇课文不论现代文古文还是诗歌,正文前的“阅读提示”或“预习提示”,都毫无例外的有一块背景介绍;在“教参”或“教师用书”里,必定有相当的篇幅是用于提供更为详尽的背景资料的,在“教学建议”一栏,往往不忘“建议”老师:“为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准确把握作品主旨,宜先将该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思想状况向学生作简要介绍。”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会时时告诫学生:“只有了解了时代背景及作者的情况,才能真正理解作品”。“背景”是理解阐释一切作品的前提和基础,并决定着作品的意义,这地位、权力似乎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它真的有这么大能耐么?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一直被恭恭敬敬奉在卷首的“背景”,有时的确是一把打开意义大门的钥匙,而有时则不过是一张大而无当随处可贴的标签,有时甚至是成了一块破坏作品整体美感,消解读者审美愉悦的补丁。
以文中标明的写作日期为线索,去查找到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及政治气候,再依照作者的生平行状和政治倾向,来推求作者当时的写作意图,进而索解作品的意义,在中学课堂里讲解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用的就是这种最为常见的鉴赏文学作品的方法和流程。教材里通常有这样一段提示:“《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或“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白色恐怖的气氛笼罩全国”)。作者在文章里描述了一幅清幽美妙的图画:曲曲折折的荷塘,密密田田的荷叶,星星点点的荷花,淡淡的月色,脉脉的荷香……这一切又交融着作者那隐隐的,却又是深沉的孤独与苦闷的心绪。这正是那个黑暗时代在作者心灵上的折射。”这还不算完,编者生怕广大中学生不能清楚而准确的感受到这种时代特征的“折射”,便进一步点明:“阅读时,要重点抓住‘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令我到底惦记着江南了’等语句的深刻含义。这样,就不难理解文章的主旨了”。本来一篇结构并不复杂篇幅也不长的写景抒情散文,理解起来的确不难的,但经这么一“提示”倒真的让人为“难”了,仿佛处处隐藏着以“春秋笔法”写就的微言大义,比如“颇不宁静”是某政治事件的折射,“江南”实指发生了反革命政变的“上海”,如此索隐下去,连天上那轮“今夜不能朗照”的月亮,也大为可疑,恐另有所指。当然,这一番喋喋不休的耳提面命也并非全无意义,起码能将这篇带几分古典意境的婉约小品升格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朱自清先生也由一位月夜漫步荷塘“受用无边的荷香月色”的颇富雅趣的文人,变身为时刻在观测政治形势的时事评论员。贴上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标签,也许有助于凸显朱自清先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但同时也带来不少尴尬,例如,若说文中的“苦闷哀愁”是当时黑暗与恐怖的“折射”,那么,通篇如荷香似月色的“淡淡的喜悦”又是什么社会情状的折射呢?如此严峻的时局下他的“喜”从何来?再者,文后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927年7月”,也就是说,朱自清先生面对这起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时隔三个月,才在一篇赏月品荷的散文抒发一缕融合在“淡淡的喜悦”里的“淡淡的哀愁”?如此这般的“介绍”、“提示”究竟是要突出“有骨气”、“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粉”的朱教授的正直义愤还是冷漠麻木?
另外,近有爱抬杠较真者,说查阅朱先生的日记,发现那天先生与太太吵了架赌了气,因而“心里颇不宁静”,于是走出家门到荷塘边散步散心!若确有此记录的话,就更表明“时代背景”这块标签实在大而无当,且贴得不是地方。再者,即使那天夫妇俩相安无事一如往常的和睦,恐也不能断定朱先生夜游荷塘的动机就是有感于那起政治事件。试想,仅以中国而论,地域之广、人口之众、事发之频,一年一月一日之内发生的可致人心绪不宁的事不知凡几!而况,作为文学家的朱自清本就是敏感善感之人,能引发他情绪波动的人、事、物,更不知凡几!一个宽泛无边的“时代背景”,又怎能框得住对得准?
我们不能说一切背景对于作品意义的理解都是毫无作用的,但是,若把它当成万能钥匙,逢锁即开,且是理解作品的唯一可靠的途径,就像浦起龙认准的那样:“缵年不的则徵事错,事错则义不可解,义不可解则作者之志与其词俱隐而诗坏。”(《读杜心解》),则不可避免的陷入一连串的困境。
首先,作品的写作背景并不都能考证清楚。能像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这样在文后清楚标明年月日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当然,因是现代作品即使无准确日期,要确定一个大致不差的写作时间段也不难,况且作者还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是,那些年代久远的作品呢?且不说史料“代远多伪”,也不说我们看到的所谓“历史”不过是历史学家的一种历史叙述,而“历史叙述早诗歌及文学作品本来是要给人们以艺术美感享受的,而这种精确到有些残酷的背景批评却常常破坏这种乐趣,好像用Ⅹ光透视机把美人看成肺腑骨骼,用化学分析把一朵花分解为碳、氢、氧。堪称集古典文学研究之大成的“鉴赏辞典”系列,就为我们提供了每一篇作品的当算是最详尽准确的背景资料,可是这又能带来什么呢?是锦上添花还是佛头着粪?唐代宋之问诗《渡汉江》“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无须解释,人们即能感受到久离家乡的归乡者的惴惴不安,这惴惴不安里有对家乡故人生死存亡的惦念,有对故乡是否拥抱游子的忧虑,还有若惊若喜的回乡之情,这是一种人人心中都有的普遍情感,读到它就勾起人对故乡的一分眷念。可是,《鉴赏辞典》本着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给这份动人的乡愁贴上一块经严密考据的“背景”:“这是宋之问从泷州(今广东罗定县)贬所逃归,途经汉江(指襄阳附近的一段汉水)时写的一首诗……宋之问这次被贬泷州,是因为他媚附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可以说罪有应得。”那份美好的情感就顿时烟消云散,在这个铁案如山的背景下,“近乡情更怯”成了被通缉的逃犯潜逃时的心理报告,“不敢问来人”则成了逃犯昼伏夜行鬼鬼祟祟的自我坦白,一首诗就这样被“背景”勾销了它作为“诗”的资格。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写得很美,是教材里的固定篇目,在课堂上由稚嫩的童声读来,尤自晶莹透彻,而一贴上背景就反而变得浑浊暧昧,“据《唐才子传》和《河岳英灵集》载,王昌龄曾因不拘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开元二十七年被贬岭南即是第一次,从岭南归来后,他被任为江宁丞,几年后再次被贬谪到更远的龙标,可见当时他正处于众口交毁的恶劣环境之中。”所以要辛渐到洛阳为他表白心迹,这当然很可能,但是,这首诗的意义被背景框架限定后,“一片冰心在玉壶”不仅成了不太谦虚的自我标榜还可能成了强词夺理的自我辩白,这首诗便不成为“诗”却成了押韵的“申述状”或“上告书”,未免大刹风景倒人胃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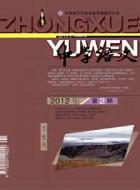
- 新课程改革,变异与恒久的交响曲 / 易继兵
- 浅谈如何落实语文三维目标 / 孙擎
- 探寻有效教学途径 构建理想语文课堂 / 高金彩
- 让语文课堂闪耀智慧之光 / 戴丹
- 提倡名著阅读,提升高中生语文综合素养 / 覃光明
- 现代教育技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 严永庆
- 高效课堂,教师该“高”出什么才有“效”? / 徐兵强
- 浅议高中语文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性 / 陈春芍
- 优质的高中语文课 / 崔光飞
- 高效课堂,要让学生“动起来” / 林国莉
- 高中语文课堂改革浅析 / 曹新胜
- 我所追求的富有魅力的语文课 / 张海容
- 接受 评判 引领 / 张晓珍
- “变”“活”中学语文课堂的几种意识 / 张玉春
- 开篇引趣,诱发好学之乐 / 吴平
- 浅析高中语文教学中审美教育的方法 / 尹兴丽
- 论语文课的审美化 / 韩振华
- 课堂上小组讨论存在问题和增效策略 / 朱亚娟
- 浅议语文课堂教学语言美 / 吴生鸿
- 中学生课外阅读心理探微 / 吴述全
- 从诗词结构角度鉴赏诗词 / 匡文豪
- 语文课堂学生主体地位的重塑 / 李娟
- 古诗词鉴赏“五突破” / 梁志钦
- 来一点“架空分析”又何妨 / 陈松泉
- 文言文有效教学初探 / 宫玉萍
- 浅谈高中语文诗歌审美教学 / 樊培如
- 实现文学类文本阅读与作文教学的对接 / 黄建慧
- 语文课要教出趣味 / 董文赟
- 试谈议论文中例证的教学 / 唐上等
- 宏观感知 把握主旨 / 张国会
- 李清照:怎一个“愁”字了得 / 张明花
- 面对阿Q,我们该说什么 / 刘荣
- 例谈情景手段在语文课堂中的运用 / 汪晓法 李丽平
- 也谈课堂提问的实效性 / 叶诞丰
- 高三学生语文学习的消极心理分析及调控措施 / 陈冬英
-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 高爽
- 以课外活动激发读写兴趣的尝试 / 卜英奎
-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 田亚琼
- 以“情”求“效” 走进语文新课堂 / 俞勤华
- 为了真理:自强不息,上下求索 / 周璨
- 阅读,让语文回归本位 / 陈立雄
- 返璞归真,走出作文教学的“暗胡同” / 田文生
- 称呼变化有意蕴 / 徐德湖
- 几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在作文中的运用技巧 / 金少成
- 君子善假于物也 / 卢文锋
- 如何培养农村高中学生作文审题能力 / 陈至宏
- 学生作文中的常见思维问题及其应对方法 / 郎杰
- 中学写作思维教学漫谈 / 石爱国
- 自改作文,善莫大焉 / 陈鹏
- 创作点滴谈 / 蒋国仁
- 创新是写作的源泉 / 蔡大囡
- 《长亭送别》导学创意 / 李成美
- 二三寸水起波涛 / 吴霖章
- 预设与生成的对话 / 吕晓乐
- 对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 / 杨生栋
- 《烛之武退秦师》导学设计 / 宋丽萍
- 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与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 / 段红伟
- 虚实相看两不厌 / 张磊
- 林语堂文化情怀与故乡风物人情 / 曾金华
- 爱和美在跳舞 / 杨金华
- 学校管理当与教改同行 / 杨森
- 走近鲁迅 / 龙健
- 思想的芦苇 / 吴政国
- 让阅读为语文插上腾飞的翅膀 / 李志国
- 《西厢记》与《牡丹亭》比较之管见 / 张晶
- 润物细无声 / 杨艳苓
- 恶之花 / 龚龙海
- 背景:标签或者补丁 / 周晓冬
- 小说中环境描写的作用 / 郭宁
- 添加还原要素阅读法 / 杨榀
- 高考赠别诗阅读中存在的问题 / 柴芳
- 从群体语言到个性语言的确立 / 谢灵敏
- 诗歌鉴赏备考“四要” / 施辉
- 点滴之间尽显礼制 / 傅成盛 张霞
- “连贯”的附庸?高考的王者? / 蒋其琪
- 一般论述类文章阅读的“四步走”做题方法 / 孙立红 孙立华
